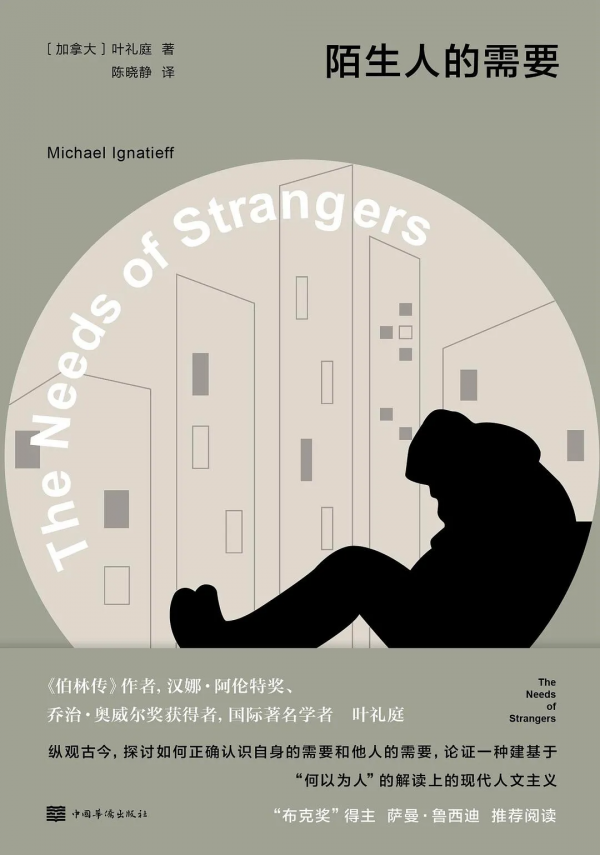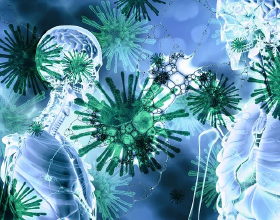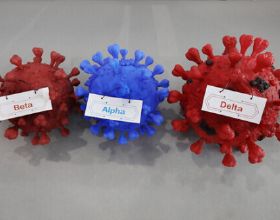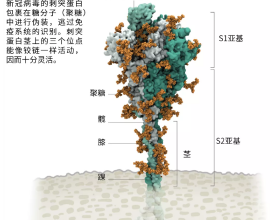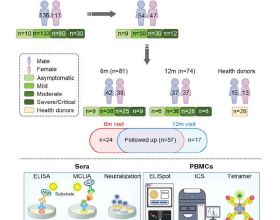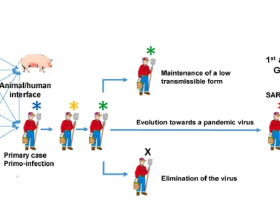在社交媒體上,我們經常會看到一種說法,叫做“來自陌生人的善意”,講的是在自己有需要的時候,陌生人主動伸出的援手。
在生活中,我們也或多或少都感受和經歷過類似的場景:有時候是傷心時來自對過的一張笑臉,有時候是遇到緊急情況時他人及時的幫助。
豆瓣話題“你收到過哪些來自陌生人的善意?”評論區截圖。
而構成陌生人善意的重要前提就是:我們的需要被看見。
這裡的“需要”當然是日常生活中一種通俗用法。但如果我們將其置於更廣闊的語境,“需要”不僅存在不同的意涵,也會延伸出一個在學術領域長久爭論的話題:什麼是他人的需要?誰有權界定他人的需要?為了他人的需要,我們可以付出什麼?付出到怎樣的程度?
顯然,這就不再是我們用樸素的道德直覺就能判斷得了的。事實上,我們對“需要”的理解既關乎民主政治,也關乎個體的自由權利。在很多時候,兩者的邊界模糊且富有爭議。由此,我們還能看見另一種流行說法:善意最傷人的時候,往往是在它自以為了解他人需要的時候。
近期出版的《陌生人的需要》一書就探討了政治哲學領域中這一相對陌生、卻極為重要的概念——需要(need)。
這本書的作者是國際知名的政治家與知識分子葉禮庭。他在書中區分了兩種“需要”:可以明確訴諸政治行動的需要,以及法律義務或公民責任都無法具體說明的需要。前一種需要的物件通常是我們生存所需的自然權利,例如食品、住所、衣物、教育、交通和醫療。後一種更多則是帶有美德色彩的後天權利,它們賦予我們生而為人所應有的尊重與尊嚴,例如博愛、社會團結與公民歸屬。
葉禮庭(Michael Ignatieff,1947- ),當今世界最具影響力、最敏銳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之一,喬治·奧威爾獎、漢娜·阿倫特獎得主。曾任教於劍橋大學、多倫多大學、哈佛大學。於2009年-2011年間出任加拿大自由黨黨魁。此前曾擔任戰地記者和政治評論員,出任多國政府顧問。著有《伯林傳》《火與燼》《戰士的榮耀》《陌生人的需要》。
在葉禮庭看來,身處現代社會,我們更多關注的是前者,這使得那些未被視作自然權利的需要逐漸被人遺忘,並悄然脫離了政治的表達。為了重新創造與豐盈關於“需要”的理論與語言,他嘗試回到過去,追溯從斯多葛到盧梭再到亞當·斯密關於“需要”的思考與論述,也為我們重新理解人的向度提供了另一視角的參照。
不做彼此精神上的陌生人——這是葉禮庭在書中試圖告訴我們的。下文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陌生人的需要》中的“前言”一章,較原文有較大幅度刪減,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原文作者 | [加]葉禮庭
摘編 | 青青子
《陌生人的需要》,[加]葉禮庭著,陳曉靜譯,三輝圖書 | 中國華僑出版社,2021年9月。
01
陌生人的道德關係
我住在倫敦北部的一條商業街上。每週二早晨,門外都會有一群退休老人在小販的推車裡挑挑揀揀,車裡有破了的窗簾、缺了紐扣的襯衫、染色的背心、破夾克衫、磨損的褲子和褪色連衣裙。門外,他們愉快地交談,同小販殺價,好似碎秸稈中啄食的烏鴉,爭搶著廉價品。
他們不算一無所有,只是生活拮据。與女士相比,男士們看起來更疏於打理:留著鬍子,臉色灰白,脖頸耷拉在發黃的襯衫領子裡。衣服下他們年邁的身軀,肯定是蒼白單薄的。女士們顯得更為沉著自信,似乎從母親那她們已經學會了要如何面對老去。應對貧窮,她們自有一套:外套褶邊整潔,紐扣依然固定在原位。
這些老人給人一種喪偶多年、子女遷居城郊的感覺。我想象他們就著電暖氣發出的光亮,獨自居住在昏暗狹小的房間裡。我曾經遇到一位獨自購物的老人,在土豆攤位前,他拎著重物、排著隊,累得差點暈倒。我讓他在酒吧裡坐下休息,幫他買好剩下的東西。雖然他確實需要幫助,但他顯然並不想要我施以援手。當時他正為了緩過一口氣來而大口喘息著,但當我們交談時,他目光直視前方,手指牢牢握住他那沉重的購物袋。所有這些老人似乎都與家人斷了聯絡,遁入自己愈加狹小的內心之境,他們緊抓那輛推車,彷彿那是載他們入海的舟筏。
電影《寄生蟲》劇照。
我與這些老人的交集,正是福利國家中陌生人道德關係的寫照。他們有所需,加之他們生活在福利國家,這些需要意味著他們對像我這樣的人所擁有的資源,有後天的或者自然的權利。他們的需要與後天權利構建起我們之間的無聲聯絡。當我們一同在郵局排隊,在他們兌現養老金支票的同時,經由國家各個複雜的系統,我收入中的很小一部分變為他們所有。對我們雙方來說,這種關係所具有的間接性是必要的。他們依靠的是這個國家,而非我,對此我們都樂得所見。我也意識到了這種間接性使我們彼此獨立。我們為彼此承擔責任,但我們並不互相負責。
我對他們的責任,由龐大的勞動分工體系來實現。以我的名義,社工們上樓來到他們的房間,最大限度地確保老人們暖和、整潔。當他們過於年邁無法出門時,志願者會送上熱飯、鋪好床,富有同情心的志願者還會聆聽他們絮語往事。當老人身體情況惡化,救護車會送他們到醫院,當他們奄奄一息時,會有護士在旁監測他們減弱的呼吸。正是有了陌生人之間的團結,有了勞動分工帶來的從需要到權利、權利到關愛的轉變,即使基礎脆弱,我們仍可以說自己生活在道德共同體中。
除了優於19世紀的濟貧院,無論以何種標準衡量,現代福利制度可能都稱不上慷慨,但它的確在嘗試滿足大部分人對溫飽、住所、醫療的基本需求。關鍵在於這是不是個體的所有需求。我們所說的“需要”不只是人類生存的基礎必需品,也指個體為了充分發揮自身潛能時的“需要”。“生存所需”與“發展所需”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那些商業街上年邁的窮人,他們得到的資源僅夠維生。但這些資源是否足夠他們過上像樣的生活呢,這有待商榷。
在這些老人並不知情的情況下,在左右翼圍繞福利國家未來展開的政治激辯中總是憑空想象他們的需要。雙方都認為老人們需要的是收入、食物、衣服、住所以及醫療,繼而爭論他們是否享有擁有這一切的權利,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資源供給是否充分。雙方都未曾提及的是,在這些單純的生存條件之外,老人們是否需要更多?
這種沉默不無理由。從衣食住行的角度來定義需要已足夠困難。畢竟人類的基本必需品是相對的、具有歷史性的,一直以來,在界定人類基本的後天權利時,每個社會都會出現激烈的討論。人類發展需要什麼,更是頗具爭議。好的生活不止一種。誰又能道明我們需要什麼才能實現為自己設定的所有最高目標呢?
02
如何界定“需要”?
我們對自身需要的自欺也是人所共知的。可以明確的是,人肯定知道自己渴望某物。但另一方面,他又很有可能意識不到自己需要什麼。正如想要的通常並不需要,需要的又往往並不是想要的。
然而如果我們時常對自身需要進行自欺,那麼對陌生人的需要也多半如此。在對人類關係的各種設想中,最危險的莫過於“我們比當事人自己更瞭解他們的需要”。在政治領域,這一立場會縱容無視民主優先權和踐踏自由的行為。其他領域亦是如此,醫生有權定義病人的需要,社工可以掌控當事人的需要,還有父母來決定孩子需要什麼,以上事例中的“僭越”行為是對“濫用”的一種“正當化”。
然而如果我們經常無法正確認識自身需要,那麼當我們無法表達它們時,為了我們的利益,必定有人為此發聲。社會上有這樣一群人,長期以來他們艱難度日,除了最低限度的生存必需品,他們不敢奢求更多。提高他們的期望值、讓他們瞭解自己從未擁有過的東西錯了嗎?認為我門外的陌生人不應滿足於推車裡的廢舊物錯了嗎?任何一種政治,如果它想要改善這些人的生活,就必須為那些他們自己可能都無法表達的需求發聲。這就是為什麼政治是如此危險的一件事:為了動員大部分人做出改變,你必須提高期望值、創造出可以超越既有現實的侷限的需要。創造需要會催生失望、引來幻滅。這好比是一場有關生命與希望的遊戲。“知情同意”這一民主前提,是這場危險遊戲唯一的保險栓。如果當事人自己都無法清晰認識自身需要的話,那麼代表他的人就更無權發聲了。
電影《小偷家族》劇照。
何時才該為陌生人的需要發聲?這是我最初產生的疑問。政治不僅是代表陌生人需要的藝術;在為陌生人自己無法表達的需要代言時,政治也是場危機四伏的交易。
對人類發展所需之物進行界定是否可行?這是我的第二個疑問。如果無法界定人類的需要,那麼代言陌生人的需要不僅危險,也將無法實現。實際上,除非個人可以認識到自身偏好並將其統一於共同需要的旗幟下,否則政治本身也將是空中樓閣。在一個既定的社會中,要對人類發展的先決條件達成某種最低限度的共識,如果沒有達成共識,始終如一的道德行為也將無從談起。
可以用政治和社會權利的語言明確表達的需要,以及不能明確表達的需要,這也是我想加以區分的。目前大部分的政治爭論是圍繞前者的,即對食物、住所、衣物、教育、就業的需要。在保守黨對福利國家的抨擊中,首當其衝的就是“需要創造自然權利”;這一抨擊使社會是一個道德共同體的概念遭到了質疑。
在我們試圖捍衛“需要創造自然權利”這一原則之餘,那些未被視作自然權利的需要則有可能被遺忘,並悄然脫離政治的表達。在表達個體既有可能對集體做出貢獻,也有可能拖累集體時,自然權利的語言提供了多種表達方式,但在表達個人對集體的需要時,它又是相對無力的。它只能將人類理想的友愛狀態體現為對彼此自然權利的尊重,基於我們自然權利承擔者的共同屬性,它能捍衛的也只是我們希望被體面對待的訴求。
然而我們不單是擁有權利的生物,一個人需要被尊重的也遠不止他的自然權利。我們所處時代的行政良知,在於它貶抑個體人格的同時,仍會尊重他們的自然權利。比如在我們最好的監獄與精神病院,囚犯和病人可以得到尚可的飲食、服裝、住所;律師與親人的探訪未被阻撓;手銬與警棍存放在警衛室。這些被認定為自然權利的需要基本都得到了尊重。然而從短暫停留的目光中,從一個動作或者一項程式中,犯人們依然能隨時感受到當權者無聲的不屑。我門外的陌生人擁有社會福利權,不過那些給予他們這些權利的官員是否尊重與關心他們,則要另當別論了。
電影《我是布萊克》劇照。
正因為金錢無法購得受到尊重的姿態,自然權利也無法確保它們成為後天權利,所以任何一個正義的社會都需要一種針對人類個體需要的公共表達。情誼、愛、歸屬感、自尊和尊重無法被規定為自然權利,因此我們應將其定義為需要,並透過已有的、並不高效的公共體系,力求將滿足這些需要變成人類的慣常實踐。如果之前我們就具備了一種可以表達需要的語言,那麼現在我們就能更好地理解“賦予人們權利”與“滿足人們需要”的區別。
我想表達的是,體面、仁愛的社會需要一種共有的語言來表達善。而我們的社會賴以生存的權利的語言缺乏關於善的表達。後者要求的是法律義務或公民責任都無法具體說明的美德行為。
有關人類需要的論述是人類善的一種特殊表達。透過需要來定義人性,就是以我們缺什麼來定義我們是什麼,強調了人類作為一個物種所特有的虛無與不完整性。我們只是擁有潛力的自然生物。我們並不具備與生俱來的萬物支配權。但我們是唯一可以創造和改變自身需要的生物,是唯一的自身需要歷經發展的生物。我們為自身創造的需要,以及由此衍生而來的後天權利語言,賦予我們作為一個物種和一個個體應有的尊重與尊嚴。因此,需要就是一種對善帶有明顯歷史性和相對性的表述。
人性善理論不應建立在“快樂至上”的基礎上,不應視快樂為人類的終極歸宿。愛帶來快樂,而我們對愛的需要超越了這種快樂;我們需要愛,是因為她同時帶給我們聯結與歸屬,讓我們與他者相連。生活中有許多深層次的需要,其中愛是至高無上的,但它們並不一定會帶給我們快樂。我們需要它們,是為了深入生命,為了最大限度地瞭解自身,為了調和我們對自身和周遭的認識。
最後,人類需要的理論必須以“人何以為人”的一系列選擇為基礎:“為人”就是要充分發揮自身潛能,而非快樂、自由這些次要目標。“為人”意味著什麼,這沒有一勞永逸的答案。記錄下人生中最為珍視之物,就是我們所要做的一切。
03
不做彼此精神上的陌生人
確實有一系列詞語來表述這些需要:愛、尊重、榮耀、自尊、團結。問題在於政治語境中對它們的隨意濫用,已使它們意義全無。它們變得廉價,是因為隨意的虛誇言辭,以及“能夠滿足人們基礎生存需求的社會,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滿足他們的非物質需求”的草率設想。然而“生存所需”和“發展所需”之間的關係要更為複雜。養老金與醫療救助也許是窮苦老人維持自尊與尊嚴的必要條件,但並非充分條件。重要的是給予方式和給予行為的道德基礎:社工們是否傾聽了這些老人的故事?公寓樓梯陡,帶他們下樓時,救護人員有否留心避免他們受到磕碰?老人們在醫院獨自驚恐之時,是否有護士在旁陪護?尊重與尊嚴正是由此而來。這些人類姿態涉及太多人性的藝術,因而無法轉化為一種持久的日常管理。
自尊和尊嚴還有賴於後天權利被如何解讀——是自然權利,是應得的,還是一種施捨?在許多西方福利國家,給予者與接受者仍將後天權利視作贈予。在困難時接受救濟,依然被視為羞恥之事。在法律層面,需要催生了自然權利,但在我門外的那些陌生人的心中,未必如此。
我們之所以尊重他人,是因為將其視為獨立的個體還是視為我們的同類,這是福利國家的核心矛盾。前者源於每個人的特質;後者則是針對他們的共性。前者要求我們區別對待他人;後者則要我們對每個人一視同仁。福利國家將不同人的需要同等化,認為不同的人應被同等對待。然而我們的需要並不一致:尊重之於你我的意義可能是不同的。此外,作為不同的人,所有的個體都應得到不同的尊重。假設每個人都有相同的需要,這可能是我們要尊重每個個體的一個必要條件,但這並非充分條件。是否有一個福利系統,可以調和平等對待每個個體與尊重每個個體之間的矛盾,至今無解。以同樣的方式對待個體的結果是人的物化——這是對現代福利最常見的批評。
難道就沒有某些需要,它們與我們對尊重的需要類似,除非犧牲掉包括被平等對待在內的部分需要,否則集體社會供給就無法滿足它們?在我們對社會團結和自由的需要之間,類似的潛在矛盾出現了。存在於自然權利語言和後天權利語言中的利己主義偏見,使我們難以理解這種矛盾,而它又是最為關鍵的。我們不僅有自身的需要,還有為他人代言的需要。許多人足夠幸運、足夠富有,他們衣食無憂、有容身之所,而同胞的窮苦,讓他們感到自身的富足蒙上了蔭翳。
電影《小偷家族》劇照。
社會良知還不足以解釋這一切。個體無法獨立掌控既定的偏好;個體的需要包括他人的需要與自身的匱乏。為了孩子我們需要好的學校,為了鄰居我們需要安全的街道,為了門外的老人我們需要舒適的養老院,不論這些需要是代表他人或是自身,都不足為奇。人類感知他人需要的能力,在最深處孕育了投身政治的動力源泉。
福利國家認可對團結的需要,但也確保擁有資源的人和資源匱乏的人維持陌生狀態。包括伊萬·伊利奇(Ivan Illich)在內的一些人認為,社會分工與社會團結無法相容。如果我們不想再做彼此精神上的陌生人,那就必須消除國家福利體系。但我懷疑門外那些領著養老金的陌生人是否還想回到過去,那會兒他們依賴兒女易變的憐憫和不穩定的慈善捐贈。收益透過官方在陌生人之間流轉,使我們得以擺脫贈予關係的束縛。但是如果社會致力於滿足對自由的需求,它就無法兼顧對團結的需要。這將依然是一個陌生人社會。
本文經出版社授權摘錄自《陌生人的需要》。原作者:[加]葉禮庭;摘編、編輯:青青子;導語校對:賈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