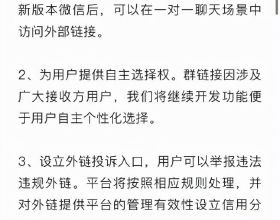作者:牛達生
20世紀百項考古重大發現之一
西夏陵的田野考古工作是從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的。在此之前,似乎人們很少關注西夏陵的存在。
我是最早參加西夏陵田野考古的業務人員之一,對1972年春第一次到西夏陵的情景仍記憶猶新。站在高處極目望去,星羅棋佈的土冢高聳雲天、氣勢宏大:腳下卻是一堆堆廢墟、一段段殘牆、一墩墩夯土臺基,俯拾即是的殘磚爛瓦,一片破敗景象。這些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廣袤、荒涼、深邃、神秘,還有破敗。此情此景,讓人不由得想起明代安塞王朱秩炅的《古冢謠》:“賀蘭山下古冢稠,高下有如浮水漚。道逢古老向我告,雲是昔年王與侯。"短短四句便道出了西夏陵荒煙野草不勝淒涼的景象,隱喻了世事變幻莫測,無論貴賤一樣猶如浮在水面的氣泡,時生時滅飄浮不定。
30多年來,寧夏的考古人員大都在這裡流過汗水、作過貢獻。西夏陵區背山(賀蘭山)望水(黃河),地勢開闊。在58平方公里的賀蘭山洪積扇地帶,從南向北坐落著9座皇帝陵園和250多座皇親國戚、達官貴人的陪葬墓。此外,還有寺廟建築、磚瓦窯、石灰窯等遺址多處。到目前為止,己考古發掘帝陵1 座、陪葬墓4座,清理寺廟遺址、碑亭遺址和磚瓦窯遺址多處,出土了大量文物,逐漸揭開了西夏陵神秘的面紗,使我們對西夏文化有了更多的認識。我們深切的感到:西夏陵具有獨特的人文景觀和豐晶的文化內涵,是研究西夏陵寢制度、西夏建築和西夏文化的寶地。理所當然,它早己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全國重點風景名勝區,也是國家文物局公佈的中國 20 世紀百項考古重大發現之一。2011年11月,西夏陵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暨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項
目正式啟動,我有幸參加了這一活動。2012年11月,西夏陵正式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眼下各項工作正在穩步推進,最後申報成功,指日可待。
西夏陵現在已經是寧夏的王牌旅遊景點之一,在國內外有相當的影響和知名度。而這一切,無不基於考古發現和研究。記得一本美國出版的《旅遊學》中說,“許多旅遊勝地,都起源於歷史功績。”銀川之所以成為歷史文化名城,不僅因為這裡是塞外江南,回族故鄉,更重要的她還是西夏都城興慶府故址,這裡有著豐富的西夏文物古蹟。銀川由一個小城市發展成為中國西部的一箇中等城市,基於西夏考古研究成果而發展起來的西夏旅遊,不能不說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風格獨特的陵園遺蹟
獨立完整
西夏陵的地面遺蹟儲存得還算完整,平面佈局十分清楚。例如3號陵,大體看來坐北朝南,呈縱向長方形。從南向北,依次排列著闕臺、碑亭、月城、神城(包括門樓臺基、角樓臺基)、獻殿、塔式陵臺等,還有神城外的四座角臺,總面積15萬多平方米。這是一個由神城及其附屬建築組成的獨立完整的建築群體。它與唐宋陵園一樣,體現了面南為尊的傳統觀念。3號陵是陵區諸陵中面積最大、造型最為奇特的一座陵園。陵區諸陵的建築臺基多為方形,而這裡基本上都是圓形的。
角臺之設
每座陵墓都有界限,這就是所謂的“兆域”。“兆域”之設古已有之,《周禮·春官》載:“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三國志·魏書·武帝紀》稱,對武帝曹操的墓,要“廣為兆域,使足相容”,也就是要擴大兆域的範圍。漢唐陵墓的兆域,因其範圍很大,沒有一個明確的地物標誌。而西夏陵,卻以神城之外的四個“角臺”為其“兆域”界線。它建在神城對角線上,距神城角闕數十米遠,從而擴大了兆域範圍。在4 個角臺中,南面角臺東西距離大,北面角臺東西距離小,在圖紙上將4個角臺用線連起來的形狀是個梯形。這個“梯形”不只是陵園的界線,似乎還含有“崗哨”的象徵意義。在古人的“事死如事生”觀念中,陵園就像皇宮大內一樣要有人守衛,而陵園無關人員大概是不可越過這條線的。
3號陵的角臺也是圓形臺基,可惜多已傾倒,僅西北角的儲存較好,底徑和高度都在6米左右。從地面出土磚瓦頻伽、塔剎等建築構件推斷,這裡很可能是一個漂亮的亭式建築。在歷代帝王陵園中都無“角臺”的設定,這是西夏陵園建築結構的特點之一。
碑亭建築
進入3號陵園,沿神道從南向北走來,首先看到的是兩座圓形的闕臺建築臺基。它們位踞神道兩側,皆為夯土所築,據實測,其中東闕臺底徑10.8米,殘高8.35米。原壁面並不是裸露的,而是用草秸泥打底、赭紅泥抹光的。地面遺物以瓦類居多,其上應有覆瓦。從臺基上還有一個圓形的二層臺,二層臺中央還有一個圓柱體,從圓柱體中心還留有一個柱洞判斷,闕臺作為陵園的入口,原來很可能是一個高大雄偉的重簷圓形樓閣建築。
由闕臺向前,神道兩側是碑亭遺址。兩座碑亭都己發掘,從遺蹟看,它是一個高2.2米,邊長21米的方形夯土臺基,但其上卻是圓形殿堂建築。己發掘的6號陵碑亭,東側為圓形建築,西側是方形建築,如果復原起來,都是各有千秋的殿堂建築。各個碑亭建築上的差異,顯示了西夏匠師獨具匠心,不拘泥完全的對稱的處理手法。當然,碑亭建築的差異,或許還有宗教或文化方面的意義,這是值得探討的。另外,唐宋陵墓多無碑亭之設,僅1995年在乾陵清理出“述聖碑”和“無字碑”的碑亭遺址,糾正了兩碑原是露天的說法。查諸資料,其他唐宋陵墓皆未發現碑亭之設。西夏陵的碑亭建築,是否受此影響抑或自創,有待研究。
殘碑文字
3號陵碑亭遺址出土了不少文物,其中最重要的是碑刻殘片和造型獨特的力士碑座。
歷代帝陵(如漢陵、唐陵、宋陵等),何帝葬於何處,規模形制如何,多有記載,具體位置也可以確認。而西夏陵僅在《宋史·夏國傳》中載有某帝陵號,至於陵園建在何處、如何營建、規模大小等,則無一字可尋。因此,確定每座陵園的陵主,便成為我們考古人員的第一課題。考古人員清理過多座帝陵和陪葬墓的碑亭遺址,出土了大量的碑刻殘片,有漢文的,更有西夏文的,提供了一些非常有價值的資料。7號陵(第五代皇帝仁宗李仁孝的壽陵)和182號陪葬墓(梁國正獻王嵬名(西夏皇姓)安惠的墓園)就是根據碑文殘片確認的。當然還有其他重要資料,如西夏在“崇宗踐位”後,曾命梁國正獻王“城中興”,可知西夏此時曾修繕都城,並改興慶府為中興府等。這些都是文獻中未曾見過的寶貴資料。又如,《宋史·夏國傳》記載崇宗作《靈芝歌》,沒有留下歌詞,但7號陵漢文殘碑卻發現了《靈芝頌》殘碑,文曰:“靈芝頌一首,其辭曰……俟時效址,擇地騰芳,……德施率土,賚及多方”,來頌揚西夏的靈瑞之氣、德被多方。殘碑證實了記載的真實性,還為西夏文字和書法藝術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著名的《涼州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簡稱《涼州碑》),至今仍是惟一完整的西夏文碑。西夏陵殘碑為西夏的碑刻資料作了重要補充。但從總體上說來,出土碑刻過於殘破。一通碑少則數百塊,多者千數塊(加上無字的可達數千塊)。其中,數十字的不多,超過百字的更是屈指可數,多為數字、一字、半字的碎塊,難成句讀,十分可惜。過去,在荒無人煙的地方,常有殘碑斷碣,引人發古之幽情,但西夏陵碑刻的殘破程度要比這嚴重得多。成吉思汗的征服戰爭是以異常殘酷而聞名的,他在滅夏戰爭的最後時刻,殺害了準備投降的西夏末帝李睍,對中興府大肆殺戮,“屠城”滅種,使這座曾經繁榮一時的西夏都城,成為一座死城,一座空城。為了破壞所謂的西夏風水,掠奪財富,又派大部隊將西夏陵翻了個底朝天。我們今天在西夏陵所見到的一堵堵殘牆、一堆堆廢墟,應該說就是當時破壞的現場。石碑的殘破程度,說明蒙古鐵騎在進行空前的大破壞時,會指定專人負責敲打,越碎越好。
力士碑座
3號陵碑亭遺址和6號陵、8號陵還出土了許多石刻力士碑座。這種碑座略呈方形,邊長60釐米左右,正面刻出人像,頂部平整。但完整的碑是什麼式樣,如何立在碑座上,至今是個謎。人體形象奇特,屈膝跪坐,袒胸露腹,面部渾圓,粗眉上翹,鼻頭粗短,雙目如鈴。最令人驚奇的是:頭部誇張,幾乎占身體的一小半;雙乳肥碩,垂於胸前;後肢屈跪,前肢多撐於雙膝,僅有一例為雙手上舉。仔細欣賞,還會發現手腕、足脛佩有環飾。碑座人物形象多有變化,並不完全一致,但都是跪坐負重的形象。這一尊尊造型奇特的碑座,如果不是和碑文殘片一同出土,誰能說清楚它是幹什麼用的。力士碑座給人以原始、粗放、誇張、神秘,反映了西夏造型藝術的獨特手法。西夏為什麼不用人們常見螭首龜跌,這又是一個謎。力士碑座的使用,不能不說是西夏陵的又一特色。
有人認為,力士手腕、足脛配戴環飾是古代西南地區土著民族愛好的一種裝飾。《北史》載:其俗“項系鐵鎖,手貫鐵釧"。党項人興起於青藏高原,西夏陵園出現這種帶釧的形象,是否是對先祖習俗的一種回眸呢?有人認為此處力士是佛教中的力士。成都五代前蜀王建永陵揹負棺床的力士、河北正定宋代隆興寺大悲閣揹負佛座的力士、寧夏賀蘭山拜寺口雙塔塔剎轉角處揹負塔剎的力士和西夏陵碑座力士,都有相類之處。看到這身壯體肥、肌肉凸顯的形象,不能不使人想起力大無比的相撲鬥士。也許西夏藝術家想借用這種形象,來顯示其“力拔山兮氣蓋世”的氣勢。說到這裡,又似乎覺得石刻人像缺少石窟造像中力士威武氣概,表情中更多的是一種無奈。也有人說,這種跪姿負重的形象,是現實生活中奴隸的反映。真是見仁見智,各有所見。
不毀的神牆
碑亭之後是月城,在我國曆代陵園中皆無月城之設。但在西夏陵建築中,月城的作用不小,它是建在神城之前的小城,二者呈倒凸字形,寬近130米,進深不到50米,是從外通向神城的一個過渡,起神城前衛的作用。月城還是排列石像生的地方,或為二列,或為三列,可惜都己破壞無存。唐陵、宋陵將石像生置於神城前神道兩側,拉的距離很長,二者的意趣是完全不同的。它使陵園的結構更為緊湊、合理。《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二三載,李元昊講究“務實”,認為唐宋禮樂過於繁縟,於是簡化禮樂制度,“革樂之五音為一音,裁禮之九拜為三拜”,並在吉凶、嘉賓、祭祀、燕享等場合實施。月城的設定和石像生的植入,可能正是西夏“務實” 精神的體現。
神城是陵園建築的主體。神城四周的夯土神牆至今大體完整,有的地段殘高達4米以上。這種夯土牆,在農村並不少見,但儲存了近千年,仍然屹立在那裡,實在是個奇蹟。神城四門的門闕(門樓)和神牆四角的角闕(角樓),更是十分奇巧,與我們常見的平直的夯土牆不同,是用夯土圓墩築成的,這在中國建築史上,在歷代建築遺址考古中尚未見到類似的例項。
神城四角的角闕,轉角主墩高大厚實,每側各有相連的兩個或三個圓墩,呈直角向兩側延伸,並與牆體相連線。兩側的墩體,其體量大小、高低相應收縮,組成一個5墩和7墩的直角形的角闕。因在遺址周圍出土了蓮花座、寶瓶、相輪、剎杆等文物,有人認為每一個圓墩上部,可能是一個亭式塔。可以想見如果復原的話,它該是多麼雄渾壯麗的建築!
神城四門的門闕,每側各有3個相連的夯土圓墩,兩闕之間是方形門址。在門址的發掘中,發現了柱礎及各種建築材料(除筒瓦、板瓦、瓦當、滴水外,還有脊獸、套獸、蹲獸等),得知原來兩闕之上是有門樓之類建築的。在古代建築中,闕是禮儀性建築,也是裝飾性建築,多獨立於宮殿、陵寢、寺廟等建築的前部,亦有在兩闕之間建門樓,並與牆體相連線,以使群體建築更加莊嚴隆重。有的闕又附加一個或兩個子闕,稱之為“子母闕”或“三出闕”,以顯示其尊貴的地位。乾陵朱雀門兩側就有三出闕闕臺,3號陵的做法是否受了乾陵建築的影響,也是一個類似“三出闕”的建築呢?
塔式陵臺
中國傳統建築講究對稱,所有主要建築都建在一條中軸線上。西夏陵園建築,大體也保持了對稱的格局,但卻是有變化的。這主要體現在神城內獻殿、陵臺兩座建築上。它們都偏離子午線,而在軸線的西側。獻殿離門址不遠,前後有坡形漫道,推測其應是一個造型別致的穿堂式殿堂建築。陵園中最引人注目的建築,是高大突兀的塔式陵臺。臺基座為圓形,其上為塔式陵臺,直徑37.5米,殘高21米,有7層塔簷。塔簷上尚存瓦片堆積,說明它是覆瓦出簷的。在轉角處的垂脊和角粱上,裝有精美的人首鳥身的迦陵頻伽(又稱妙音鳥)和綠色琉璃的套獸。1號陵、2號陵這兩座陵園中的陵臺比3號陵高,有9層塔簷,高23米,顯示了陵主尊貴的地位。但陵主為誰,尚難確定。陵臺之所以和塔聯絡起來,是因為它實際上是一座實心的八角形密簷式塔。根據考古資料判斷,現在看似大土包的陵臺,原來是外抹赭紅泥、覆瓦出簷、簷角飾以套獸,頂為八角攢尖式的雄偉壯觀的塔式建築。
我國自春秋戰國以來,帝王陵墓的陵臺,或為圓丘狀,或為覆鬥形,未聞有塔形的。如果說西夏陵與歷代帝陵最大的不同點是什麼,就是它與眾不同的塔式陵臺。因此,西夏陵亦被媒體稱為“東方的金宇塔”。在歷史上,皇帝視自己為“佛”,受人頂禮膜拜者多有。北魏皇帝更是如此,謂“朕即佛”。大同雲岡石窟著名的“曇耀五窟造像”,就是按照北魏前五代皇帝的真身雕造出來的。西夏皇帝是否稱自己為佛,已無從稽考,但塔式陵臺實際上就是一座瘞埋佛骨、讓人頂禮膜拜的佛塔。這意味著西夏皇帝有視己為佛的觀念,希望他死後被人當佛去膜拜、供奉。
變化的格局
人們也許會問,其他未開放的帝陵陵園,建築結構和平面佈局是否與3號陵園相同?在結構上、其他諸陵建築臺基基本上是方形的,而3號陵如前所述最大的不同點是建築臺基都圓形的,神城上的門闕、角闕也是圓形的,甚至陵臺的基座也是圓形的,顯得特別奇特。就平面佈局而言,應該說基本是一致的,都是坐北朝南,都呈縱向長方形,面積都在10萬平方米以上。但諸陵平面佈局又有所差異,最大的不同是多數陵園都有外郭。1號陵、2號陵和7號陵外郭是全封閉的,將全部地面建築圈入城郭內,角臺置於外郭的四角,因此“兆域”範圍有所縮小。另外,在東碑亭前方又加一小碑亭,成為3座碑亭。同時在神城內對角線的交會點上,又設定中心臺(方形夯築,邊長5米,高5米),這是唐宋陵所沒有的,它的用途至今不明:5號陵、6號陵的外郭則是開口式的,但5號陵附有象徵性的甕城。總之,可分為單城式、重城式;重城又分為開口式、封閉式、附甕城式。陵園建築基本格局一致而又富有變化的特點,避免了陵園建築的呆板單調,反映了西夏人民的創造精神。
牛達生:寧夏文物考古研宄所研究員,寧夏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西夏文化研宄中心學術委員。主要研宄西夏考古,兼及寧夏史地、西夏學、錢幣學、印刷史等。主持過拜寺溝方塔等遺址的發掘,因西夏木活字印刷的研究成果,獲中國出版印刷行業最高獎“畢異獎”。主要著作有:《西夏活字印刷研宄》《西夏錢幣研究》《西夏遺蹟》《西夏考古論稿》《西夏拜寺溝方塔》等。
本文出自《大眾考古》,2014年第9期,21-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