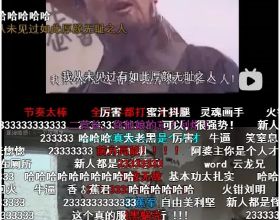《復活》
列夫·托爾斯泰
儘管好幾十萬人聚居在一小塊地方,竭力把土地糟蹋得面目全非;儘管他們肆意把石頭砸進地裡,不讓花草樹木生長;儘管他們除盡剛出土的小草,把煤炭和石油燒得煙霧騰騰;儘管他們濫伐樹木,驅逐鳥獸;在城市裡,春天畢竟還是春天。
《雙城記》
查爾斯·狄更斯
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那是智慧的年頭,那是愚昧的年頭;那是信仰的時期,那是懷疑的時期;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們全都在直奔天堂,我們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簡而言之,那時跟現在非常相像,某些最喧囂的權威堅持要用形容詞的最高階來形容它。說它好,是最高階的;說它不好,也是最高階的。
《追憶似水年華》
馬塞爾·普魯斯特
在很長一段時期裡,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有時候,蠟燭才滅,我的眼皮兒隨即合上,都來不及咕噥一句:”我要睡著了。”半小時之後,我才想到應該睡覺;這一想,我反倒清醒過來。
《百年孤獨》
加西亞·馬爾克斯
很多年以後,奧雷連諾上校站在行刑隊面前,準會想起父親帶他去參觀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當時,馬孔多是個20戶人家的村莊,一座座土房都蓋在河岸上,河水清澈,沿著遍佈石頭的河床流去,河裡的石頭光滑、潔白,活像史前的巨蛋。
《茶花女》
小仲馬
我認為只有深刻地研究過人,才能創造出人物,如同只有認真地學習了一種語言才能講它一樣。
《傲慢與偏見》
簡·奧斯汀
凡是有錢的單身漢,總想娶位太太,這已經成了一條舉世公認的真理。這樣的單身漢,每逢新搬到一個地方,四鄰八舍雖然完全不瞭解他的性*情如何,見解如何,可是,既然這樣的一條真理早已在人們心目中根深蒂固,因此人們總是把他看作自己某一個女兒理所應得的一筆財產。
《日瓦戈醫生》
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
他們走著,不停地走,一面唱著《永誌不忘》,歌聲休止的時候,人們的腳步、馬蹄和微風彷彿接替著唱起這支哀悼的歌。
《局外人》
阿爾貝·加繆
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養老院的一封電報,說:“母死。明日葬。專此通知。”這說明不了什麼。可能是昨天死的。
《貴族之家》
屠格涅夫
春光明媚的一天已近黃昏,小朵小朵玫瑰色的彩雲高懸在晴朗的天空,彷彿並不是徐徐飄動,而是緩緩沒入碧空深處。O省省城最邊緣的街道中的一條街道上,一幢美輪美奐的宅第敞著的窗前(事情發生在一八四二年),坐著兩個婦女:一個有五十來歲,另一個已經是七十來歲的老太婆了。
《了不起的蓋茨比》
弗朗西斯·司各特·菲茲傑拉德
我年紀還輕、閱歷不深的時候,我父親教導過我一句話,我至今還念念不忘。“每逢你想要批評任何人的時候,”他對我說,“你就記住,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並不是個個都有過你擁有的那些優越條件。”
《項鍊》
莫泊桑
世上的漂亮動人的女子,每每像是由於命運的差錯似地,出生在一個小職員的家庭;我們現在要說的這一個正是這樣。她沒有陪嫁的資產,沒有希望,沒有任何方法使得一個既有錢又有地位的人認識她,瞭解她,愛她,娶她;到末了,她將將就就和教育部的一個小科員結了婚。
《老人與海》
厄尼斯特•海明威
他是個獨自在灣流中一條小船上釣魚的老人,至今已去了84天,一條魚也沒逮住。
《情人》
瑪格麗特·杜拉斯
我已經老了,有一天,在一處公共場所的大廳裡,有一個男人向我走來。他主動介紹自己,他對我說:“我認識你,永遠記得你。那時候,你還很年輕,人人都說你美,現在,我是特地來告訴你,對我來說,我覺得現在你比年輕的時候更美,那時你是年輕女人,與你那時的面貌相比,我更愛你現在備受摧殘的面容。”
《基督山伯爵》
大仲馬
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在避風堰瞭望塔上的瞭望員向人們發出了訊號,告之三桅帆船法老號到了。它是從士麥拿出發經過的裡雅斯特和那不勒斯來的。立刻一位領港員被派出去,繞過伊夫堡,在摩琴海岬和裡翁島之間登上了船。
《荊棘鳥》
考琳·麥卡洛
1915年12月8日。梅吉·克利裡過了她的第四個生日。媽媽收拾好早飯的盤碟,不聲不響地把一個褐色的紙包塞進了她的懷裡,叫她到外面去。於是,梅吉便蹲在前門旁邊的金雀花叢背後,不耐煩地扯了起來。她的手指不靈活,那包包又扎得挺結實。它有幾分象是波利尼西亞人開的雜貨店裡的東西,這使她覺得,不管它裡邊包的是什麼,反正不是家裡做的,也不是捐贈的,而是買來的。這可真了不起。包的一角露出了一個好看的淡金色的東西;她更加起勁地扯著那紙包,扯下的長長的紙條亂成一團。
《雪國》
川端康成
穿過縣界長長的隧道,便是雪國。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車在訊號所前停了下來。
《被背叛的遺囑》
米蘭·昆德拉
懷孕的高郎古傑夫人吃多了牛腸竟然脫了肛,下人們不得不給她灌收斂藥,結果卻害得她胎膜被撐破,胎兒高康大滑入靜脈,又順著脈管往上走,從他母親的耳朵裡生出來。
《安娜·卡列尼娜》
列夫·托爾斯泰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巴黎聖母院》
雨果
距今三百四十八年六個月一十九天,巴黎老城、大學城和新城三重城廓裡,一大早群鍾便敲得震天價響,把全市居民都弄醒了。
《大象的眼淚》
莎拉·格魯恩
炊事篷的紅白遮棚下只剩三個人,就是格雷迪、我和油炸廚子。格雷迪跟我坐在一張破舊的木桌前面,一人面前一隻凹痕累累的馬口鐵盤子,盤上擱著一個漢堡包。廚子人在櫃檯後面,正在用刮鏟刮鍋子。油鍋早熄火了,但油膩味兒縈迴不去。
來源:詩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