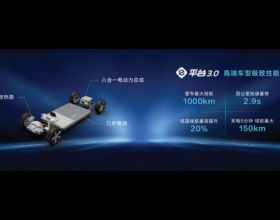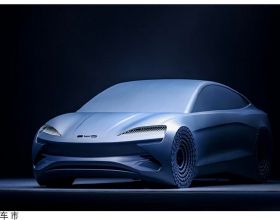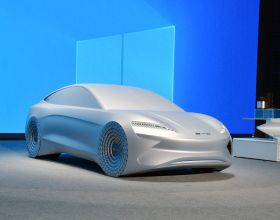因為生活正變得越來越疲沓、瑣碎、庸碌和公式化,人的想象力也相對變得老化和平淡。所以現在儘管有故事生動的作品不停地被人叫好,但我讀後總是有一股難言的失望,因為我看不到一部真正的優秀作品所應散發出的精神光輝。
——《遲子建散文集》
0 1
我的夢開始的地方
從中國的版圖上看,我的出生地漠河居於最北端,大約在北緯53度左右的地理位置上。那是一個小村子,依山傍水,風景優美,每年有多半的時間白雪飄飄。我記憶最深刻的,就是那漫長的寒冷。冬天似乎總也過不完。
我小的時候住在外婆家,那是一座高大的木刻楞房子,房前屋後是廣闊的菜園。短暫的夏季來臨的時候,菜園就被種上了各色莊稼和花草,有的是讓人吃的東西,如黃瓜、茄子、倭瓜、豆角、苞米等;有的則純粹是供人觀賞的,如矢車菊、爬山虎等等;當然,也有半是觀賞半是入口的植物,如向日葵。一到晝長夜短的夏天,這形形色色的植物就幾近瘋狂地生長著,它們似乎知道屬於它們的日子是微乎其微的。我經常看見的一種情形就是,當某一種植物還在旺盛的生命期的時候,秋霜卻不期而至,所有的植物在一夜之間就憔悴了,這種大自然的風雲變幻所帶來的植物的被迫凋零令人痛心和震撼。

我對人生最初的認識,完全是從自然界的一些變化而感悟來的。比如我從早衰的植物身上看到了生命的脆弱,同時我也從另一個側面看到了生命的從容。
童年圍繞著我的,除了那些可愛的植物,還有親人和動物。請原諒我把他們並列放在一起來談。因為在我看來,他們都是我的朋友。我的親人,也許是由於身處民風淳樸的邊塞的緣故,他們是那麼地善良、隱忍、寬厚,愛意總是那麼不經意地寫在他們的臉上,讓人覺得生活裡到處是融融暖意。當然,他們也有自己的痛苦和煩惱,比如年景不好的時候他們會為沒有成熟的莊稼而惆悵;親人們故去的時候,他們會抑制住自己的悲哀情緒。我從他們身上,領略最多的就是那種隨遇而安的平和與超然,這幾乎決定了我成年以後的人生觀。
生物本來是沒有高低貴賤之分的,但是由於人類的存在,它們卻被分出了等級,這也許是自然界物類競爭、適者生存的法則吧,令人無可奈何。尊嚴從一開始,就似乎依附著等級而生成的,這是我們不願意看到和承認的事實。雖然我把那些動物當成了親密的朋友對待,但久而久之,它們的斃命使得憐憫心不再那麼強烈,我與庸常的人們一樣地認為,它們的死亡是天經地義的。只是 成年以後遇見了許多惡意的人的猙獰面孔後,我又會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些溫柔而有情感的動物,愈發地覺得它們的可親可敬來。 所以讓我回憶我的童年,我想到親人後,隨之想到的就是動物,想到狗伸著舌頭對我溫存地舔舐,想到大公雞在黎明時嘹亮的啼叫聲,想到貓與我同時爭一隻皮球時的猴急的姿態。在喧譁而浮躁的人世間,能夠時常憶起它們,內心會有一種異常溫暖的感覺。
所以,在我的作品中,出現最多的除了故鄉的親人,就是那些從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的動物,這些事物在我的故事中是經久不衰的。比如《逝川》中會流淚的魚;《霧月牛欄》中因為初次見到陽光、怕自己的蹄子把陽光給踩碎了而縮著身子走路的牛;《北極村童話》裡的那條叫“傻子”的狗;《鴨如花》中的那些如花似玉的鴨子等等。此外,我還對童年時所領略的那種種奇異的風景情有獨鍾,譬如鋪天蓋地的大雪,轟轟烈烈的晚霞,波光盪漾的河水,開滿了花朵的土豆地,被麻雀包圍的舊窯廠,秋日雨後出現的像繁星一樣多的蘑菇,在雪地上飛馳的雪橇,千年不遇的日全食,等等。我對它們是懷有熱愛之情的,它們進入我的小說,會使我在寫作時洋溢著一股充沛的激情。我甚至覺得, 這些風景比人物更有激情和光彩 ,它們出現在我的筆端,彷彿不是一個個漢字在次第呈現,而是一群在大森林中歌唱的夜鶯。 它們本身就是藝術。
在這樣一片充滿了靈性的土地上,神話和傳說幾乎到處都是。我喜歡神話和傳說,因為它們就是藝術的溫床。相反,那些事實性的事物和已成定論的自然法則卻因為其冰冷的面孔而令人望而生畏。神話和傳說喜歡以兩種方式存在,一種類似地下的礦藏,我們看不見摸不著,但能嗅到它的氣息,這樣的傳說有待挖掘。還有一種類似於空中的浮雲,能望得見,而它行蹤飄忽,你只能仰望而無法將其捺入掌中。神話和傳說是最絢麗的藝術靈光,它閃閃爍爍地遊蕩在漫無邊際的時空中。而且,她喜歡尋找妖嬈的自然景觀作為誕生地,所以 人世間流傳最多的是關於大海和森林的童話 。

對我來講,神話是伴著幽幽的爐火蓬勃出現的。在漫長的冬季裡,每逢夜晚來臨的時候,大人們就會圍聚在爐火旁講故事,這時我就會安靜地坐在其中聽故事。老人們講的故事,與鬼怪是分不開的。我常常聽得頭皮發麻,恐懼得不得了。因為那故事中的人死後還會回來喝水,還會悄悄地在菜園中幫助親人剷草。有的時候聽著聽著故事,火爐中劈柴燃燒的響聲就會把我嚇得渾身悚然一抖,覺得被燭光映照在牆面上鬼影憧憧。 這種時刻,你覺得心不是自己的了,它不知跳到哪裡去了。 當然,也有溫暖的童話在老人們的口中流傳著,比如畫中的美女每天在一個固定的時刻下來給窮人家做飯,比如一個無兒無女的善良的農民在切一個大倭瓜的時候,竟然切出了一個活蹦亂跳的胖娃娃,這孩子長大成人後出家當了和尚,成為一代高僧。這些神話和傳說是我所受到的最早的文學薰陶了,它生動、傳神、洗練,充滿了對人生間生死情愛的關照,具有悲天憫人的情懷。
也許是因為神話的滋養,我記憶中的房屋、牛欄、豬舍、菜園、墳塋、山川河流、日月星辰等等,它們無一不沾染了神話的色彩和氣韻,我筆下的人物也無法逃脫它們的籠罩。 我所理解的活生生的人,不是庸常所指的按現實規律生活的人,而是被神靈之光包圍的人,那是一群有個性和光彩的人。他們也許會有種種的缺陷,但他們忠實於自己的內心生活,從人性的意義來講,只有他們才值得永久的抒寫。
儘管我如此熱衷於神話的傳說,但我也迫切感覺到它們正日漸委頓和失傳。 因為生活正變得越來越疲沓、瑣碎、庸碌和公式化,人的想象力也相對變得老化和平淡。 所以現在儘管有故事生動的作品不停地被人叫好,但我讀後總是有一股難言的失望,因為我看不到一部真正的優秀作品所應散發出的精神光輝。
還有夢境。也許是我童年生活的環境與大自然緊緊相擁的緣故吧。我特別喜歡做一些色彩斑斕的夢。在夢境裡,與我相伴的不是人、而是動物和植物。白日裡所企盼的一朵花沒開,它在夢裡卻開得汪洋恣肆、如火如荼。我所到過的一處河灣,在現實中它是淺藍色的,可在夢裡它卻煥發出彩虹一樣的妖嬈顏色。我在夢裡還見過會發光的樹,能夠飛翔的魚,狂奔的獵狗和濃雲密佈的天空。
有時也夢見人,這人多半是已經做了古的,我們稱之為“鬼”的,他們與我娓娓講述著生活的故事,一如他們活著。 我常想,一個人的一生有一半是在睡眠中度過的,假如你活了八十歲,有四十年是在做夢的,究竟哪一種生活和畫面更是真實的人生呢? 夢境裡的流水和夕陽總是帶有某種傷感的意味,夢裡的動物有的兇猛有的則溫情脈脈,這些感受,都與現實的人際交往相差無二。有時我想,夢境也是一種現實,這種現實以風景人物為依託,是一種擬人化的現實,人世間所有的哲理其實都應該產生自它們之中。我們沒有理由輕視它們,把它們視為虛無。要知道,在夢境中,夢境的情、景、事是現實,而孕育夢境的我們則是一具軀殼,是真正的虛無。而且,夢境的語言具有永恆性,只要你有呼吸、有思維,它就無休止地出現,給人帶來無窮無盡的聯想。它們就像盛宴上酒杯被碰撞後所發出的清脆溫暖的響聲一樣,令人回味無窮。

我對文學和人生的思考,與我的故鄉,與我的童年,與我所熱愛的大自然是緊密相連的。對這些所知所識的事物的認識,有的時候是憂傷的,有的時候則是快樂的。我希望能夠從一些簡單的事物中看出深刻來,同時又能夠把一些貌似深刻的事物給看破,這樣的話,無論是生活還是文學,我都能夠保持 一股率真之氣、自由之氣。
0 2
北方的鹽
鹽那雪白的顏色常使我聯想到雪。在北方,鹽與雪正如雷與電,它們的美是裹挾在一起呈現的。
鹽與雪來歷不同。雪從天上來,而鹽來自地下。雪的成因與低沉的雲氣有關,而鹽的提取有兩種途徑,其一是多年礦物質的沉積,其二便是海水的凝結。不論它們來自天上還是人間,其形成都有一個浪漫的過程。雲與海水作為雪與鹽的載體,其氤氳與浩淼的氣質總令人浮想聯翩,誰能想到縹緲的雲會幻化出那麼輕盈、美麗、燦爛的雪花?誰能想到奔湧的海水會萃取出結晶的、閃著寶石一樣光澤的鹽粒?
雪來了,天氣越來越冷了。這時的北方大地寸草不生,看不到一抹綠色,所有的植物都成了寒冬的戰利品,被徹底地俘虜了,無聲無息。我童年記憶中的北方人的餐桌上,是看不到新鮮的綠色菜蔬的。不似現在,運輸的暢通和市場經濟的發達,數九天氣也能吃到來自南國的蔬菜。

鹽在漫漫寒冬中披著它銀色的鎧甲在北方閃亮登場了。它其實在秋天就亮著它的白牙向北方女人微笑了。秋季是北方人醃菜的時節,家庭主婦們把還新鮮的豆角、辣椒、芹菜、黃瓜、蘿蔔、芥菜等塞進形形色色的缸裡,撒上一層又一層的鹽,做成鹹菜,以備冬季食用。北方人愛吃的、一直以來被大張旗鼓醃製的酸菜,更是缺少不了鹽。鹽被白花花地撒向缸裡的時候,會發出簌簌的聲響,好像鹽在唱歌。在秋天,山間的蘑菇也露出毛茸茸的頭了,蘑菇除了曬乾外,還可以用鹽醃漬在罈子裡儲存起來,冬天時用清水漂出它的鹽分,吃起來味道仍是鮮美的。所以鹽在秋季是撒向北方土地的最早的雪,它融化了,融化在菜蔬最後的清香中。 如果你問一個北方人,你們的灶房裡什麼物件最多?我猜十有八九的人都會衝口而出:鹹菜缸!的確,醃酸菜的大缸,醃蘿蔔和芥菜的中等型號的缸,以及醃糖蒜和韭菜花的罈子等等,就像樂池上擺放著的形形色色的樂器一樣,你一進灶房它們就會撲入你的視野,並且在你不小心碰撞了它們的時候,為你奏出或沉鬱或清脆的樂聲。
鹹菜是北方人餐桌上的“正宮娘娘”,在寒風呼嘯的日子裡佔據著統治地位,因而北方人也較其他地區的人攝鹽量大,形成了口重的習慣,似乎不多加鹽的食物都是寡淡無味的。北方人對鹽有種近乎崇拜的心理,認為它是力量的化身,所以民間流傳著吃鹽長力氣的說法。那些靠力氣而生活的伐木工及家庭主婦,對鹽的青睞可想而知了。記得童年時看電影《白毛女》,看到白毛女在山洞裡因為多年吃不到鹽,而過早地白了少年頭的時候,鹽在我心目中還具有了烏髮的作用,這印象一直延續至今,根深蒂固。現代膳食講究低鹽少糖,這與北方人對鹽的巨大熱情是背道而馳的。北方人心腦血管的發病率遠遠高於江南,其氣候的寒冷與攝鹽過量無疑是兩大元兇。儘管如此,北方人對鹽仍然像對老朋友一樣緊緊相擁,人們並未將它當敵人一樣警惕著,雖然冬季可以從副食商場購得新鮮蔬菜,紫白紅黃地點綴著餐桌,但在餐桌的一角,總會有幾碟顏色黯淡的醬菜與之唱和著,有如一部歌劇在結尾時撒下的嫋嫋餘音,它們呈現著舊時陽光的那種溫暖與美好,令人回味。
當我們吃著醃製的醬菜望著窗外的雪花、聽著時光流逝的聲音時,濃雲會在深冬的空中翻卷,海水會在遙遠的天際湧流。而當我們為著北方的凍土上所發生的那些故事無限感懷時,淚水便會悄然浮出眼眶。淚水一定來自大海,不然它為什麼總是鹹的?!
因為有了寒冷,有了對寒冷盡頭的溫暖的永恆的渴望,有了對鹽那如同情人般的纏綿和依戀,我想 北方人的淚水會比南方人的淚水更鹹。
03
是誰扼殺了哀愁
現代人一提“哀愁”二字,多帶有鄙夷之色。好像物質文明高度發達了,“哀愁”就得像舊時代的長工一樣,捲起鋪蓋走人。於是,我們看到的是張揚各種世俗慾望的生活圖景,人們好像是卸下了禁錮自己千百年的鐐銬,忘我地跳著、叫著,有如踏上了人性自由的樂土,顯得是那麼亢奮。
哀愁如潮水一樣漸漸回落了。 沒了哀愁,人們連夢想也沒有了。 缺乏了夢想的夜晚是那麼的混沌,缺乏了夢想的黎明是那麼的蒼白。
也許因為我特殊的生活經歷吧,我是那麼地喜歡哀愁。我從來沒有把哀愁看做頹廢、腐朽的代名詞,相反, 真正的哀愁是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是可以讓人生長智慧、增長力量的。

哀愁的生長是需要土壤的,而我的土壤就是那片蒼茫的凍土。是那種人煙寂寥處的幾縷雞鳴,是映照在白雪地上的一束月光。哀愁在這樣的環境中,悄然飄入我的心靈。
我熟悉的一個擅長講鬼怪故事的老人在春光中說沒就沒了,可他抽過的煙鍋還在,怎不使人哀愁;雷電和狂風摧折了一片像蠟燭一樣明亮的白樺林,從此那裡的野花開得就少了,怎不令人哀愁;我期盼了一夏天的園田中的瓜果,在它即將成熟的時候,卻被早霜斷送了生命,怎不讓人哀愁;雪來了,江封了,船停航了,我要有多半年的時光看不到輪船駛入碼頭,怎不叫人哀愁!
我所耳聞目睹的民間傳奇故事、蒼涼世事以及風雲變幻的大自然,它們就像三股弦。它們扭結在一起,奏出了“哀愁”的旋律。所以創作伊始,我的筆觸就自然而然地伸向了這片哀愁的天空,我也格外欣賞那些散發著哀愁之氣的作品。
我發現哀愁特別喜歡在俄羅斯落腳,那裡的森林和草原似乎散發著一股酵母的氣息,能把庸碌的生活發酵了,呈現出動人的詩意光澤,從而洞穿人的心靈世界。他們的美術、音樂和文學,無不洋溢著哀愁之氣。比如列賓的《伏爾加河縴夫》、柴可夫斯基的《悲愴交響曲》,艾託瑪托夫的《白輪船》、屠格涅夫的《白淨草原》、阿斯塔菲耶夫的《魚王》等等,它們博大幽深、蒼涼遼闊,如遠古的牧歌,凜冽而溫暖。所以當我聽到蘇聯解體的訊息,當全世界很多人為這個民族的前途而擔憂的時候,我曾對人講,俄羅斯是不死的,它會復甦的!理由就是:這是一個擁有了偉大哀愁的民族啊。

人的憐憫之心是裹挾在哀愁之中的,而缺乏了憐憫的藝術是不會有生命力的。 哀愁是花朵上的露珠,是撒在水上的一片溼潤而燦爛的夕照,是情到深處的一聲知足的嘆息。可是在這個時代,充斥在生活中的要麼是慾望膨脹的嚎叫,要麼是麻木不仁的冷漠。此時的哀愁就像喪家犬一樣流落著。 生活似乎在日新月異發生著變化,新資訊紛至沓來,幾達爆炸的程度,人們生怕被扣上落伍和守舊的帽子,疲於認知新事物,應付新潮流。於是,我們的腳步在不斷拔起的摩天大樓的玻璃幕牆間變得機械和遲緩,我們的目光在形形色色的慶典的焰火中變得乾澀和貧乏,我們的心靈在第一時間獲知了發生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的新聞時卻變得茫然和焦渴。
在這樣的時代,我們似乎已經不會哀愁了。 密集的生活擠壓了我們的夢想,求新的狗把我們追得疲於奔逃。我們實現了物質的夢想,獲得了令人眩暈的所謂精神享受,可我們的心卻像一枚在秋風中飄蕩的果子,漸漸失去了水分和甜香氣,乾澀了、萎縮了。我們因為盲從而陷入精神的困境,喪失了自我,把自己囚禁在牢籠中,捆綁在屍床上。那種散發著哀愁之氣的藝術的生活已經別我們而去了。
是誰扼殺了哀愁呢?是那一聲連著一聲的市井的叫賣聲呢,還是讓星光暗淡的閃爍的霓虹燈?是越來越眩目的高科技產品所散發的迷幻之氣呢,還是大自然蒙難後產生出的滾滾沙塵?
我們被阻隔在了青山綠水之外,不聞清風鳥語,不見明月彩雲,哀愁的土壤就這樣寸寸流失。 我們所創造的那些被標榜為藝術的作品,要麼言之無物、空洞乏味,要麼迷離儻蕩、裝神弄鬼。 那些自詡為切近底層生活的貌似飽滿的東西,散發的卻是一股雄赳赳的粗鄙之氣。 我們的心中不再有哀愁了,所以說盡管我們過得很熱鬧,但內心是空虛的;我們看似生活富足,可我們捧在手中的,不過是一隻自慰的空碗罷了。
這個時代還需要神話嗎
在香港某大學,一天午後,我去黃子平先生的課上班訪。所謂班訪,就是座談。黃子平出了個題“好山好水好文章”,我落座後對了一句“廢水廢氣廢都城”,學生們笑起來。講演之前,我對學生說,我高考時,作文寫跑題了,因為我沒有抓住中心思想,得了最低分,所以我接下來要講的,可能會背離主題。
果然,一開始,我就信馬由韁地從童年所聽到的神話講起。我說,我生長的那個地方,是個小村子,非常寒冷,每年有大半年在飄雪。那時候不通電,沒有電視,冬天黑得早,我們吃過飯,就搬著小板凳,圍聚在火爐旁,藉著爐火的光,一邊喝茶一邊講故事。
說故事的都是老人,他們講的,大都是神話故事。什麼年畫中的姑娘每天從畫中下來,為貧窮的小夥子做飯;什麼趕考的秀才在夜晚的花園遇見花神,花神護佑秀才,使他中了狀元;什麼一對無兒無女的老人在種菜時,收穫了一個大倭瓜,把它切開,裡面竟然蹦出來一個活潑的男娃娃。
這樣的神話,使寒冬變得溫暖,使黑暗變得光明。當然,也有恐怖的神話,比如借屍還魂、狐仙害人一類的,但結局總會蹦出一個孫悟空似的聖人,能夠清除妖孽,懲惡揚善。可以說,我最早的文學啟蒙,就是這些神話。
我由此談到了自己的新長篇《額爾古納河右岸》,我說其中的一個情節,就是老人們講給我的,他們說那是一個真實的故事。當地有個無兒無女的獵人,有一次進山打獵,忽然看見一隻懷孕的狐狸。獵人很高興,因為狐狸的皮毛很值錢。獵人舉起槍,朝狐狸瞄準。然而未等他扣動扳機,狐狸卻像人一樣站直了,它抱著兩隻前爪,給獵人作個揖,叫著獵人的名字,說,某某某,我知道你好槍法!狐狸作揖已讓獵人手軟了,再加上它說的那句話,更是讓他心驚膽戰,獵人知道自己遇到了得道成仙的狐狸,連忙放下獵槍,跪下。狐狸轉身朝密林深處去了。
獵人回到家,把他的奇遇說給左鄰右舍的人聽,從此他放下獵槍,以種地為生了。獵人變成農夫後,日子過得安閒,他一天天老了。終於有一天,他平靜地過世了。在他的葬禮上,忽然來了一對如花似玉的姑娘,她們一身素白,為他弔孝。當地人都不認得她們。她們為農夫守靈,直到把他送到墓地。農夫入土後,那雙女孩突然間無影無蹤了。村裡人這才反應過來,那對女孩,一定是當年獵人放過的有身孕的狐狸,她是帶著她的孩子,為老人送終來了,以報答獵人當年的不殺之恩。

我從神話,又講到大自然,我覺得神話的誕生,離不開這樣的“好山好水”。我的文學,我的世界觀,與神話是分不開的。然而我剛講完,一個女生就舉手咄咄逼人地提問,說,來自東北的女作家,你講得也太誇張了吧,狐狸怎麼能開口說話呢!再說了,現在是一個科學的時代,這些神話都是糊弄人的,有什麼意義呢!她很激憤,彷彿我是一個賣狗皮膏藥的江湖騙子,愚弄了她。
我笑了笑,心平氣和地對她說,看你的年齡,也就二十歲上下的樣子。 你生長在香港這樣一個國際大都市,從小享受到的是豐富的物質生活。你眼中只有一個世界,這個世界是由摩天大樓、跨海鐵路、高速公路、汽車、電腦、電話構成的,你們所受的教育,使你對科學無比信賴。你們沒有可能聽祖輩人講故事,而書本的神話故事又不如時髦的流行讀物更能吊起你們的胃口。你們這一代人,既沒有聽神話的環境,也沒有接受神話的情懷了。所以,你們喪失了與另一個世界溝通的可能性。
我得感謝這位女生,她很坦率地講出了她這一代人的心聲。他們眼裡的神話,也許是克隆人、無土栽培的植物、奈米技術產品、太空梭、掌上電視。孟姜女哭倒長城,在他們眼裡一定是荒謬的;宇航員沒有發現月球有生命的跡象,那麼他們一定認為嫦娥奔月的故事也是荒誕的。總之,所有的神話,在“科學”的手術刀下,都經不起解剖。可是, 僅僅活在一個物質的世界裡,人難道不就成了一塊蛋白了嗎?

全球化、城市化的程序,在漸漸消解神話,大自然的退化,也在剝奪神話產生的土壤,我不敢想像,再過一個世紀,有多少神話會就此失傳?我們這個時代,難道真的不需要神話了嗎? 人類因為對萬事萬物有悲憫的情懷,所以才一路走到今天,我想如果有一天神話絕跡了,人類就到了消亡的邊緣。
也許我的一些話觸動了那位女生,她再次提問:你怎麼讓我們相信神話呢?
我說,人生對你們來講僅僅是開始,等你們將來年歲大了,想著自己的肉身會灰飛煙滅時,也許對神話就有認同感了。
在我眼裡,能給生靈以關愛,給大自然以生機,給人以善良的神話,是萬古長青的!
遲子建:藝術的淬鍊正如從童話到神話 遲子建:有一種煙火,可能深藏地下,又回到人間 遲子建:外賣小哥,是我們最溼潤的人間煙火 遲子建:我們時代的塑膠跑道 王宏圖丨《煙火漫卷》展現的善良與明亮
本文節選自
《遲子建散文》是原“中華散文插圖珍藏版”叢書中的一種,多年來得到廣大讀者的認可。這個選本收遲子建散文數十篇,較為全面地反映了作者的散文創作成就。
推薦閱讀
點選圖片即為購書頁面
遲子建 《煙火漫卷》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20年度“中國好書”
這是一部聚焦當下都市百姓生活的長篇小說,遲子建以從容洗練、細膩生動的筆觸,燃起濃郁的人間煙火,柔腸百結,氣象萬千。一座自然與現代、東方與西方交融的冰雪城市,一群形形色色篤定堅實的普通都市人,於“煙火漫卷”中煥發著勃勃的生機。
過了凜冽的寒冬,南下的候鳥就要北歸了。也不知什麼時候起,瓦城裡的人像候鳥一樣愛上了遷徙。一場疑似禽流感的風波爆發,令候鳥成了正義的化身。在瓦城人看來候鳥怕冷又怕熱,是個十足的孬種。可如今,人們卻開始稱讚候鳥的勇敢。小城看似平靜安逸,卻是盤根錯節,暗流湧動,城外世外桃源般的自然保護區,與管護站遙遙相對的娘娘廟都未曾遠離俗世,動物和人類在各自的利益鏈中,浮沉煙雲……
這部小說是根據1910年冬至1911年春在東北哈爾濱爆發鼠疫的史實創作的。小說描寫哈爾濱傅家甸地區的民眾在鼠疫來臨之時遭受的滅頂之災。特別著力於王春申、翟芳桂、翟役生、于晴秀、喜歲等普通民眾的描寫,官員於駟興、醫生伍連德等人物也都很有特色。小說內容密集、豐富,不張不揚、徐徐道來,如一幅暈染的風情圖,充滿小人物的悲歡哀樂。
《額爾古納河右岸》精裝版
《額爾古納河右岸》是一部描寫鄂溫克人生存現狀及百年滄桑的長篇小說,展示了弱小民族在嚴酷的自然環境和現代文明的擠壓下的頑強生命力和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以及豐富多彩的民族性格和風情。本書獲得第七屆茅盾文學獎。
中國北方蒼茫的龍山之翼,一個叫龍盞的小鎮,屠夫辛七雜、能預知生死的精靈“小仙”安雪兒、擊斃犯人的法警安平、殯儀館理容師李素貞、繡娘、金素袖等,一個個身世性情迥異的小人物,在群山之巔各自的滾滾紅塵中浮沉,愛與被愛,逃亡與復仇,他們在詭異與未知的命運中努力尋找出路;懷揣著各自不同的傷殘的心,努力活出人的尊嚴,覓尋愛的幽暗之火……
遲子建 |《寒夜生花》| 人民文學出版社
茅盾文學獎自一九八一年設立迄今,已近四十年。這一中國當代文學的*獎項一直備受關注。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大多在文壇耕耘多年,除了長篇小說之外,在中篇小說、短篇小說和散文等“短”題材領域的創作也是成就斐然。為更完整地呈現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的綜合創作實力、藝術品位和思想內涵,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遴選部分獲獎作家的中篇小說、短篇小說和散文的經典作品,編成集子,薈萃成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短經典”叢書,得到了專家和讀者的一致好評。
《寒夜生花》一書是第七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遲子建的“短”作品精選集,收錄了《秧歌》《向著白夜旅行》《燈祭》《飛向泥土的箭》等經典短篇小說和散文篇目。
編輯 | 巴巴羅薩 主編 | 魏冰 心
圖片 | 《白日焰火 》
找記者、求報道、求幫助,各大應用市場下載“齊魯壹點”APP或搜尋微信小程式“壹點情報站”,全省600多位主流媒體記者線上等你來報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