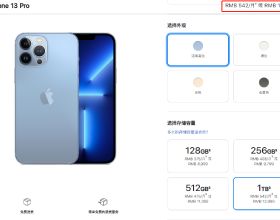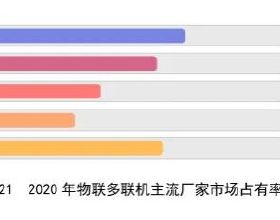光明日報記者 王建宏
有位沿海城市的朋友,看到大篇幅的“西海固”報道,深為觸動,遂在電子地圖中輸入查詢,竟一無所獲。
“西海固”三個字,就是這麼奇特——在聯合國很有名,地圖上找不到,卻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貧困的代名詞。
西海固到底在哪裡?
西海固最初為寧夏南部山區西吉、海原、固原的合稱。1953年至1955年,在這片地域曾短暫設立過“西海固回族自治區”。後來,隨著行政區劃的變化,西海固所指的範圍也幾經變遷,逐漸成為寧夏中南部9個貧困縣區的代稱,佔據了寧夏地理版圖的65%。
劉克瑞的老家,就在固原市原州區張易鎮毛套村,那裡是地地道道的“舊西海固”。他不太善於表達,似乎根本說不出“最不適宜人類生存的地方”這句話。但是,他說得毫不遲疑,流利而順暢。1972年,他出生的前一年,他的老家就因為這句話在聯合國出了名。

在實施全域封山禁牧前,無序的放牧曾給寧夏的生態造成巨大破壞。生態和生存一度成為西海固走不出的怪圈。固原市委宣傳部供圖
蔚藍,可以是大海,可以是天空,但也可能是噩夢的顏色。很長時間裡,只要聽到有人讚美老家的天空特別藍,劉克勤都覺得渾身不得勁兒。天越藍,太陽越大,就越不下雨。西海固人關於旱的噩夢,就是藍色的。就連民歌“花兒”都唱出了焦渴:“溝岔裡的水乾了,我的嗓子幹得冒火了。”
在西海固的大部分地方,水代表著財富,有無水窖是衡量貧富的重要標準。由於缺水,孩子們的臉是灰撲撲的,頭髮總像稻草一樣蓬在頭上。上門提親,只要男方家裡有兩眼水窖,那多半是門好親事。生活在這裡,會有一種強烈的感覺:世上最大的不公,就是出生地的不同。
在中國地圖上,寧夏猶如瀚海中游弋的一葉扁舟,南北狹長,中部略寬。黃河從寧夏小舟的左舷中部切入,自西南向東北,北部平原溝渠縱橫、稻香魚肥、瓜果飄香、風光秀美,而超越“半壁河山”的中南部則是丘陵起伏的黃土高原,以及被毛烏素、騰格里兩大沙漠夾擊的荒漠戈壁。
西海固之困,歸根結底源於人與水、土等自然資源的錯配。“人隨水走,水隨人流”,對錯配的資源重新最佳化配置,乃終結之道。用一句通俗的話,就是“搬出去”。
上世紀八十年代,劉克瑞的大哥劉克勤成了寧夏第一代“移民”。自此之後,寧夏在近40年時間裡,分6個階段,累計搬遷123萬人。其間,除了考上農校的二哥外,劉克瑞的三哥、四哥和六弟相繼成為百萬大移民的一分子。
繼秦漢時期的軍事移民、唐宋時期党項民族的兩次內遷、元代的大規模政策性移民、明清兩代的移民開發後,百萬大移民成為這片區域最大規模的人類遷徙,涉及寧夏總人口的六分之一。
遷出百萬人,換得千山綠。
百萬大移民以對貧困的“減法”,實現生態的“加法”,破解了“生存”與“生態”的雙重困境。在移民主要遷出區固原市,降雨量由退耕還林前的年均200多毫米,增至600毫米左右,部分縣區達到1000毫米。
“曾經連個野豬毛都沒見過,如今時常被野豬禍害!”這是西海固生態改善後,人們有點“凡爾賽”的表達,看似在抱怨,神情中卻透著驕傲。
各種絕跡的野生動物重新迴歸,生態產業和生態旅遊逐漸興起,成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最好註解。在跳出“越窮越墾,越墾越窮”的惡性迴圈後,貧困代際傳遞的慣性力量日漸式微。

移民從大山搬出來,集中搬遷至近水靠路的移民新村。固原市委宣傳部供圖
西吉縣的“西”,即西海固的“西”。龍王壩,是這個縣的典型村莊,揹著山、抱著山、山外套著山,丘荒禿嶺,望不盡的蒼涼。人挑驢馱,為吃水來回走上兩個鐘頭,是一代代“龍王壩人”難以抹去的集體記憶。
多年後這個初冬,站在高處俯瞰依偎在六盤山懷抱中的村落,夏日旺盛的草木呈現一種冷冽肅殺之氣,白牆藍瓦的民居錯落有致,一幅生態畫卷拓印於黃土高坡上。在這個村,直接從事旅遊業的就有300人,加上配套行業,帶動了800多人就業。全村近年累計接待遊客300多萬人次,旅遊收入超過4億元。
劉克瑞遷入的地方叫紅寺堡,後來成為全國最大的易地生態移民集中安置區。在這裡,在閩寧鎮,在大戰場……在諸多縣內移民安置區,黃河水經現代工程技術,提灌進焦渴大地,人、水、土資源的最佳化組合,使昔日的沙丘荒漠成為阡陌縱橫的綠色家園。

羅山腳下的紅寺堡是全國最大的易地生態移民安置區。紅寺堡區委宣傳部供圖
移民搬遷這些年,層林染綠了山頭,自來水接到了灶頭,光纖寬頻扯到了炕頭,致富路連通了外頭,公交通到了村頭……人與自然的對抗、博弈與和解,在戈壁灘上開闢了一個新家園,也還原了一個山清水秀的遷出區。
隨著西海固從一個地理空間概念,演化為一種自然與人文融合的地緣標識,其外延也包括了劉克瑞現在的新家——紅寺堡。只不過,如今的西海固,已是一個全新的西海固。
《光明日報》( 2021年11月28日10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