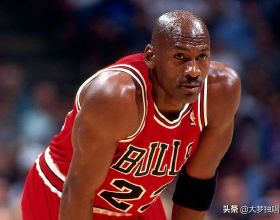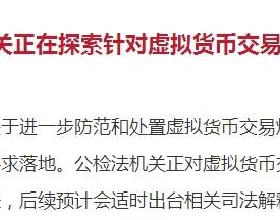□趙瑞峰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正月,康熙皇帝沿京杭大運河第六次南巡,二月經行山東境內的泇河,途次(旅途中住宿的地方)臺兒莊。當時正在滕縣任教、年近五旬的嶧縣人李克敬,連夜收拾行囊,小心帶上早已寫好的詩稿,馬不停蹄地朝臺兒莊而來。此行他是想趕早將詩呈獻給好像專門為他而停留的康熙皇帝。
李克敬,光緒三十年《嶧縣誌》有傳,然而稍嫌簡略;據縣誌所錄李克敬好友唐建中所撰《翰林院編修李克敬墓碑》(以下簡稱《墓碑》):“公諱克敬,字子凝,號小東,行四……生而穎異,五歲能誦尚書。八歲了五經,十歲能屬文賦詩,弱冠已為通儒,補博士弟子員。才滿山左,久且滿天下……公生於順治己亥,雍正丁未卒於官,享年六十九歲。”李克敬雖有才如此,但在52歲之前屢試不第,名場坎坷,甚不得意。舉業不就,只好和那些科考頻遭失敗計程車人一樣,走設帳授徒之路,做了西席先生。李克敬既“才滿山左,久且滿天下”,因此四方之人慕名爭相延聘,徐州、曲阜、滋陽等地都留下他授徒的足跡。他“教人,善於獎誘”,其門下弟子“皆卓有成就,掇巍科,膺祿仕”,但這反過來也加重了他科場失意之感。
據《嶧縣誌·李克敬傳》:“同郡翰林顏光斆(曲阜三顏之一),視學浙江,延之使代衡幕中,所賞拔皆一時之名士。至今兩浙戶祝顏公稱賢學使,克敬左右之力為多。”可見李克敬不僅才華過人,辦事能力也不一般,可謂顏的得力助手。至於賓主相得,顏對其倍加器重,那是自然。儘管如此,看其收錄在縣誌寫於這一時期的詩歌,那種科考不遂的隱隱心痛和牢騷不平,還是不可抑制地顯露出來。
康熙南巡圖
如果沒有康熙皇帝的最後這次南巡,李克敬又無法適逢其會,則其恐怕多半也會跟稍早於他的蒲松齡一樣,功名不就,便設帳授徒,間或短暫作人幕席,老則歸鄉,以著書終其一生。但康熙皇帝的這次南巡,讓他得機獻詩,從而時來運轉。其實在四年前,即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皇帝第四次南巡時,曾駕過泇河,於臺兒莊亦作短暫停留。只不過那時李克敬受聘遠在外地課徒,無緣獻詩,只能在“已是蹉跎過盛年,忍把愁鞭逐日去”的低沉歌吟中等待機會。
李克敬獲悉康熙皇帝南巡將至臺兒莊,又熟悉清廷規定——皇帝出巡各地,當地要組織文士碩儒敬獻詞章,歌功頌德,李克敬心情激動難抑。對欲以“蕭然布衣士,一朝動帝王”的他來說,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為此他調動全部的文學才華,閉門構思,精心結撰了《皇雅》和《聖頌》兩篇詩,以供呈獻。
《皇雅》共八章六十四句,茲節選其中兩章:
承天撫世,稽古帝王,書契以來,未有穆穆我皇。軼殷越周,流虞漂唐,三後在天,配之彌光。(第一章)
穆穆我皇,其道配天,藹藹如雲,奫奫如淵。兆民遊之,春草露鮮,洋洋洩洩,不能言其然。(第二章)
《聖頌》一章四十句:
皇矣聖帝,亙古一君,治軼頊嚳,德邁華勳。乃神乃聖,允武允文,詩成雅頌,筆追典墳。廟算莫遁,威服無垠,極地極天,悉主悉臣。含生之類,莫不榮欣。軫念東國,饑饉薦臻。輟漕賙賑,如救溺焚,三年不賦,以蘇斯民。遣吏往脯,爾飢爾呻,還爾井裡,勿嗟離群。出之寒谷,煦以陽春,奪諸斯命,賜之形神。富而教之,禮化絪縕,於變無跡,油油其醇。睿慮猶廑,省以時巡,瓊哉至德,開闢未聞。歡祝雷動,齊壽蒼旻,億萬斯年,沐我皇仁。
這兩篇依古雅頌之體而作的詩思想難免庸俗,卻也氣格不凡,詞采斐然,表現了李克敬的確過人的文學才華。這兩篇詩和詩前《南巡雅頌》序收錄在《嶧陽雲門李氏族譜》中。
臺兒莊古城夜色
李克敬一路風塵僕僕地趕到臺兒莊泇河行在,即將兩詩獻上。關於他呈詩的具體情形,因無文獻可徵,無從得知;李克敬似亦無詩記之,令人不解。《墓碑》謂:“時獻詩賦者六七百人,進呈二十一卷,欽拔(李克敬)第一。”至於這個獻詩的結果,李克敬究竟是當天便知還是隔日才知,雖無相關記載,倘依情理推測,也不難知道當為後者。因“時獻詩賦者六七百人,進呈二十一卷(約兩千餘篇)”,即使由皇帝身邊掌院學士先自從中篩選評定優秀者,再進呈御覽以定甲乙,也斷非一日可辦。李克敬家在六七十里路之外的嶧縣坊郭社,回家坐等訊息固不無可能。然其急於第一時間欲知曉結果的心理,勢不允許他返家,只能就地在臺兒莊暫住,靜候訊息。當時泇河“緣堤列肆”,商賈迤邐,吃住都很方便;風景也不錯,“鱗鱗瓦屋俯澄波,畫舫樓船絡繹過”“一夜漁火,歌聲十里”,閒來逛逛,不會有無聊之感。
李克敬究竟沒有白等,“欽拔第一”,這正是他渴望得到的結果。然而,拔得頭籌並不等於科考中第,一時也看不出有多大實惠,但能得到皇帝青睞,身價則陡然倍增,一朝名傾天下,朝廷內外一些官員則爭相與之交接。其中康熙皇帝近臣文淵閣大學士陳廷敬與其子侍讀學士陳壯履“前後遣人迎(李克敬)至澤州(今山西晉城,二陳老家),至屬校其文集”。這些官員對後來李克敬的科考獲第想來不無影響。
臺兒莊運河故道(孫南邨攝影)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李克敬應鄉試,一舉奪魁。七年後(1715年)已56歲的李克敬赴京,應會試、殿試聯捷,館選翰林院庶吉士。時距李克敬泇河獻詩已有八年,康熙皇帝猶記其名,召陛前與之交談,以此得奉命入值南書房,至此可謂功成名就。此時的李克敬再也不會寫那種“金闕既無分,玉京名相望”不無牢騷情緒的詩句。但“初入翰林,名噪甚”“名隨之,謗亦隨之”,等待他的不免是譭譽交加的宦海生涯。面對互相傾軋的官場險惡,李克敬萌生激流勇退的想法,便以養親為由,上書辭官,獲准。這恐怕是當初泇河獻詩和後來官場初得意時的李克敬所不會想到的。至於其後來複出補散館,授以翰林院編修,編撰國史,已是後話,不再敘述。
除了這次專門到臺兒莊泇河獻詩,李克敬此前至少有兩次經過臺兒莊,一次是為顏光斆延請赴浙做幕僚,自臺兒莊登船南下,再次就是結束幕賓生涯沿運河北上返鄉在臺兒莊舍船上岸。但那只是匆匆過客而已,不會留下特別的印象。不料幾年之後的臺兒莊之行竟成了決定他人生命運的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