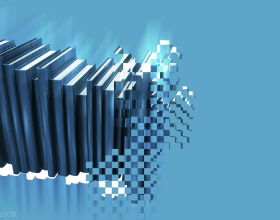上篇
儘管賀綠汀先生“躲”進了華東醫院,儘管這個以給高階幹部看病而聞名的醫院如何“森嚴壁壘”,但是,九十歲的賀綠汀卻躲不過追蹤而來的問候、祝福和鮮花!這位曾寫過無數精彩樂章,並以一曲《游擊隊歌》而名震天下的作曲家,這回是絕對無法再“遊擊”到別處了。
賀綠汀今年整整九十歲了,滄桑風雨的九十年!
按照中國人做虛歲大壽的慣例,去年,賀老先生的祝壽活動可謂是“轟轟烈烈”。一場“賀綠汀音樂作品演奏會”,讓人聽了,就彷彿跟著音樂走路,走過了數十年的中國歷史,有悲壯,泣而無聲;有狂歡,喜形於色。有諸多的舊雨新知,尤其是無數桃李弟子簇擁而至,他實在是很高興,雖然,也累。所以,今年近7月20日生日時,他便不事聲張地“躲”進了醫院,就像一個“老游擊隊員”。
可是,他的“戰略”“戰術”,絕對逃不過熱愛著他的人們的眼睛。他們不屈不撓地帶著鮮花和歡聲笑語來了。於是,他的病房,不可避免地成了歡樂大世界,成了花房……
在這一天的同一時刻,在北京皇冠假日飯店的藝術沙龍里,也聚集著一批帶著歡聲笑語來的人們。他們用樂器,用歌聲表達著自己。從“嘉陵江上”的“百靈鳥”,到“晚會”上的“搖籃曲”,一曲“幽思”的“牧童短笛”,訴說了上海與北京相距遙遠的“怨別離”……
感謝現代化的通訊裝置,得以使北京的聲音熱線傳真給了病房中的賀綠汀。而賀老的答謝,又乘著電波的翅膀,飛臨首都的上空。他深謝關心他的人們,說:“大家冒著酷暑,為我賀壽,實不敢當……”
許多年前,年輕的賀綠汀因革命而被投入監獄。他在獄中曾口占一首《浣溪沙》以言志,上闋的末一句是:“不知何處是吾家。”下闋的第一句是:“好夢有情來歡迎。”今夜,在賀老的夢中,在醫院做的這個夢中,有那樣多的愛戴者陪伴,他還能找著回家的路麼?
他的家,空空的了,像一隻溫暖的巢,等著他的歸來。滿院子的綠蔭和蟬聲,還有他所鍾愛的四季鮮花,都在等待著已邁開人生第九十個年頭之步的老人。
他的失聰,使他一直的形象是費力地戴著助聽器,認真地傾聽著別人的訴說。此情此景,讓人感動。他過去享有的“硬骨頭”綽號,依然緊隨著他,形影相隨。他還是不平則鳴,用那帶有辣椒味的湖南普通話。他依然酷愛音樂,而對酒吧音樂堂而皇之的泛濫感到憤怒。他就是他。或許你可以說他近乎偏頗,但這種執著,卻能讓人感受到一種人格上的分量。
賀綠汀最關心的,是國家大事。1988年時,他曾在某次會上誠懇地說:“我老了,我要死了。行動不方便了。我要退出政協常委,一退到底。政協不能儘讓八十、路都走不動的人來幹,要讓能幹實事的人來幹。我不能尸位素餐!”可是,他並沒有從此“躲”進小樓成一統。他每天聽新聞廣播,讀多種報紙,他在政治上依然敏銳。他不僅是個成功的音樂家,而且,還是中國共產黨中有著六十九年黨齡的老同志,所以,他受到黨內外的廣泛尊重,應當是可以理解的。
賀綠汀每天堅持寫回憶錄和寫日記,而這一切,無疑和他所奉獻給後人的音樂作品一樣,將成為他生命的延續。他最近在重讀唐詩宋詞,還在讀一本歷史回憶錄,這兩者,都使他浮想聯翩。
“我們都是神槍手,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我們和賀老一起消滅各種敵人,包括病魔。“我們都是飛行軍,哪怕那山高水又深”,我們和賀老將唱著歌行軍,在人生旅途愈走愈遠,愈堅定不移……
上海的夜空,今天是一張樂譜,星星是流動著的不朽旋律。(1993.7.20)
下篇
1930年1月2日,江蘇高等法院高字第359號刑事判決書主角“賀如萍”在南京刑滿出獄。四顧茫茫,兩手空空,幸好在徐州任教的侄子賀滌心寄到三十元,他得以有錢買車票,東去上海。賀如萍,即賀綠汀,這一年,二十七歲。
據史中興《賀綠汀傳》,賀綠汀到上海的第一個住處,是在甘世東路(今嘉善路)崇仁裡一家小店的樓上。這是他在湖南嶽雲學校時期同學劉已明以每月六元租住的一個地方。劉已明在老家做了幾年音樂老師,帶著所賺的二百元,想報考國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他鼓勵賀綠汀也一起報考。
目前,對賀綠汀人生軌跡有清晰描述的,一是史中興出版於1989年的《賀綠汀傳》,另一是賀綠汀女兒賀逸秋、賀元元出版於2003年的《我的父親賀綠汀》。前者在傳主去世前十年出版,相信素材採訪起始應更早,故《賀綠汀傳》得益於傳主本人回憶應是確信的。後者是傳主女兒,雖然出版稍晚,但所寫史實也值得重視。
2021年6月12日,我從自忠路沿復興中路一路向西步行至嘉善路,實地探訪崇仁裡。崇仁裡沿馬路一排二層建築還在,一樓仍以各種小店為多,門牌號碼從55至81號。崇仁裡的門牌在其間,為69弄。門頭尚在,只是應該有“崇仁裡”三字的門額被白石灰覆蓋,空空如也。與弄堂口幾位納涼的居民攀談,他們大約五六十歲,尚能記憶早年那一排小店中有藥店、成衣鋪、老虎灶等等。令我比較意外的是,他們居然都不知道嘉善路69弄另有大名“崇仁裡”。
關於劉已明的住處,賀逸秋所說與史中興不同:“父親出獄後,得到在徐州當中學教員的侄子的資助來到上海。父親找到在上海音樂專科學校學習的岳雲藝專同學劉已明,劉已明在上海今岳陽路建國西路口一個裁縫店的樓上租了一間小房子,父親就在他那裡睡地板。”史說“甘世東路(今嘉善路)崇仁裡”與賀逸秋說“今岳陽路建國西路口”,相距稍遠。但賀逸秋所說也沒錯,因為《賀綠汀傳》中說了:“劉已明準備考試,又把家搬到了建業裡。賀綠汀也住了過去,把買菜、做飯的活兒包了下來。”
賀逸秋說的“今岳陽路建國西路口”正是建業裡,只不過跳過了甘世東路(今嘉善路)崇仁裡。
劉已明本人在《憶綠汀在上海》一文中,對往事的回憶或許更細緻:“不久,綠汀兄找到了我的住地,我既驚奇又欣喜地瞭解了他的不幸遭遇,原來他才從南京監獄裡出來,生活困難。我毫無考慮地邀他同住、同吃、同學習,並另租了一間大一點的房子;我記得房子租金每月為光洋6元。又租了一架鋼琴,每月租金10元。我每週去學校上幾門理論課,上兩次鋼琴課。綠汀兄每天在房裡練習鋼琴、讀書、看報、做飯等等。”
賀綠汀對那一段也有文字記錄,但簡略:“2月到上海借住難友劉炳華處,時湖南嶽雲藝專同學劉已明來滬報考上海音專,我即遷住他處,並在西門路西門裡私立小學當教師。這一年我寫了《小朋友音樂》與《小朋友歌劇》兩本書,由北新書店出版,得了一筆稿費,有了點錢,便準備投考上海音專。1931年2月考入音專,選學作曲及鋼琴,同時在另一處私立小學任教以維持生活。”
賀綠汀從劉已明處搬走的下一個住處,是西門路(今自忠路)西門裡4號。他在一傢俬立小學找到了工作,月薪25元。這個小學校名,《賀綠汀傳》明確為“上海小學”,賀逸秋則將其稱之“西門小學”。
賀逸秋說:“後來在西門裡有個西門小學招聘教師,父親又去應聘。校長叫瞿伯華,租了兩座弄堂房子辦私立學校。學校只有三位教師,他同意父親應聘,讓他當初級班的教師,每月工資25元。這樣,父親就有了職業,並從劉已明處搬出,住在學校曬臺上的閣樓裡。”
西門裡的門牌,是自忠路原380弄,現已拆除,原址變身為一個叫“華府天地”的高檔樓盤。西門裡的舊時模樣,大約與一路之隔尚且存活的西成裡、豐裕裡相似。西門裡故事多,如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期間,周恩來常到此開會;張大千昆仲居住在17號;艾青與力揚從杭州到上海,最初也是在西門裡安身的;胡也頻被捕後,沈從文將懷孕的丁玲從原住處遷移到西門裡的李達、王會悟夫婦家中……
西門裡之後,賀綠汀的下一個住所是哪裡呢?賀逸秋回憶:“1930年夏天,父親報考上海音專小提琴科未被錄取。同年9月,三伯來到上海,為父親添置了一些衣物和日用品,併為他在甘世東路租了一間亭子間。於是父親辭去了小學教員一職,專心準備考試。”賀綠汀在次年春季進入音專,成為鋼琴與和聲兩門課的選課生。如此,賀綠汀與甘世東路的緣分就有了兩次。這兩次對他而言,都有著紀念意義:第一次是借同學光,在上海落了腳,也在此確定選擇音樂作為終身事業。第二次,則目標更明確,在這裡複習應考,並遂願。
賀綠汀在1931年春天考取音專後,姜瑞芝姐弟從邵陽來到上海。《賀綠汀傳》:“曾和他並肩參加火燒英商煤油庫的積極分子姜瑞芝,和弟弟一起,也到上海報考音專來了。賀綠汀為她補習和聲和鋼琴。會同三哥和他們在巨潑來斯路(今永福路)62弄美華里15號合租下一所三層樓的房子:三樓是姜瑞芝姐弟,二樓是一位浙江同學,他三哥住底層,他住二樓亭子間。”
這一段訛誤較多,需要訂正。首先,巨潑來斯路並非“今永福路”,而是“今安福路”。永福路在法租界時期名稱是古神父路。兩者相去不遠,但卻是兩條不同的馬路。其次,說美華里在62弄也是錯的。因為,無論是巨潑來斯路時期,或是後來的安福路,62弄都是德安裡的總門牌。只是德安裡現在已在城市改造中成為永遠的過去時。原處,矗立的是一幢有著玻璃幕牆的高樓。
但,巨潑來斯路或安福路,是確有美華里的,門牌是安福路191弄。從路口北進向南,有不寬的道路,直通弄堂深處。弄底,有三排共二十二幢石庫門房子,15號在第二排最靠裡的位置。大約在很長時間裡,15號西面的窗外,應該是一塊不大不小的菜園。
據1931年5月《新建美華里召租》廣告:“法租界善鍾路西首、巨潑來斯路南首、麥琪裡西首有三層樓石庫門房屋多幢。弄口裝有鐵門,屋身堅固,自築丈寬馬路。每間房屋之內,裝有抽水馬桶,且空氣清新,日光充足,離善鍾路電車站甚近,交通便利。租金每幢每月自三十元起。如合意,請向本里第一衖末家接洽。南京路四十九號美華地產公司啟。”
賀逸秋說:“1931年三伯因賣了兩部書的譯稿,有了幾百元的稿費,在上海美華里15號租了一幢三層樓的房子。三伯住在一樓,父親當時已經在上海音專讀書,就搬來住在二樓的亭子間。我母親那時還沒有和父親結婚,她和我小舅舅也在上海音專學習,姐弟倆租住在三樓,其餘的房間出租。那時的生活比較安定。但想不到禍從天降,當年5月下旬,來了幾個‘包打聽’,拿出一個信箋,上面寫著:‘賀××共產黨中央住機關’一行字,就把三伯抓走了。”
據《賀綠汀傳》:“後來三哥還是判了六個月徒刑。同時被捕的一個同志也判六個月徒刑。”賀逸秋的“三伯”、賀綠汀的“三哥”賀培真原系中共黨員,但在美華里時期,已無組織關係。所以,“包打聽”以“賀××共產黨中央住機關”為名抓人顯然是不確的。最後判刑僅六個月,應該也不是以“共產黨中央住機關”的罪名量刑的。據說,晚年賀綠汀一直想透過檔案系統弄清當年究竟是誰向當局告密,但無果。

賀綠汀與賀培真在泰安路76弄4號家中合影(1956年春,上海)
這件事產生的最直接的後果,應該是美華里15號的房租無以為繼。至於賀培真被抓時間,賀逸秋說是“5月下旬”,不確。因為《賀綠汀傳》說:“一·二八”淞滬戰爭爆發時,“三哥還在服刑”。以刑期往前推,不應該在“5月下旬”。
賀培真被抓時間及同時被抓者是誰?1931年7月19日《申報》有報道:
“浙滬警備司令部、日前得據密報、謂現有反動份子多人、匿跡法租界巨潑萊司路美華里十五號門牌、請速派員往捕等情、當由偵緝處探員楊鳳歧、持文逕投法捕房特別機關、會同中西包探、按址拘獲賀文麟、葉蘭山兩名、並抄獲反動檔案多種、一併帶入捕房、轉解司令部訊究。”
如此,賀培真(即賀文麟)被抓時間應該在7月中旬,同時被抓者是葉蘭山。葉蘭山後來也被判刑六個月,再往後,下落不明。不知道葉氏是否就是《賀綠汀傳》中所言及租住在美華里15號二樓的“浙江同學”?對此,賀培真、賀綠汀昆仲似無回憶。
關於這段時間的經歷,賀綠汀在1934年11月曾著文發表:
“1931年春入國立音樂專科學校隨黃今吾先生學和聲,隨查哈羅夫先生學鋼琴。1932年中日‘一·二八’戰事發生,離校到武昌藝專任音樂理論教師,同時翻譯英國音樂理論家E.Prout所著《和聲學理論與實用》。1933年再回母校,正式以理論為主科,隨黃今吾先生學作曲。今年6月父親逝世,故鄉大饑饉,三哥亦因病停止他的職業去休養。為著生活,也許會要暫時停學罷,我的生活路程永遠是曲折的。”
賀綠汀與姜瑞芝姐弟在1932年2月離開上海,姜氏姐弟因音專停課、賀綠汀則應私立武昌音專聘。他與姜瑞芝,當年暑假期間在邵陽老家結婚。等他再次回到上海,已是1933年的秋天。
1934年春天,他從拉都路(今襄陽南路)敦和裡搬到了雷米路(今永康路)133號樓上,樓下是家木工油漆店,“咯吱咯吱的鋸木聲和叮叮咚咚的鐵錘敲擊聲終日響個不停”,隔兩個門牌,139號的樓上住著三位積極參加左翼文化運動的青年:陳荒煤、張庚、呂展青。呂是賀在音專同學,他們為了生計,還曾一起承包過某個私立小學的教學。
呂展青即呂驥,後來成為新中國音樂領域的領導人。在第一屆文代會上,呂驥是中華全國音樂工作者協會主席,賀綠汀是副主席(另一位副主席是馬思聰)。當然,這是後話。繼續回到1934年,有一次呂展青被當局盯上,賀綠汀幫忙到139號樓下的菸紙店打聽有無呂氏信件,因此也被盯上。所以,賀綠汀夫婦當晚就搬家到了拉都路(襄陽南路)84號王春生裁縫店的樓上。
這一年的暑假,賀綠汀看到俄裔美籍作曲家、鋼琴家齊爾品“徵求有中國風味之鋼琴曲”的啟事,他在現在已煙消雲散的84號樓上,寫出了三首鋼琴小品《牧童短笛》《搖籃曲》和《思往日》。這成為賀綠汀的成名作和代表作。賀逸秋回憶:84號樓上的小屋,“矮小且不通風,夏天熱得不能進屋。父親只好一大早趁太陽還沒有出來,從曬臺爬到屋頂上,坐在屋面上寫作。”
我對賀綠汀幾處舊居的探訪,其實就是田野考察。透過對實地觀察、與居民交談,查閱存世的歷史文字,將兩個時間中空間進行比較、疊印、組合,以企儘量恢復傳主活動的歷史現場。
對賀綠汀舊居,我先後四次走訪了泰安路74弄4號(現存)、安福路(原巨潑來斯路)美華里15號(現存)、自忠路(原西門路)西門裡(不存)、嘉善路(原甘世東路)崇仁裡(現存)、襄陽南路(原拉都路)敦和裡(現存)、永康路(原雷米路)133號(現存)、襄陽南路(原拉都路)84號(不存)和岳陽路、建國西路口(原祁齊路、福履理路)的建業裡(不存)。
1930年9月,賀培真從河北到上海,曾住“拉斐德路幸福裡”,《賀綠汀傳》說,此時的賀綠汀,為了全力複習應考,辭去了西門裡小學教職,搬進“拉斐德路幸福裡”與三哥同住。不久,為了讓賀綠汀有個更好的學習環境,賀培真在甘世東路為賀綠汀另租了亭子間。拉(通譯為“辣”)斐德路,即今復興中路上,並無“幸福裡”地名。距復興西路不算遠的華山路1420號,倒是有個幸福裡,但無當事人確認,不敢妄定。
岳陽路、建國西路口(原祁齊路、福履理路)的建業里名字還在,只是該處建築在大部拆除後,又仿照原有外貌復建了起來,仍以“建業裡”命名。究其內裡,實際上只是姑存其名而已,今“建業裡”已非原“建業裡”了。所以,在“現存”和“不存”的選項中,應選“不存”。

上海泰安路76弄4號賀綠汀故居(吳霖攝於2021年5月5日)
新中國成立後,賀綠汀一家大約在上世紀50年代末起,一直住在上海泰安路74弄(又稱“亦村”)4號的花園別墅裡。這是賀綠汀一生安居最久的住址,直到1999年4月去世。(2021.6.14.端午)
責編:孫小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