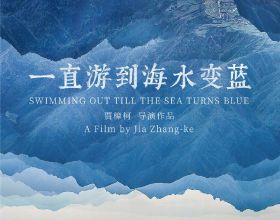由魯迅文化基金會、中國美術家協會版畫藝術委員會、中央美術學院、南京市文化和旅遊局主辦的“第二屆魯迅版畫大展”在南京金陵美術館展出,觀眾在參觀。宋寧攝\光明圖片

張夢陽 1945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紹興文理學院魯迅研究院“鑑湖學者”特聘講座教授,研究方向為魯迅及中國現當代文學。著有《魯迅全傳·苦魂三部曲》《中國魯迅學史》《魯迅的故事》《阿Q——100年》等。
本報教育部主辦
今年是魯迅誕生一百四十週年,同時也是他最重要的作品《阿Q正傳》發表一百週年。
《阿Q正傳》發表了一百年,阿Q那滑稽而可憐的苦臉在人們心中活了一百年,關於阿Q的閱讀與論爭也進行了一百年。由《阿Q正傳》的閱讀史、爭論史,我以為,可以總結出五種魯迅作品讀法。
深讀法
十年前我在《光明日報》“光明講壇”上發表過一篇講座《深讀魯迅 學會思考》,在青年讀者中反響很好。今天還要首先強調深讀,這是因為,《阿Q正傳》看似與魯迅的其他作品不同,有些地方像通俗小說,但實際上含意最深,它最需要深讀。
從作家的創作本意與知情者的本初評論出發,是作家、作品研究的正確途徑。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阿Q典型研究主要是沿著這一途徑向前進展的。
從1921年12月4日起,《阿Q正傳》在《晨報副刊》連載,每週或隔週刊登一次,剛登到第四章時,當時主編《小說月報》併兼記者的沈雁冰(即後來成為現代文學巨匠的茅盾),就以大評論家的慧眼,洞察到剛問世四章的《阿Q正傳》的偉大價值,在回答讀者疑問時明確指出:
至於《晨報副刊》所登巴人先生的《阿Q正傳》雖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來,實是一部傑作。你先生以為是一部諷刺小說,實未為至論。阿Q這人,要在現代社會中去實指出來,是辦不到的;但是我讀這篇小說的時候,總覺得阿Q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國人品性的結晶呀!我讀了這四章。忍不住想起俄國龔伽洛夫的Oblomov了!
茅盾這段對《阿Q正傳》的最早評語,實質上已經包含了後來百年間《阿Q正傳》研究的主要方面,切中肯綮地道出了《阿Q正傳》的真義。其中所謂阿Q是“中國人品性的結晶”的提法,其實與後來馮雪峰所說的阿Q是“一個集合體”“‘國民劣根性’的體現者”的觀點是一脈相承的。而對俄國作家岡察洛夫筆下人物奧勃洛莫夫的聯想,則啟悟研究者發現阿Q與世界文學中的奧勃洛莫夫等著名人物形象屬於同一性質的藝術典型。“總覺得阿Q這人很是面熟”一語,正反映了這類藝術典型的普遍性特徵。
《阿Q正傳》在《晨報副刊》連載完畢一個多月之後,直接瞭解魯迅創作意圖的周作人,以仲密的名義在《晨報副刊·自己的園地》專欄中發表了《<阿q正傳>》一文,著重透露了《阿Q正傳》的主旨:“阿Q這人是中國一切的‘譜’——新名詞稱作‘傳統’——的結晶,沒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會的因襲的慣例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現社會里是不存在而又到處存在的。”阿Q“是一個民族的型別”。“他像神話裡的‘眾賜’(Pandora)一樣,承受了惡夢似的四千年來的經驗所造成的一切‘譜’上的規則,包含對於生命幸福名譽道德各種意見,提煉精粹,凝為個體,所以實在是一幅中國人品性的‘混合照相。’”文章一併透露了阿Q的生活原型——“一個縮小的真的可愛的阿貴,雖然他至今還是健在”。
作家自己的陳述,是理解作品本意最可靠的根據。魯迅1926年在《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中自己陳述《阿Q正傳》創作主旨時,也說要“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魂靈來”,“在中國實在算一件難事”。他“只得依了自己的覺察,孤寂地姑且將這些寫出,作為在我的眼裡所經過的中國的人生”。
毫無疑義,“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魂靈來”,使讀者從作者“眼裡所經過的中國的人生”中,感到“我們的傳統思想”給國人所造成的“精神上的痛苦”——正是魯迅創作《阿Q正傳》的主旨和本意。《阿Q正傳》發表時的1921—1922年,“周氏兄弟”關係尚未破裂,他們的意見是一致的。
然而,一般讀者對魯迅創作《阿Q正傳》的本意卻是不易接受的。孫伏園當時想為他主編的《晨報副刊》辦個“開心話”欄目,刊載與匯聚一些可笑、幽默的文字,讓人們在閱讀報紙時獲得輕鬆快意。魯迅依循“開心話”欄目的風格,將先前用於《狂人日記》《藥》等作品的筆名“魯迅”更換為“巴人”,“取‘下里巴人’,並不高雅的意思”。第一章“序”的話語風格也與先前的含蓄深斂、凝練沉鬱不同,加進了許多幽默和風趣。表面依照傳記通例,但具體內容卻完全抽空式處理,姓氏、名號、籍貫等無從確認,與傳統史傳的嚴肅“崇高”生成反諷,也與先前嚴峻深刻的批判大相徑庭。因而魯迅去世後,《阿Q正傳》改編中加進逗人發笑的滑稽、噱頭和自己的東西,使之浮淺化、庸俗化,導致對魯迅本意的扭曲。
這不禁引我想起一樁往事。1981年5月,我到揚州參加魯迅誕辰百年紀念大會籌備會,途經南京,當時任文學研究所所長的沙汀同志託人請我到南京代他看望一下陳白塵先生。我輾轉到陳白塵先生家時,雷恪生等中央實驗話劇院準備演《阿Q正傳》的眾多演員也在。代沙汀同志問過好後,大家就一塊兒談起來。陳白塵先生說,一位女大學生看了他改編的劇本後,說他是照抄魯迅,沒有自己的東西,這怎麼能稱為編劇呢?陳白塵先生接下來就說,他積累了幾十年的經驗和教訓,才明白完全按照魯迅本來的文字編,不加進任何逗人發笑的滑稽、噱頭和自己的東西,才是最正確的編法。事實證明,陳白塵先生說得非常對。他編的電影《阿Q正傳》和主演阿Q的嚴順開是大家比較認可的,也符合魯迅的本意。
其實魯迅生前就提到,他擔心人們不理解他的本意,造成種種曲解。早在1930年10月13日致王喬南的信中他就寫道:“我的意見,以為《阿Q正傳》,實無改編劇本及電影的要素,因為一上演臺,將只剩了滑稽,而我作此篇,實不以滑稽或哀憐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國此刻的‘明星’是無法表現的。”近六年之後,在魯迅逝世前兩個多月,又有人想把《阿Q正傳》搬上銀幕,而魯迅在1936年7月19日致沈西苓的信中又提出了經過十四年觀察所得出的看法:“《阿Q正傳》的本意,我留心各種評論,覺得能瞭解者不多,搬上銀幕以後,大約也未免隔膜,供人一笑,頗為無聊,不如不作也。”
由此,提醒我們要準確理解魯迅創作《阿Q正傳》的本意,就必須深讀。只有這樣,才能從中得到啟悟,“開出反省的道路”。否則,如果只是浮淺化、庸俗化地當作滑稽小說去讀,只能適得其反,扭曲魯迅的本意。
博讀法
我以為,要讀懂《阿Q正傳》,僅限於讀這一本書和魯迅著作是不行的。需要博覽群書,從世界文學視野對《阿Q正傳》進行比較與聯想。當年茅盾在《阿Q正傳》剛發四章時,就發現阿Q與世界文學中的奧勃洛莫夫等著名人物很相像,就在於他博覽過眾多外國文學作品。
其實,《阿Q正傳》跟塞萬提斯筆下的堂·吉訶德和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更為相像。塞萬提斯在《堂·吉訶德》裡借主人公的口說:“喜劇依照(羅馬作家)西塞羅的意見應該是人生的一面鏡子,世態的一副模樣,真理的一種表現”。莎士比亞同樣借哈姆雷特的口說:演戲的目的是“給自然照一面鏡子,給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貌,給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態,給時代和社會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記。”經過時間的長期磨鍊,阿Q、堂·吉訶德、哈姆雷特等偏重反映人類精神弱點的藝術典型確實成為一種諷世的鏡子,人們可以從中照出自己的精神面貌。阿Q反映了人們失敗後在假想中追求精神勝利的普遍弱點,堂·吉訶德表現了落後於時代的主觀主義的荒謬和愚蠢,哈姆雷特演繹了人們在關鍵時刻易犯的猶豫性格,奧勃洛莫夫體現了俄國地主貴族的懶惰與散漫。它們最重要的哲學啟悟意義就是:對人們的認識邏輯、方法進行反思,啟示人們正確地認識自己與認識世界,糾正缺點,正確行動。
從歷史脈絡來看,精神勝利法這種精神現象不是孤立的。遠的不說,明末清初利瑪竇、南懷仁等傳教士攜“西學”來華,當時的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即喜歡以一種“老子化胡”式的想象來理解“西學”。甚至一些學者中的佼佼者也這樣認為,譬如黃宗羲曾說,“勾股之術,乃周公商高之遺,而後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竊其傳”。王夫之在談論西洋曆法時,也曾說“西夷之可取者,唯遠近測法一術,其他皆剽襲中國之緒餘,而無通理可守也”。方以智說,西方曆法雖然精準,但其實都是中國古已有之的東西,“其皆聖人之所已言也”,只是後人不爭氣失傳了,“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被西方人撿了去發揚光大。而降至近代,鴉片戰爭一聲炮響,帝國主義列強用大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正如馬克思在《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一文中所指出的:“清王朝的聲威……掃地以盡,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擊”。然而在致命的打擊面前,中國封建統治階級卻拒絕正視現實,承認失敗,以總結教訓,重振國風,反而文過飾非,“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靠虛假的精神勝利來麻醉自己和國民的靈魂。正如許多研究家都引證過的那樣,近代中國不乏精神勝利法的例項:1841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後,清朝的將軍奕山向英軍卑屈求降,對朝廷卻誑報打了勝仗,說“焚擊痛剿,大挫其鋒”,說英人“窮蹙乞撫”。道光皇帝居然也說:“該夷性等犬羊,不值與之計較。況既經懲創,已示兵威。現經城內居民紛紛遞稟,又據奏稱該夷免冠作禮,籲求轉奏乞恩。朕諒汝等不得已之苦衷,準命通商。”英國侵略軍於虎門攻堅不克,竄入沒有嚴密設防的北方沿海,進入天津大肆騷擾時,在道光皇帝的“聖諭”中,卻在大講“該夷因浙閩疆臣未能代為呈訴冤抑,始赴天津投遞呈詞,頗覺恭順”。殖民者窮兇極惡地入侵,卻說成是“投遞呈詞”“呈訴冤抑”;殖民者一路的燒殺擄掠,卻說成是“頗覺恭順”;分明是在帝國主義侵略面前遭到慘敗,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屈膝求和,大批賠款割地,在有關的“聖諭”中卻還裝得趾高氣揚,說成是“妥為招撫”和“入城瞻仰”等鬼話。在這樣的“精神上的勝利法”面前,阿Q比起來都是不如的。
因此,這一時期對中國人來說,至關重要的需要有人大喝一聲,使之猛醒,實現精神的自覺。魯迅所扮演的歷史角色,正是承擔起這樣的重任。
以上的背景知識,只有透過博讀法,廣博地閱讀古今中外的歷史典籍和文學經典,才可能理解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魯迅創作《阿Q正傳》的本意。
省讀法
魯迅1934年11月14日在《答〈戲〉週刊編者信》中總結自己的創作初衷時說過:“我的方法是在使讀者摸不著在寫自己以外的誰,一下子就推諉掉,變成旁觀者,而疑心到像是寫自己,又像是寫一切人,由此開出反省的道路。”所謂“開出反省的道路”,實質上就是作家設法把自己的精神意旨傳達給讀者、又設法使讀者逐漸接受、進行反思的道路,用西方文藝理論的術語來說,就是其中包含著接受美學。
魯迅雖然沒有運用這種術語,但早期在《摩羅詩力說》中就闡述過這樣的原理:人人心中“有詩”,但是大多數人“未能言”,要靠“詩人為之語”,為之“握撥一彈”,讀者則“心絃立應”,而且“益為之美偉強力高尚發揚”,產生積極的反響。這啟示我們:要讀懂《阿Q正傳》,就須把自己放進去,與魯迅心貼心地反省自己,做到“省讀”。只有這樣,才可能有所醒悟。
這100年來,《阿Q正傳》幾乎成為考驗一個人閱讀力、領悟力和自我反省自覺性的試金石,啟發人們精神反思的警示器。坦率而言,精神勝利法在遭遇個別挫折且無可奈何時,也不妨作為寬解自己的應時之法,並非不能稍微使用一下,否則,阿Q可能早就不能那樣達觀,而是直接瘋掉了。但是,如果把精神勝利法當成一種長期的處世哲學,則是絕對不行的,因為如果那樣,人們就可能永遠陷在迷夢中不知覺醒,最後像阿Q那樣死了還不知怎麼死的。
苦讀法
茅盾先生在近百年前就在《魯迅論》中說過:“現代煩悶的青年,如果想在《吶喊》裡找一點刺激(他們所需要的刺激),得一點慰安,求一條引他脫離‘煩悶’的大路:那是十之九要失望的。因為《吶喊》所能給你的,不過是你平日所唾棄——像一個外國人對於中國人的唾棄一般的——老中國的兒女們的灰色人生。”如果你“不肯承認那裡面也有你自己的影子,那最好是讀一讀《阿Q正傳》。”“你沒有你的‘精神勝利的法寶’麼?你沒有曾善於忘記受過的痛苦像阿Q麼?你潦倒半世的深夜裡有沒有發生過‘我的兒子會闊得多啦’的,阿Q式的自負?算了,不用多問了。總之,阿Q是‘乏’的中國人的結晶;阿Q雖然不會吃大菜,不會說洋話,也不知道歐羅巴,阿美利加,不知道……,然而會吃大菜,說洋話……的‘乏’的‘老中國的新兒女’,他們的精神上思想上不免是一個或半個阿Q罷了。不但現在如此,將來——我希望這將來不會太久——也還是如此。”
正如林興宅所說:阿Q的精神勝利法,是整個人類“前史時代”的一種世界荒謬性,不可能短期消失的。為了我們自己身上儘早避免這種阿Q的荒謬性,很有必要多讀一下《阿Q正傳》。王冶秋描述過這種閱讀過程:“這篇民族的傑作,絕不是看一遍所能消化的:看第一遍:我們會笑得肚子痛;第二遍:才咂出一點不是笑的成分;第三遍:鄙視阿Q的為人;第四遍:鄙棄化為同情;第五遍:同情化為深思的眼淚;第六遍:阿Q還是阿Q;第七遍:阿Q向自己身上撲來……第八遍:合而為一;第九遍:又化為你的親戚故舊;第十遍:擴大到你的左鄰右舍;十一遍:擴大到全國;十二遍:甚至到洋人的國土;十三遍:你覺得它是一個鏡;十四遍:也許是警報器。”起碼要讀十四遍,才能接近魯迅《阿Q正傳》的本意,可謂是一種“苦讀”。中學生裡流行著“三怕”說——“一怕文言文,二怕寫作文,三怕周樹人”。這裡面有魯迅文章本身難讀與教學方法不當等問題,但還有學生害怕苦讀。作為教師,如果只用“好玩”的一面來吸引學生讀魯迅,這恐怕是不行的,我們承認魯迅文章可能難讀難懂,常說些逆耳之言,但又包含深厚意義。要讀懂魯迅,必須下一番苦功夫,不能圖輕鬆。因為讀懂魯迅和《阿Q正傳》,對自己一生更好地理解世界、認識自己都是極有意義的。
關於阿Q典型性的研究,從高中時期在韓少華老師指導下初讀,到大學階段中國現代文學課反覆讀,再到後來於研究、寫作中隨時讀,以及在楊憲益、戴乃迭翻譯的《魯迅小說選》細讀英文版,這60年間,我個人閱讀《阿Q正傳》何止十四遍,已超過一百四十遍。有的年輕朋友在我講這一段時還不太相信這個數字,其實我一直以此書為映象不斷反省自己,至今仍然感到需要繼續讀下去、自省下去,有些地方沒有讀透,還需要再讀、再回味、再思考。這種需求之下,苦讀當然是必要的。
悟讀法
高爾基稱讚契訶夫的作品“能夠使人從現實性中抽象出來,達到哲學的概括”。哲學境界是文學作品最難達到的峰巔。魯迅寫《阿Q正傳》也正是從現實生活中的阿貴抽象出來,以“我總算被兒子打了”這種粗俗、簡單的話表現了精神勝利法的荒誕邏輯,達到哲學的概括。
我們在讀《阿Q正傳》時,不能脫離實際,但又不能過實。魯迅創作《阿Q正傳》時,之所以把具體內容完全抽空,阿Q的姓氏、名號、籍貫等無從確認,未莊也模模糊糊,就是引導讀者脫離過實的窠臼,進行超越性的想象,悟出後面所藏的深邃哲理。《阿Q正傳》確實寫了阿Q的“革命”,但其創作主旨是對國民性弱點或民族病作有力的暴露與打擊。透過阿Q,他不僅批判辛亥時期的“革命”,而且廣及整個人類歷史怎樣結束改朝換代的惡性迴圈、進入政治文明化的問題。要理解這更深的歷史哲學,就須有更加超越的悟性,更加強調“悟讀”。
歸根結底,《阿Q正傳》是一部魯迅先生這位大哲創作的啟人精神反思、開出反省道路的哲學小說。它是魯迅以至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也是最早進入世界文學畫廊的現代偉大經典。魯迅命名的“精神上的勝利法”,揭示出人類精神機制深處的奧秘——在人類的精神與物質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間隔”與“隔膜”,具有從外界退回內心,把物質世界的失敗化為精神幻覺的勝利的“特異功能”。魯迅出於改變人類精神的崇高目的,經過長期、艱苦的對人類精神的研究,形象地發現和揭示出這一弱點,並加以命名和高妙的表達。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經這樣評價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全世界沒有比這更深刻、更有力的作品了。這是目前人類思想產生的最新最偉大的文字,這是人所能表現出的最悲苦的譏諷,例如到了地球的盡頭問人們:‘你們可明白了你們在地球上的生活嗎?你們怎樣總結這一生活呢?’那時人們便可以默默地遞過《堂·吉訶德》去,說‘這就是我給生活作的總結,你難道能因為這個責備我嗎?’”。魯迅從“提煉精粹,凝為個體”創造阿Q這個藝術典型,到後期寫阿金這個矇昧顢頇的都市孃姨形象,都是從根本點上總結當時中國人的生存方式,啟悟他所摯愛的中華民族從精神幻覺的迷夢中覺醒,掙脫出“瞞和騙的大澤”,敢於正視人生,直面艱難的物質實境,正確地認識自己與認識世界。這才是一種最根本的精神啟蒙與哲學啟悟。如果阿Q誕生百年後的今天,有人問我們:“你們可明白你們是怎樣生活過來的嗎?”我們或可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默默地遞過《阿Q正傳》去,說:“這就是我們覺醒的總結,我們還會以此為‘映象’繼續提高我們覺醒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