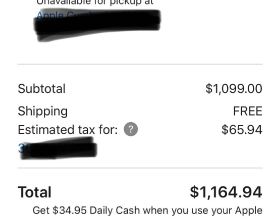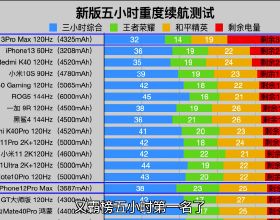這是新冠出現的第二年,是距離非典首例爆發的第19年,也是世界上第一個“超級傳播者”被發現的第115年。
1906年8月,紐約長島牡蠣灣的一起不尋常的傷寒聚集案例引發衛生部門的注意。
富有的沃倫一家,家裡11個人,6人都感染了傷寒。
傷寒在當時是最可怕、傳播最廣的疾病之一,人們對它幾乎是談之色變。
當讓人疑惑的是,傷寒是一種窮人病,鍾愛的是城中髒亂差的貧民窟,或是逼仄擁擠的公寓樓。
沃倫一家十分富有,住在富人區,本不該和這種疾病產生聯絡,那麼他們一家是怎麼患上這種疾病的呢?
衛生工程師索帕經過長時間的排查,最終把目光鎖定在了廚師瑪麗身上。
索帕發現,瑪麗之前工作過的七個家庭,無一例外都爆發過傷寒疫情,甚至有人因為感染傷寒不治身亡。
但是瑪麗從沒有兌換過傷寒,而且本身面色紅潤,體格壯碩,十分健康,任誰也不能相信,瑪麗會和傷寒產生關係。
但事實上,醫生從瑪麗的糞便中檢測出大量的傷寒病菌,他們無法解釋為什麼瑪麗不會患上傷寒,可毋庸置疑,瑪麗就是那8個家庭患上傷寒的源頭。
人們不知道該如何處置這個“健康的病毒傳播者”,只能把她隔離人群,囚禁在北兄弟島上。
瑪麗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其實誰都不知道該如何給瑪麗定罪,她是最危險也是最無辜的兇手。
人們畏懼她,又同情她失去自由。
經過3年的抗爭,瑪麗終於重獲自由,條件是她不能再做廚師,而且必須定時去衛生局報道。
可惜瑪麗沒有信守承諾,她只有廚師的手藝能餬口,沒多久她就改名換姓,去一家婦科醫院的食堂當了廚師。
瑪麗(右)在北兄弟島上與一名細菌學家合影,這時瑪麗60歲左右
1915年,那家婦科醫院爆發了傷寒,共25人感染,2人死亡,瑪麗再次被千夫所指,“傷寒瑪麗”,成了流行病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符號之一。
瑪麗自那之後再次被關進了北兄弟島,一直到1938年因中風併發症去世。而直到去世,她本人都沒得過傷寒。
這就是人類有記載的世界上第一個“超級傳播者”,一個被動的”兇手“,一個被命運捉弄的普通人。
在傳染病面前,比起看不見摸不著的病原體,人們似乎更害怕自己的同類。甚至不惜以最大的惡意揣測和對待他們。
瑪麗的結局是被囚禁了一生,那19年前的那些非典超級傳播者們,他們過得又怎麼樣呢?
01
世界衛生組織提出,如果1人將病毒傳染給10人以上並且都被確診,那麼該傳播者可以稱為超級傳播者。
然而,這個專業術語被放置在大眾語境中,就變成了另一個情感色彩濃厚的詞語——毒王。
黃杏初就是這樣一個“毒王”,他還是全廣東、全國、全球報告的首例感染非典病毒的病人。而首例常常被大眾非常不理性地理解為“病源”。
2002年底,黃杏初突然回了河源市老家。他本是深圳一家客家菜飯店的大廚,臨近年關返單正是最忙碌的時候,但是黃杏初卻病了。
他全身無力、畏寒、高燒不止,去醫院打吊針接受常規治療都不起效用,黃杏初也有點害怕,請假回了老家。
可是在家休息了幾天,黃杏初的身體也不見好轉,病情反而愈加嚴重,12月15日,他被緊急送往河源市人民醫院。
那時不管是醫生還是黃杏初的家人,都以為他患上了嚴重的感冒,住幾天院就會好的。
沒想到,住院的那幾天,黃杏初不僅沒有好轉,還出現了呼吸困難的症狀。
醫生不敢大意,在17日安排他轉院至廣州軍區總院搶救,第二日就上了呼吸機。
黃杏初萬萬想不到的是,他在生死線掙扎求生的時候,河源市人民醫院先後有9名醫護人員因為高燒倒下了。
那時候,還沒有“非典”這個詞語,人們也不明白這是一場多麼危險的戰役。
越來越多的人因為高燒、呼吸困難被送進醫院。
郭先生是早期感染者之一,發病比黃杏初只晚一兩天。
2002年12月,經河源市人民醫院轉送廣州。他被送到了鍾南山的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在那裡,他度過了2003年的春節。
經過一個多月的治療,黃杏初終於慢慢恢復了健康,當時他並沒有把這次生病當做一件大事,只當是自己之前累得狠了,小病攢到一塊兒變成大病才會如此兇險。
出院後沒多久,黃杏初就回到在深圳工作的飯店繼續上班了。
而他上班的第二天便聽說,中山市在傳播不明原因的肺炎,情況兇險,已經被命名為“非典型肺炎”,而傳染的源頭是河源市。
黃杏初聽到這個訊息大吃一驚,因為報道的那些症狀,他太熟悉了,
“這不是和我之前住院的症狀一模一樣嗎......”
“我之前得的不會就是這個非典吧?”
“不會的,不會的,我怎麼可能那麼倒黴,我現在都好了,他們那個還沒有特效藥呢,我怎麼可能是那個病呢.....”
黃杏初越想自己的之前得的病就越害怕,又忍不住抱著僥倖心理安慰自己。
沒多久,非典疫情開始在全國蔓延,黃杏初工作的飯店也因為違章建築被拆除了,黃杏初沒了工作回到了家鄉。
2月24日,黃杏初到廣州軍區總醫院複診,最終確定自己當初所得的就是非典。
而且他還是全國,乃至全球報告的首例感染非典的病人。
02
在很多人看來“首例”意味著源頭,這一刻黃杏初“火”了,媒體記者爭相報道訪問,衛生部門追蹤調查 ,
他們都想知道,黃杏初到底做了什麼,或者說是從哪裡“帶來”的病毒。
而一些不理智的人已經在給黃杏初按頭銜:“毒王”“超級傳播者”“罪魁禍首”......尤其是在得知黃杏初還感染了9名醫護人員後,他們更加的義憤填庸。
當初接診黃杏初的葉醫師是病情最嚴重的,他在生死線上走了一遭,03年春節前夕才度過危險期撿回一條命。
然而葉醫生的恢復沒有黃杏初好,雖然命撿回來了,但是被病毒損傷了肺部,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一年裡有半年都會咳嗽,最愛踢的足球也再沒有碰過。
其他幾位醫護人員症狀都比較輕微,可結局卻更讓人痛心。
有兩個女護士被感染時都懷有身孕,其中一位被確診感染了“非典”,在搶救過程中孩子沒了,這成了她心中永遠的傷疤。
還有一位女同事屬於疑似病例,雖然沒有確診,但當時也發燒治療過,後來她懷的孩子生下來了,但是孩子被確診患有先天性白內障,很多人懷疑這和感染“非典”有關!
最最讓人意外的是,黃杏初的家人沒有一人感染髮病。
被感染的不僅僅是9個人,他影響的是9個家庭,和很多人的人生。
那一段時間黃杏初自己都覺得自己是個罪人,但細想一下,他又真的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
他沒辦法給自己申辯,譴責的聲音從全國各地湧來,他覺得自己像個“過街老鼠”,被別人“審視”或“嫌棄”的目光壓得喘不過氣來。
他想去重新找工作,但是對方一聽他是感染過非典的黃杏初,都不願意聘用他,還用異樣的眼光打量他。
這種巨大的心理負擔,讓黃杏初感到迷茫和絕望:我也是病人,我也是受害者,為什麼只因為我是第一個患病的就要遭受歧視?
他開始逃避,逃避所有媒體的採訪,躲開社會的關注,幾乎拒絕了所有露面的機會。
2003年5月22日是黃杏初最後一次在公眾面前露面,他在媒體的監督下,向廣州軍區總醫院捐獻了含有病毒抗體的血清。
他說,自己最希望的就是這場患病經歷能夠不影響自己的工作,以後自己和家人只想過平靜的生活,之後就再次“神隱”了。
2013年,非典10週年之際,有記者找到了黃杏初的老家想採訪他,卻撲了一個空。
黃杏初家的房子是一棟三層小樓,和周圍的房屋相比顯得十分豪華。
不過這棟房子幾乎已經荒廢了,早就沒有人住了,周圍鄰居對黃杏初的近況也是一問三不知,
只知道他在城裡開餐館,孩子們在城裡讀書,記者想要個電話聯絡採訪,卻一直打不通。
黃杏初似乎想與過去徹底斬斷,但是心裡的傷痛又豈是時間能治好的
03
除了黃杏初,非典時期還有一位感染力度最大的超級傳播者叫周作芬。
有人曾這樣形容周作芬:他的一聲咳嗽,足以引起人們對死亡的恐懼。
他住院50多天,先後感染了130多人,為了救他兩名醫護人員殉職,可是他本人最後卻病癒出院了。
2003年的1月31日,廣州第一例本地SARS病人在廣東省中醫院病癒出院。同一天,從事海鮮批發生意的周作芬在家人的陪同下走進中山二院。
周作芬是個典型的要錢不要命的生意人,他已經連續5天咳嗽發熱了,但是時間臨近新年,檔口生意正是最忙碌的時候,也是最賺錢的時候,他捨不得休息。
這天是農曆的除夕,還在檔口工作的周作芬咳嗽突然加重,呼吸困難,才在妻子的勸說下去中山二院檢查。
進醫院的時候,周作芬的病情不算嚴重,他腰間綁著一個收款人的錢包,辦理了住院手續後還在妻子一起在病床上數錢。
他覺得自己才44歲,身體強壯年富力強,一點小病小災,打兩天點滴很快就好了。卻不想他的病情會急轉直下。
當天晚上醫院接到緊急通知,廣州出現了非典型肺炎,而周作芬那時的血氧飽和度僅為68%,已經陷入了昏迷,他很可能得的就是這種肺炎。
2月1日,大年初一,周作芬被緊急轉到中山三院搶救,直到4天后,人們才終於知道周作芬作為一個超級傳播者有多麼可怕。
周作芬在中山二院只停留了24小時,可所有接觸過他的醫務人員,包括放射科主任、副主任,呼吸科醫生、護士、實習醫生、護理員、配餐員,擔架工人、救護車司機,共30餘人相繼患上非典。
其中負責幫他轉院的救護車司機範信德病情最重,於2月23日搶救無效身亡。
而周作芬轉到三院後佈局,就因為缺氧全身發紫,病情進一步惡化,必須立即插管、上呼吸機。
這又是一次和病毒的零距離接觸,插管過程中隨著一陣劇烈的咳嗽,周作芬帶血的濃痰一下子噴到了天花板上,
病毒汙染了周圍的環境,參與救治的所有人,先後兩批共20多名醫務人員被感染。
之後周作芬的岳父、岳母、妻子、兒子等21名親屬也相繼病倒,住進了他隔壁的病房搶救、配上了呼吸機。
而這個時候周作芬的病情在慢慢好轉,第二天他就甦醒了過來;第三天就能摘下呼吸機面罩......第六天已經能坐起來吃蘋果和醫護人員開玩笑了。
周作芬意識清醒後最關心的問題就是:這些天治病到底花了多少錢,
醫生半開玩笑地告訴他,你已經毒倒了50多名醫務人員,20多名親朋好友,80多人的醫療費應該超過100萬了。
這一刻周作芬笑不出來,不是因為錢花得太多,而是無法接受自己成了災難的源頭。
整個中山三院傳染病區因為他而陷入癱瘓,岳父母被感染後沒能挺過去,在他病癒前去世,還有兩名醫護人員也是因為搶救他而被感染殉職的.....
從那一天開始周作芬沒了笑容,他的淚水打溼了枕頭,從此開始躲避媒體的採訪和所有來探望的人。
3月3日周作芬病癒出院,作為商人,他提出給救治他的醫生護士們送一些錢作為謝禮,但是被拒絕了。
最後,他請人做了一面錦旗,上面寫著“起死回生,再世華佗”,然後舉著錦旗“撲通”一聲跪在了醫生面前,久久沒有站起來。
之後他就像完成了什麼任務一樣,從人們的視線裡消失了。
04
我們無法知道周作芬當時心裡到底是什麼滋味,不過可以想象,家庭的不幸,輿論的壓力和治病花去的數十萬費用,對周作芬來說都可以算的上是滅頂之災。
而對他的生活影響最嚴重的還是“歧視”。
逃離生死線一個多月後,周作芬曾出面請曾經的主治醫師陳燕清吃飯,地點是一家海鮮酒樓。
周作芬說,之前這家酒樓的海鮮是他提供的,現在雖然依舊是他提供,不過他和酒樓只能做地下生意,一旦被客人知道是他供的貨,估計就沒人來了。
其實還不止是酒樓,那一個多月裡,不管周作芬是下館子還是娛樂消遣,只要被人發現自己是那個超級傳播者周作芬,就會被客氣的請出去,
他住的小區甚至都有人因為他搬走了...
這是周作芬第一次體會到人們目光帶來的壓力,他摧毀的不止是一個人的信心,更是一個人的人生。
所以之後海鮮鋪老闆周作芬消失了,他換掉手機號碼,搬離原來住的小區,換掉了幹了多年的海鮮檔口。
他不再主動聯絡與“非典”時期有關的任何人,很多記者尋到他的家,但無一例外地吃了“閉門羹”。
曾有來自國家、省、市衛生部門,甚至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尋找他,可從來沒有成功過,不是吃閉門羹,就是被“放飛機”。
周作芬消失得很徹底,他甚至沒在媒體上留下過任何一張照片,唯一一張照片還是送錦旗的時候醫院幫他拍的,
他笑的僵硬,侷促地拿著錦旗,躲在幾個醫生身後。
可是在這個資訊透明的社會,沒有人能完全隱藏行蹤,
2011年,他在當地一家報紙的角落刊登了一則遺失宣告,“荔灣區周作芬先生,遺失營業執照兩本,現登報作廢申明”,根據他刊出的營業號,證實是他本人。
他還在家鄉做生意,只是為了保護自己和家人,選擇了逃開某些人的視線。
人類的自衛意識有時候是個可怕的東西,他對“自己人”無限寬容,對他人又極力藐視。
儘管過去了19年,當地人再想起周作芬,第一個反應還是:哦,就是那個“毒王”,就是因為他當年在做海鮮生意,搞得我心裡有陰影,後來一直都不願去他待過的海鮮市場買東西。
其實作為非典的患者來說,黃杏初和周作芬都是受害者,他們不幸被命運選中,成為被口誅筆伐的替罪羊,
讓人欣慰的是,他們不僅戰勝了病毒, 也戰勝了人們的歧視,再次將自己的生活推向了高潮,
他們神隱是在保護家人,一些理智的人們也在透過“搖頭”來保護他們的安寧.....
揭開舊傷疤是為了忘卻的紀念,更是為了警示後人。
無論是什麼樣的傳染性疾病,非惡意傳播的感染者同後來的患者、健康者應該處於一樣地位,他們都是受害者,都是被命運戲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