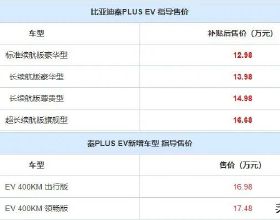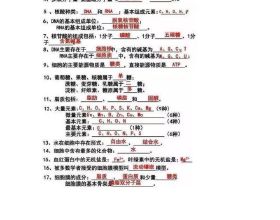大克鼎 高93.1釐米,口徑75.6釐米,重201.5千克 大克鼎銘文
“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館受贈青銅鼎”特展最大亮點無疑是大盂鼎和大克鼎。其實早在2004年,上海博物館就曾經聯合國家博物館舉辦過兩鼎的“合璧”展,彼時的展覽實則是為了慶祝大鼎的捐贈者、潘祖蔭孫媳潘達予先生百歲壽誕,以此表達對於國寶守護者的敬意。北青藝評此前曾介紹了大盂鼎,本文將著重揭秘大克鼎的身世。
大克鼎的年代
在此次展覽中,策展方將大克鼎的年代定為西周中期孝王時代。這一觀點來自上海博物館前館長馬承源先生。馬先生斷代的依據主要有三點:一是根據銘文所示,克的祖父(文祖)師華父服事周恭王,從而判斷作為孫子的克當在孝王;一是銘文中冊命禮上擔任右者的申季出現在恭王器五祀衛鼎銘文中,彼時申季官階尚低,僅為邦君厲的下屬,因此大克鼎時代與五祀衛鼎時代不能相去太遠;一是同一人所作的克鍾銘文出現的紀年“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而依據四分月相說判斷此紀年和日期符合孝王十六年的歷譜。此外,關於大克鼎以及克組青銅器的斷代則有陳夢家的夷王說,郭沫若和唐蘭的厲王說(上博李朝遠先生亦持此說),以及上海博物館周亞先生的夷、厲之際說。我們更加贊成大小克鼎皆為厲王器的觀點。
首先,大克鼎與小克鼎的器型更接近於厲王時期的禹鼎,相比於宣王晚期的四十二年、四十三年逨鼎,兩件克鼎的腹部更深,顯得年代更早。但這種立耳、腹部微垂、獸蹄狀足的造型,是西周晚期常見形制。這一器型與西周中期淺垂腹、柱狀足造型有很大差別。其次是克鼎腹部的波曲紋很成熟,與所見的厲王、宣王器如頌器、函皇父器等相近。再次,大克鼎的右者申季也見於厲王時的伊簋,未見得與五祀衛鼎的申季是同一人。還有就是,大克鼎銘文製作字模的同時加刻了界格,這種形式多見於厲王時期。最後,根據筆者以往的研究,西周中期極少見周王派遣使者巡視諸侯或王畿的銘文,而小克鼎銘文則表明,周王派遣克“捨命於成周,矞正八師”,即代表周王到成周(洛邑)視察成周八師軍隊。這與周厲王加強王室權力的改革有關,更與該時期對南淮夷的大規模戰爭密切相關。
“克組器”是個大家族
學術界習慣上將同一人擁有的多件青銅器稱作“某組器”。“克”的家族在西周雖然並不是望族,但以大克鼎為代表的“克組器”數量龐大,堪稱青銅器裡的“大家族”。
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一書談及小克鼎的出處時引用古董商趙信臣的話說,光緒十六年(1890年)(實際“克組器”出土時間為光緒十五年,即1889年)在陝西岐山(應當為扶風)任村任姓家出土“百二十餘器”。而1934年出版的《續修陝西通志稿》卷135《陝西金石志》則說,大克鼎“發現之處若土室(即窖藏),然共得鍾、鼎、尊、彝等器七十餘……”兩處記錄出土青銅器數量差距較大,但總體而言此次發現數量的確驚人。
任村窖藏中與克有關且儲存至今的器物有:大克鼎1件,小克鼎7件,師克盨3件,克盨1件,克鎛1件,克鍾5件,共計18件。宋代呂大臨撰寫的《考古圖》中著錄一件伯克壺,其出土地點也在任村一帶,且其銘文中的伯克應當就是大小克鼎中的克。但可惜的是,伯克壺早已丟失,僅存宋人描摹的線圖。
從銘文可知,克的祖先有文祖師華父(大克鼎)、皇祖釐季(小克鼎)、皇祖考(孝)伯(克鎛)。郭沫若先生認為大克鼎的師華父就是小克鼎的釐季,是一名一字的關係。但是,通觀金文辭例,皇祖與文祖在輩分上還是有差異的。祖父以上數代先祖皆稱皇祖,而“文祖”則常和“文考”同時出現,“文考”是先父輩,那麼“文祖”應當就是祖父輩。例如興鍾銘文有“高祖辛公、文祖乙公、文考丁公”,這裡明顯是三輩祖先——曾祖(辛公)、祖父(乙公)和父親(丁公)。因此,克器的文祖師華父應當比皇祖釐季和孝伯輩分要低,是克的祖父。同樣被譽為皇祖的釐季和孝伯也不是一輩人,這從名字中的排行可以看出,但世代久遠可以統稱為“皇祖”。
師華父的職官是“師”,這並不是一個很高的職位,主要職事與軍隊有關。在西周金文中以“師”為氏的人很多。克起家的職官是膳夫,這是一個內廷供奉天子膳食的小官。由於是天子身邊的近臣,因而可以臨時向外部傳達天子命令。在西周早期國家體制中,內朝與外朝的界限並不清晰,服務於天子本人的職官有時也會從事宮外事務。在小克鼎中,克就作為膳夫奉命巡視成周八師,這很像是明代太監出鎮邊關作監軍,當然克本人並不是太監。最後,克還是繼承了祖父的職位,出任“師”官,名字也變成了“師克”,其職事是執掌宿衛部隊——左右虎臣。
總之,克家族職官、地位並不屬於高門望族,但由於能夠服務於內廷,從而擁有相當的權勢。目前發現的克組青銅器雖然不是克器全部,但已經數量驚人(有學者認為同出任村窖藏的中義父諸器也是“克組器”),而且“克組器”的紋飾相當精美,器型也規整可觀。相比之下,出自南宮望族的南宮柳鼎就拙樸很多。這可能與克是家族宗子(伯克壺)地位有關,也可能是厲王寵信近臣,有意抬高其地位。
來源: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