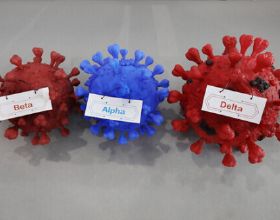瓊玉姐
· 袁志軍
每年進入七月,我的思緒便不得安寧。
連日來,滂沱大雨像是天河水決了堤,電閃雷鳴,震耳欲聾,很多地區都遭遇了洪災,損失挺重。深夜,聽著一聲接著一聲的驚雷滾過樓頂,雨點拍打在玻璃窗上噼啪作響,思緒便不由自主地又回到45年前那同樣的一個風雨交加之夜,想起在唐山大地震中遇難的戰友,想起了瓊玉姐……
1970年5月,入伍兩年多的我從天津部隊機關調到唐山駐軍醫院,由打字員改做衛生員。
那天晚上,剛剛睡下就聽到大喇叭裡傳來緊急的呼喊聲:“同志們請注意!現在急救室裡有5名因公負傷的戰士正在搶救,急需要大量輸血,要求同志們踴躍獻血,踴躍獻血!”我心裡一驚,像是聽到了緊急集合號,立馬穿上衣服,拿出百米賽跑的勁頭兒,風風火火地跑到檢驗科。科門口已經擠滿了要求獻血的戰友,我個子小、體重輕,三鑽兩竄便站到了最前面,心裡只想著要第一個獻血,擼起衣袖,衝著一位穿白衣、戴白帽的女檢驗員嚷道:“先抽我的,我是O型血!”
“小同志,你先別急,我們必須要複查血型,這是規定。”她言語和藹,動作輕柔,一邊在我的右耳垂上採了血樣,一邊上下打量著我,輕聲地問:“哪個科的?我好像沒有見過你。”我回答:“內一科的,剛調來第六天!”
化驗結果,確定我為O型血。她微笑著問:“怕抽血嗎?我看你身子骨挺弱,要不行這回就……”我嘴上接連說著“不怕”,可心裡還真有些犯怵,這是我長到19歲頭一回獻血,要抽300毫升啊!我本來個頭兒就不高,會不會影響到我以後長個兒呢?這樣想著,伸出的胳膊就有些發顫,手心裡也好像攥著一股涼氣。
她肯定是瞧出了我此時的心情,囑咐我把頭側向一邊,為了分散我的注意力,她還不斷地和我嘮嗑兒,問我多大了?當兵幾年了?老家在什麼地方?父母都幹什麼工作?一開始我答話的聲音還有些發顫,慢慢地心情平穩了下來,說話也就自然多了。不大一會兒,她就拔出針頭,在針眼上壓了根棉棒,輕鬆地說:“好了好了!把胳膊彎過來多壓上一陣兒,免得出血。”我心想,怎麼沒覺著疼啊? 她把一瓶貼著標籤的血,舉到我面前輕聲地說:“小同志啊,你可真勇敢!看看吧,這就是你身上的熱血,要流到戰友們的身體裡去了。”
看著那殷紅的血,我心裡嘀咕,很想摸一摸:“血真是熱的嗎?”
眼巴巴地望著急診室的護士取走了血,我才如釋重負般長長地撥出了一口氣,心裡似乎有些得意,雖說沒能夠像先烈那樣在戰場上流血犧牲,可總算是有了一次為救戰友而奉獻熱血的機會。我自豪地衝那位親切的女檢驗員笑笑,這時才看清她潔白的口罩上面,露出一雙美麗而 清亮的杏核眼。
第二天按時去上班,護士長知道我剛獻過血,特意體貼地安排我休息一天。我回到宿舍,躺在床上閉著眼,心想這要是在家裡該有多好,媽媽肯定會給我做一些好吃的,想著想著,竟朦朦朧朧地睡著了。不知過了多久,聽到有輕輕的敲門聲,我揉揉眼睛下地開門,門外面筆挺地站立著一位身著整潔軍裝的女同志,30歲出頭,中等身材,鮮紅的領章映襯著她紅撲撲的漂亮臉龐。我怔怔地望著她,似曾相識,可一時又想不起在哪裡見過?
“怎麼啦?昨天晚上還抽過你的血,今天就不認識了,小小年紀這麼健忘啊?”她露出兩排雪白整齊的牙齒,呵呵地笑著。
“哎呀,真對不起!”我欣喜地叫著,“因為昨晚您戴著大口罩,我沒看清,沒想到您會來看我。”我忙不迭地把她讓進屋。她拉著我的手要我上床躺下,拉過被子給我蓋好,然後坐在床邊輕聲細語地說:“你一個女孩子剛調過來,就為戰友輸血,身體又不太壯實,我昨晚一見就挺喜歡你,特意煮了幾個雞蛋,帶了包紅糖來給你補養一下。”說著,她從挎包裡拿出紅糖,用軍用茶缸為我沏了一茶缸的紅糖水,又掏出用白毛巾裹著的雞蛋,剝好皮放進茶缸,還掏出一個小勺說:“來,快趁熱吃了。”我激動地坐起身來,只覺著有一股暖流通遍全身,一時不知道說些什麼才好,剛剛見過一次面的戰友,對我就像是一個親姐姐,這份親情、這份愛,我該怎樣報答啊!要知道,那年頭兒要能吃上個雞蛋,可不像現在喝杯開水那樣容易。戰士們只有在患頭痛腦熱病痛時,才能吃到一碗雞蛋麵條。捧著她送到我手裡的雞蛋,我的鼻子有些發酸,淚水不由自主地模糊了視線。
她看到我這副模樣,頗有些嗔怪地說:“客氣什麼啊,穿上軍裝咱們就是親姐妹,我是你姐姐,你是我妹妹,親妹妹,懂嗎?”
“我吃、我吃……”我有些不好意思,喃喃地說。
她讚許地說:“哎,這就對了,一會兒再喝點兒紅糖水身上就有勁了。我今天正好休息,就陪你說會兒話吧!”
透過聊天兒,知道她叫劉瓊玉,1951年當的兵。瓊玉姐出生在湖北省一個偏遠山村的土財主家,4歲就死了親孃,繼母心狠手黑,對待年幼的她還不如傭人丫頭,白天干髒活、累活不說,到了晚上還讓她睡在柴房,一年四季吃不飽、穿不暖、挨打受罵,那份罪受的。
好容易等到14歲,家鄉解放了。她看到解放軍隊伍裡也有女兵,打心眼兒裡羨慕,就整天圍著那些女兵轉,知道了很多從沒聽說過的新鮮事。就是從那時起,她下決心要脫離開那個見不著光亮的家,一輩子跟著共產黨走!部隊開拔時,她偷偷地跑出來尾追在隊伍後面,軟磨硬泡地參了軍。她原本準備隨著部隊去抗美援朝,可部隊開到河北唐山時就駐紮待命,以後沒有去朝鮮,而是組建了駐軍醫院在唐山紮了營,她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建院的元老,部隊成了她真正的家,首長、同志、傷病員都成了她的親人。
後來她與醫院一位醫療助理員相愛結婚,丈夫事業心強,正直可靠,後來提拔為醫務處副主任,他們有了三個可愛的兒子,家庭挺美滿,也挺幸福。說著,說著,她戛然而止,目光裡掠過一絲淡淡的哀愁。我不解地問:“怎麼了?”她眨了眨有些發紅的眼睛,咬了咬微微顫抖的嘴唇,才輕輕地嘆了口氣說:“人啊,沒有十全十美的,我當兵快二十年了,到現在還不是一名黨員,可做夢都盼著黨組織能吸收我。”
原來,不能加入黨組織的原因,不是因為她的思想和工作不好,她年年都立功受獎,而是因為她的出身不好。她每年都向黨支部遞交一份入黨申請,已經寫過十幾份了,還定期向黨組織彙報思想,她不知道還要考驗多久,才能實現自己這一夙願。
她的話也勾起我的心事。我出身在革命幹部家庭,入伍半年就加入了共青團,並很快就填寫了入黨志願書。我渴望黨組織能早日批准。不料,一封外調信頃刻間使我成了走資派的女兒,那份已填好的志願書作廢了,我頓時像正在燃燒著的篝火被暴雨熄滅……也是從那時起,凡屬絕密檔案不讓我列印,再後來我被調離了工作,有一種被髮配的苦澀……
沒有想到,竟然還有比我更委屈的人。瓊玉姐從小姑娘時就背叛了封建家庭,走進了革命隊伍,經受二十多年的考驗,她還在虔誠地苦苦追求。相比之下,我受的這些挫折算不得什麼了。
從那天起,我一直很是敬重瓊玉姐,把她當作親人,有什麼心事都向她訴說,她也總是一點一滴地開導我,從沒有煩過。記得有一回,我到學習室取筆記本,走近門口無意聽到裡面兩個人的對話聲,其中一個啞嗓子的男聲說:“上邊又要求換人了,我看你去吧!”我聽出這是團支部書記。另外一個女聲接道:“我去過了,讓沒去過的去吧!”這是護士小吳。“都輪過一遍了。”團支書說。“誰說的,小袁還沒去過呢!”小吳說。團支書似乎愣了一下,說:“她不是政治審查不合格嗎?”
聽到這裡,我只覺得腦子嗡嗡地響,他們下面再說什麼我已經聽不清了。我知道他們所說的“換人”,是去北京執行政治任務,這在當時是保密的,說我政治審查不合格,肯定是指我父親的問題。我委屈得不能自制,筆記本也不取了,咬緊牙跑回宿舍碰上門,一頭撲倒在被子上放聲慟哭。
後來哭累了,覺著實在委屈,爬起來就去找瓊玉姐。靜靜地聽我說完經過,瓊玉姐撲哧一聲笑了,她說:“這算什麼呢?到底還是個孩子。”她說她很理解我的心情,她也最怕週六下午過黨團生活,全科人不是黨員就是團員,只有她什麼也不是,只好留下來值班,那心裡的滋味真是不好受。
瓊玉姐輕聲說:“我們不是說好要經受住黨的考驗嗎?什麼叫考驗,這就是!這也算是小小的考驗,連這點都經受不住,真要是遇到生死攸關的大考驗,還不得當逃兵啊!”她讓我相信,黨組織不會忘記我倆,心胸要放開一點,眼光要看遠一點,別因為這些小事失去自信,對黨組織失去信心。聽了她的話,我心裡就像是打開了一扇窗,一下子感到豁亮了。
1974年8月,隨著父親問題的落實,我終於成為一名黨員。瓊玉姐聽到這個訊息後,高興的就像過年,滿面春風地把我拽到她家,鑽進廚房手忙腳亂地炒了兩道菜,滴酒不沾的她破例開啟一瓶白酒,和我碰杯後一飲而盡,辣的她直皺眉頭,捂著嘴不住地咳嗽著。當時我不想說話,只是默默地流著淚,淚水大滴大滴地落在酒杯裡,我為瓊玉姐多年的夢想還沒有能夠成真感到難過,我情願今天是為她祝酒……
1976年初,瓊玉姐到天津的一家大醫院進修,好幾個月我們沒有見過面,但一直保持著通訊。7月下旬裡的一天,她突然回來了,說是生病了,高燒不退,滿嘴起了泡。那一天的天氣出奇的燥熱,我就抱著個西瓜去看她。我的到來讓她很是開心,拉著我的手,說她不能呆太久,很快還要回天津去進修,可不知為什麼這次回來特別戀家,從心裡捨不得再走。
或許這就叫做預感,萬萬沒有想到,這竟是我和瓊玉姐最後的談話,沒過兩天,準確地說是1976年7月28日凌晨,一個風雨交加、電閃雷鳴的深夜,唐山發生了強烈大地震,正在熟睡的人們還沒弄清楚發生了什麼,就被深深地埋在了倒塌的房屋裡,我們美麗的醫院瞬間變為碎磚亂瓦,我也被埋在廢墟里,身負重傷。當我被戰友們搶救出來後,碾轉到石家莊駐軍醫院住院治療,這期間一直沒有聽到瓊玉姐的訊息,心裡很是惦記。
4個月後,當我一瘸一拐地回到唐山醫院時,方知瓊玉姐所居住的那幢樓裡只倖存了9個人,她和丈夫及兩個兒子全都遇難了,大兒子因在外地當兵才得以逃生。這怎麼會?我不相信是真的。
“她明明說該回去進修了,她一定是迴天津了。”我自言自語,反覆叨咕著:“她不會死,她肯定是迴天津了,她去進修了。”
戰友們說:“她真的不在了,就埋在機場的花生地裡”。
我不信,我要去那裡證實。那天,我懵懵懂懂地深一腳、淺一腳地走了好半天,彷彿走了一個世紀才來到那片土地,那是一片地震前一天我還和戰友們為花生鋤草的土地,那片沒有來得及收穫就堆起幾百座墳塋的土地。這裡有我的瓊玉姐嗎?慢慢地走過一座座墳塋,撫摸著墓碑上一個個熟悉的戰友名字,就如同在和他們握手,他們的音容笑貌活生生地浮現到眼前。我沒有流淚,堅信他們還在,他們只是去執行任務了,這對當兵的來說很正常,他們遲早都會回來的。
我的手突然觸控到了“劉瓊玉”的名字,她的身邊還有丈夫和兩個兒子。我的全身頓時像是觸電一般地顫抖,只覺得天旋地轉,眼冒金星,一下子癱軟在墳塋前。趴在那堆黃土上我不由的號啕大哭……
組織上給遇難的戰友們都定為了烈士,生前有入黨要求的經黨支部討論透過追認為中共黨員。在討論瓊玉姐的時侯,同志們一致認為她早就該是一名黨員了,於是很順利地通過了。當院黨委宣佈追認她為中共黨員後,我為瓊玉姐精心製作了一個小花圈,買了幾樣點心、水果,拎了一瓶白酒,又來到她的墳前,把這個好訊息告訴了她,這可是她生前苦苦追求、做夢都盼望的好訊息。我久久地坐在她的墳前,默默地向她傾訴,相信她一定能聽到我的訴說!我一仰頭喝下了半瓶白酒,沒覺出辣,只覺得甜,很甜!另外半瓶都倒給瓊玉姐了,看見她也一飲而盡,這一回沒有聽到她的咳嗽,她在笑,衝著我笑,笑著笑著,我們都流淚了……
時間如梭,轉瞬45年過去了,但我始終無法忘記在地震中犧牲的戰友們,每年的7月,思念就會加劇。在紀念唐山大地震30週年、40週年之際,我們曾在唐山駐軍醫院工作過、倖存的一百多名老兵,集結回到故地祭奠震亡的戰友們。
在祭奠活動上,我遇到了瓊玉姐的大兒子蔡明,地震前他參軍到北京空軍當地勤兵,我還去部隊上看過他。唐山大地震他失去了父母和兩個弟弟,瞬間成了孤兒,他是瓊玉姐留下的唯一骨血。蔡明後來與唐山駐軍醫院的一名護士結婚,他們有了一個兒子,兩人先後調到天津某部醫院工作。
1990年夏天,我也調到天津駐軍醫院,同在一個城市,彼此心裡很親很近見面卻很少,我見他就想起瓊玉姐,他見我就想親孃,我們都會傷心難過。我每次打電話瞭解他的近況,說不了幾句就哽咽淚下,蔡明總是懂事的轉移話題,讓我多開心多保重。
瓊玉姐啊,相信你的在天之靈,一定會保佑兒子一家人平安健康,幸福吉祥。
袁志軍
【作者簡介】袁志軍, 1951年5月出生於河北省邢臺市,1968年2月由保定七中應徵入伍。先後在駐津某分部、255醫院、254醫院工作,歷任打字員、衛生員、護士、醫生、政治處幹事、醫務處助理員等職,曾榮立三等功,上校軍銜退休居天津。自小喜愛文學,23歲發表處女作,堅持業餘創作,發表小說、散文、報告文學、評論達70萬餘字,為天津市作家協會會員。喜愛攝影,有500多幅攝影作品在報刊和新媒體發表,攝影作品多次參展,連續三屆入圍特倫伯奧地利超級攝影巡迴展,為中國老攝影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