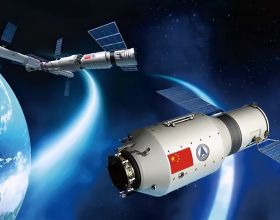我十歲左右,母親已經六十歲了,從我記事起,媽媽就是一個老太太,她因為年輕的時候,受了太多的苦,老了就渾身的病,咳嗽哮喘、高血壓。
那時候太窮了,娶完七個嫂子,我們家已經可以說家徒四壁,家裡就有三個水缸,一個放醃製過冬的酸菜,一個放土豆,另外一個放米。冬天買不起煤,就靠拾柴過冬,我每天都要出去拾柴,十歲左右拿把斧頭,在寒風凜冽中,砍那種死樹墩,有一次差點砍到自己腿上。母親老了,常年勞累過度讓她脊背有些彎曲,面容憔悴不堪。肺虛和缺乏營養也讓她極度的疲勞。她總是說趕快長大吧,什麼時候把你聘了,我就放心了,看那架勢,她恨不得十幾歲就把我嫁出去。
父親和母親經常吵架,他們一吵架我就心裡特別難過,我就會躲在村子後面的墓地裡。總是後悔來到這個世上,希望我趕快離開或者逃走,從小到大,除了年老的父母,就是七個年齡相差甚遠的哥哥,我羨慕人家有姐妹的女孩,至少也有個說心裡話的人。
冬天拾柴,夏天挖豬草,秋天拾田,這些我們這代六零後沒怎麼幹過的,我都幹過。十四歲,我就當家了,家裡的一應人情往來,來客人端茶倒水做飯支應都是我。這倒好,早早培養了我獨立自強自立的品性,我從此不再是一個孩子,而是一個大人,我會放學回來寫完作業就手拿鐮刀去割羊草,我會夏天天矇矇亮的時候,把提前晚上堵上的雞窩開啟,把雞用一路撒玉米豆的辦法引領到大隊部的場院,因為我發現場院裡很多秸稈上殘留著糧食。傍晚我再去把它們叫回來,如此七天以後,它們再也不用我引領,自己去刨著吃,飽了回來喝水。那時候別人家的雞冬天就不下蛋了,我們家的雞因為吃的飽,一冬天都在下蛋。場院一般都在村子外面,就是怕雞鴨豬遭害。我的雞就像訓練有素的隊伍,按時出去,到點回來。雞的問題解決了以後,我再考慮豬,挖豬草是我最頭疼的事情,我一邊上學,一邊挖豬草,那時候一放學,就是早上去學校,中午一點放學,下午不上課。我下午就需要挖明天一天的豬草,可是有時候下雨天就挖不成了,豬就得餓著。我從我媽冬天醃製酸菜過冬,想到了一個辦法,既然人可以吃酸菜,豬也可以吃啊!我媽說當然可以,但是怕我挖不到那麼多,我就利用星期天,挖一整天的豬草,壓到大甕裡,上面壓一塊大石頭,灌上冷水。幾天以後它就發酵了,新挖豬草在陸陸續續壓進去。這樣再也不用擔心下雨天了,最可笑的是夏天發酵的菜會招致生蛆,那些蛆也讓我媽一起餵豬了,豬還特別愛吃,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增加了蛋白質了。
我從來沒有過童年、少年,別的孩子聚在一起玩跑公里、抓羊拐的時候,我在想辦法怎麼多挖豬草,十二歲,我認識了村子裡一個南方來的走資派,發現了我的新大陸,原來一個人可以擁有那麼多的書,別人躲之不極的人,我卻是欣喜若狂,偷偷天天去他家看書一小時,一開始根本不給我借,後來發現我是真的喜歡,就把那些他視為珍寶的書借給我,十二歲我讀了《紅樓夢》《三國志》十三歲,我看《資質通籤》那時候,雖然很多看不懂,但是,就是喜歡,一種無法說出來的愉悅讓我變得開朗活潑,不再糾結父母的爭吵,不再厭世,走路都哼哼著歌。書本讓我快速成長起來,書里人物故事就像我前世的朋友,我不再糾結我沒有時間出去玩了,因為我發現了一個更大的世界,我更加不願意和同齡的孩子在一起玩耍,因為她們熱衷的玩耍,在我眼裡不值一分錢。我沒有朋友,書本就是我的最好朋友和老師,我變得孤獨而快樂,在一眾小朋友和村裡人眼裡,我是那樣一個不合群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