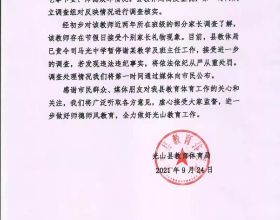“勒死他!勒死他!”我正睡著覺,突然聽到隔壁人聲嘈雜,把我從睡夢中驚醒,有意識地看了看錶:晚上一點鐘!
緊接著,聽到隔壁說:“死了!再也不會給我們找麻煩了!”
第二天,兩個人自己報了案,都被公安機關帶走了。
女的叫花,今年四十多歲了,長得面板細嫩,中等身材,看上去有三十來歲。二十多歲時搞了一個物件,開始由於父母不同意,過了五年離了,後來找物件總是不理想,時間長了,就跟這個好幾天,又跟那個男的好幾天,總是不如意,所以一直沒有結婚。最近遇到一個男的,比她小五歲,長得憨厚結實,很有力氣,二人就像乾柴遇烈火,一下就好上了。這個男的剛刑滿釋放,本來想好好過日子,可是近兩個月來,有一個叫胡鬧的人,經常上門找事。
找事的主要原因是:這個女人離婚後,跟著這個胡鬧在一塊廝混,胡鬧在她裝修房子的時候為她掏錢,還買了傢俱。胡鬧的錢從哪裡來呢?說白了就是他從別處偷來的,結果在一次作案中,被逮住,判了十幾年的刑,剛剛釋放出來。出來後,胡鬧看到原來和自己好的女人又跟這個小夥子好上了,便三天兩頭來要賬。
這天晚上大約十二點鐘。胡鬧喝了不少的酒又來要賬,三個人說著說著就打起來了,胡鬧被這兩個人:一人肋著脖子,一人抱著雙腿,活活給勒死了!
女人在家一定要守規矩,否則是會出問題的!
在我們這裡還有一個故事叫《無頭案》的故事。
張莊的貴田叔暴病死去,停屍三天,出殯葬埋。喪事總管是張吉祥,他辦事精細,不出閃失。多少年來,村裡的紅白喜事,婚喪嫁娶,人們都請他做主持。
貴田叔一生勤勞,家景富裕,暴病死去,一沒請醫,二沒用藥,兒女們心裡過意不去,想把喪事辦得體面一些,也算盡場孝心。出殯那天親朋好友,鄉里鄉親來了很多,總管張吉祥也精神了三分。
貴田叔的老伴,早在十年前病故。按照鄉俗,要把墳刨開,挨棺挖坑,夫妻合葬。張吉祥派了四個壯勞力去挖墳。挖墳人去不多時,王雨陽氣喘吁吁跑回來,慌里慌張對張吉祥說:“祥哥,了不得啦!貴田叔家的墳剛破土,刨出一個無頭屍。”張吉祥聽了這話,像傻了一樣,臉色變得刷白,唔唔地說:“別混說,別混說!”王雨陽更急了,極力辯解道:“這是混說的事嗎,不信你看看去!”
張吉祥腦子裡迷濛蒙,亂糟糟,在那裡站了一會,也不再說什麼,跟上王雨陽就走。鄉親們聽說貴田嬸的墳裡挖出個無頭屍,無不感到稀奇,也都跟著來到墳地。到地一看,果然有一具屍首,一半還埋在土裡。屍體早已腐爛,骨架倒還完整,只是沒有人頭骨。
這時,張吉祥似乎清醒了一些,和挖墳人把屍骨慢慢搬進一間灌田的水泵房,上了鎖,派人看守。村治保主任給縣公安局掛了電話。
縣公安局接到報案電話,非常重視,馬上開會研究,決定派科長和王明理來張莊破案。李科長外出執行任務,掛長途電話讓他速回,王明理當天下午就來到村裡。
王明理二十八歲,省公安學校畢業,頭腦聰敏,辦事自恃,進村只一天,便掌握了幾個重要情況。
七、八年前,村裡出過一件事,鬧得滿城風雨。有個外村來的風水先生,說過一段順口溜:“奇怪奇怪真奇怪,親哥倆雙胞胎,前世冤家轉世來。弟弟張吉祥,哥哥張吉泰,明爭暗鬥爭家財,一個世上享清福,一個慘死土裡埋。”
王明理覺得這條線索非常重要,想順藤摸瓜,一打聽,這個風水先生早死了。
張吉祥有個雙胞胎哥哥,叫張吉泰,十年前外出做小買賣。
一去不回,活不見人,死不見屍。從大田裡挖出無頭屍,村子裡街談巷議,紛紛談論。張吉祥好像傻了一樣,六神無主,這事很多人犯了猜疑。
還有人說,那幾年村裡常鬧鬼,有人在夜裡看見過一個無人頭的半截屍,晃晃悠悠在街上走,脖腔子裡發出呼呼地聲音,像是發洩什麼不平。王明理當然不信鬼,只是想從中發現什麼線索,問了一些人,也理不出個頭緒。
晚上,王明理微微鎖著眉頭,雙手插進褲兜裡,獨自在屋裡度來度去,心裡盤算著什麼。一抬頭,看見月光下有個黑影一閃。“誰?”“是我,同志,你是公安局的?”進來的人叫支蘭花,她原是張吉祥的老婆,外號大白桃,早已經改嫁給趙裕民。“有什麼事”“我,我替男人告狀。”大白桃哆哆嗦嗦拿出一封信,交給王明理。
信是張吉泰寫給支蘭花的,上邊有這樣幾句話:“都說老二膽小怕事,那全是假的,他心狠手黑,我擔心為了家產他會向我下毒手。要是有那一天,你一定要替我申冤報仇。”
大白桃哭得淚人一般,再三苦苦哀告:“同志,求求你,為我那屈死的男人報仇。”“這些年為什麼不早告?”“我,我不敢,害怕。”
經化驗鑑定,信是十年以前寫的。王明理叫人去找張吉祥。
張吉祥見到王明理,頭也不敢抬,手也沒處放,臉上冒出豆大的汗珠子,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看張吉祥嚇成這個樣子,王明理心裡明白了八九,他說話聲音不高,卻很有震攝力:“張吉祥!知道公安局為什麼找你嗎?”張吉祥一聽這,嚇得眼都直了:“我沒,沒害俺哥一。”王明理果斷做出決定,拘留了張吉祥。
王明理押著張吉祥去縣公安局,剛出村正碰上匆匆趕來的李科長。他向李科長簡要彙報了情況,臉上掛著得意的神色,在他看來,一樁人命關天的案子,他單槍匹馬進村三天,就搞出個眉目,也算是進展神速了。
李科長剛來,不瞭解情況,不多說什麼,只好叫他把人先押走。下午,王明理趕回張莊,把了解到的情況向李科長作了全面介紹。他還告訴李科長,孫吉樣被關進公安局,像是精神失常了,嘴裡反覆說著:“都怪我,都怪哥,我對不起你。”
李科長邊聽邊思考,最後提出兩個意見:一,要對大白桃進行調查瞭解。二,你說張吉泰不識字,信是託誰寫的,一定要了解清楚。王明理聽了冷冷一笑,這信是十年以前從外地寫回來的,想查出是誰代寫的,那還不是大海撈針。
兩個人正碰情況,張吉祥的老婆找上門來,滿臉淚痕地說:“我敢擔保,他沒殺俺哥,他怎麼敢殺人,誰不知道他膽小,連個雞也不敢宰。”
張吉祥老婆還反映一個情況,那年張吉泰外出做小買賣以前,有一天晚上,找到弟弟張吉祥說:“你嫂子有外心,不走正道,對我不懷好意,我擔心有一天他們要害我。”
王明理冷冷一笑,問她這事以前和誰反映過沒有?張吉祥老婆說沒有。王明理說:“這不結了,你哥死了十年,你不說,現在把你男人抓起來了,說這些話誰信。”“依我是要說的,可他不讓,他膽小,不敢說,那工夫村裡風言風語,他怕惹事。”
張吉祥老婆見公安局不相信她的話,哭著走了。
經瞭解,大白桃是小王莊人,做姑娘的時候就很風流,與本村的趙裕民勾勾搭搭,名聲很臭。趙裕民是有名的浪蕩公子,人稱趙大少。父母嫌她敗壞門風,做主聘給了張吉泰。
村裡還有人說過這樣一個情況,張吉泰有一手鋸盆鋸碗的手藝,每到春冬兩閒,就挑上挑子外出做活,一去就是一個月二十天。
這年,剛剛收罷大秋,張吉泰又挑上挑子,到外縣串鄉去了。村裡有個叫劉狗的,這人是出了名的懶蟲,農忙不摸鋤,冬閒不拾糞,整天溜來逛去,靠坑哄拐騙混日子。村裡人們看見他來了,家家插門閉戶,像避瘟疫一樣。
有天晚上,劉狗肚裡灌了二兩白乾,躺在炕上睡不著。他知道張吉泰出門去做小買賣了,大白桃是個騷貨,便想去尋歡作樂。他偷偷跳進張吉泰家院裡,正想敲窗戶叫門,就聽屋裡有男人說話。正在這時,忽聽張吉泰叫大門,急忙鑽進草棚子裡。
大白桃出來開門,問怎麼這麼晚才回來,張吉泰說天氣突然變冷,回來拿衣服。張吉泰剛進屋,“啊”了一聲就不言語了。就聽大白桃說“勒死他,使勁勒!”屋裡沒了聲音,大概是張吉泰被勒死了。
劉狗出來蹲在牆根,就聽屋裡兩人商量,要把張吉泰的頭取下來,以防萬一。劉狗聽了半響,也沒聽出那男的是誰。後半夜,男的向外背屍,大白桃故意把門開得很響,還煞有介事,假惺惺地喊:“已經回親了,等天明再走吧,著那門子急呀!”
劉狗跟著那人出了村,那人藉著月光,找到一個新墳,把土扒開,把張吉泰埋了。人頭埋在另一處。那人埋完屍首,沒有回張莊,奔了小王莊。劉狗尾隨在後,見那人進了一家大門,在門上畫了個記號。
劉狗回到張莊村外,把張吉泰的頭刨出來,埋到一棵歪脖樹下。偏巧下了一陣雨。
第二天,劉狗去到王家莊,找著那個門口敲了三下,有人出來開門。劉狗去到他家問道:“昨天晚上,你到張莊去了吧?”那人一聽,嚇出一身冷汗,連連說:“沒有,沒有!”劉知道人對了,又說:“你後來埋的那個圓東西,土地爺說那裡不可靠,給你挪了個地方。”那人咕通一聲給劉狗下了跪說:“大哥,你饒命,我給你錢。”
這件事唯一的對證就是劉狗,李科長和王明理叫治保主任去把他找來。
劉狗有四十多歲,小矮個,溜肩膀,長得尖嘴猴腮,下巴額有幾根山羊鬍子,兩個小眼一個勁眨巴。治保主任叫公安人找,他進門就表白:“我劉狗就是懶點,過門坎的事一點也不幹。”
問起這件事,他嘿嘿笑了,說那是吃飽了沒事幹,瞎編胡謅。
他還說:“我的話還不如放屁,放屁還有股昧,我的話沒一個人相信。”經向村裡人瞭解,人們也是這種看法,他們說:“雞蛋裡邊沒骨頭,劉狗嘴裡沒實話。”
公安局把張吉祥抓起來,趙裕民和大白桃暗暗高興,兩口子打酒炒菜想慶賀一番。剛把酒菜擱上桌,劉狗眯著小眼來了,他大模大樣走進屋,往飯桌旁一坐,也不等趙裕民讓,端起酒杯先幹了一個,又吃了一口菜才說:“趙大少兄弟,哥我遇上點壓手的事,你借我倆錢花。”
趙裕民滿臉陪笑:“自已哥們,好說好說,用多少?”劉狗把臉一繃:“少了不行,得一千塊。”趙裕民咧咧嘴,強笑著說:“我想辦法,我想辦法。”
劉狗告訴裕民,公安局的人找過他,問張吉泰的事,叫他給敷衍過去了。
趙裕民最怕劉狗,過去他就說過:“我一句話要你小命。”以前隔三差五的借錢,從沒還過,今天還不是又來趁火打劫。錢可以花,恐怕多少錢也封不住他的嘴。想到這,他一邊給劉狗斟酒,踩了大白桃小腳尖一下說“你去拿瓶好酒。”又向她使了個眼色,大白桃心領神會,又拿來一瓶上等酒給劉狗滿滿斟了一大杯。劉狗早喝得半醉,一飲而盡,又一連幹了三大杯。想吃菜,忽然覺得肚子疼起來,哎喲一聲倒在炕上,翻滾了一陣子不動了,嘴裡吐出白沫。趙裕民向大白桃說:“快,去叫人!”
大白桃到街上只喊了一聲,公安局李科長便首先來到他家,只見劉狗趴在炕上不醒人事,趙裕民也捂著肚子在地上翻滾。李科長叫人馬上把他們送醫院搶救。
公安局早把裕民、劉狗等幾個人,做為重點懷疑物件,對他們的行動暗中監視,所以大白桃只喊了一句:李科長。便趕了來。
劉狗在醫院裡昏迷了兩天一夜,經多方搶救,才脫離了危險。
這時,公安局的李科長和王明理來到病房。劉狗一見李科長和王明理,十分緊張,氣喘呼籲辯解說:“我心裡沒鬼,不是自殺。”醫生告訴劉狗,他喝了農藥,要不是公安局的李科長和王同志送來搶救,早見閻王去了。
劉狗聽了這話,如夢方醒,氣得大罵趙裕民,他說:“李科長,王同志,勒死張吉泰有那碼事,就是趙裕民乾的。我知道人頭埋在哪,走,叫人跟我刨去”
人們找來鐵鍬,用擔架抬著劉狗,來到找到那棵歪脖樹。劉狗指著露出地面的一個樹根說:“就挖這。”果然刨出一個人頭骨。
根據劉狗提供的情況,又對張吉泰那封信進行了驗證,確定是趙裕民的筆跡。經請示局領導,拘留了裕民。局裡科長李景明提審趙裕民,問他為什麼酒中下毒。趙裕民非常狡猾,根本不承認下毒,理由是要知道酒中有毒,自己還能喝。
提到張吉泰那封信,趙裕民毫不隱諱,說是有一次在外鄉碰到了張吉泰,孫求他代寫的那功夫還不知道後來和支蘭花成為一家。
問起張吉泰被殺的事,趙裕民態度坦然地說:“要是張吉泰真的被害,我是應該懷疑,他老婆成了我的老婆,叫我也得懷疑。不過,我們是張吉泰多年沒音信,經人介紹結婚的。除了劉狗,還有誰證明我殺了張吉泰。誰都知道,劉狗是個無賴,他的話沒一個人信。再者說了,地下的屍骨多得是,怎麼能說這個人頭骨就是張吉泰。”
趙裕民矢口否認殺害張吉泰,劉狗的話出爾反爾,又不能全信,再沒有別的證據,屍體是否就是張吉泰不能確定,無法定案。
公安局領導決定,派人到國家科學院,去為人頭骨畫像,以斷定是否張吉泰的屍骨。李科長要繼續留在張莊,決定派王明理和民兵王雨陽二人,背上人頭骨到科學院去。王雨陽娘聽說,堅決反對兒子去。村子裡前些年就鬧鬼,現在真的刨出個無頭屍,她怕陰魂把兒子叫了去。經李科長村幹部再三做工作,雨生娘才勉強答應了。大隊釘了個木箱子,把人頭骨裝好,縣公安局開上介紹信,王明理和王雨陽出發上路。因要到省公安廳換信,晚上住在省招待處,兩人住三張床位的房間,木箱子放在另一張床下。他們跑了一天,著實累了,洗了洗上床睡覺,剛剛把燈關閉,就聽那張床下“吱吱”地響,雨生頭髮根子一怔,說:“有鬼!”王明理雖說不信什麼鬼神,那聲音也聽到了,也有幾分害怕。只是因為自己是公安人員,才大著膽子說:“怕什麼。根本沒鬼。”還故意咳嗽了幾聲,吱吱聲沒了。
剛想入睡,床下又吱吱響起來。王明理穿鞋下了床,貓著腰去聽那箱子,終於弄明白了,原來是床頭的暖壺響。他把暖壺蓋按了按,聲音沒了。
科學院按照人頭骨,畫出人頭像。雨生看了和王明理說:“沒錯,就是張吉泰。”二人回到縣城,又回到張莊,經鄉親們辯認,都說就是張吉泰。李科長讓人把大白桃叫來,拿出人頭像說:“你看這是誰?”
大白桃當時嚇得吼了一聲,連連認罪,承認張吉泰是趙裕民用繩子勒死的,回到縣公安局,再次提審趙裕民,唸了大白桃的口供,又拿出人頭像。證據面前,趙裕民知道無法抵賴,低頭認罪。真相大白張吉祥釋放回家。縣法院在張莊村北,召開萬人公判大會。殺人犯趙裕民被判處X刑,同案犯支蘭花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
有人編了兩句順口溜:冤有頭,債有主,違法遲早要敗露;守法紀,莫害人,犯罪必遭受苦刑。
常言說:不報不報,時刻未到,時刻一到必定要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