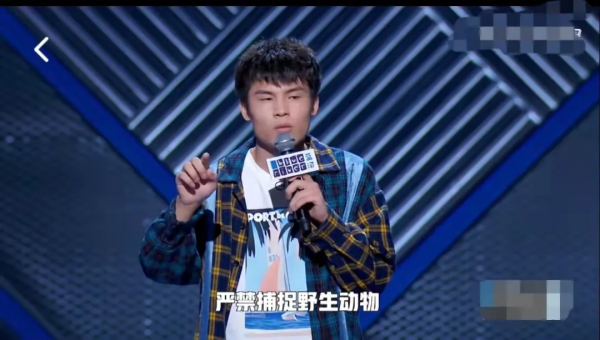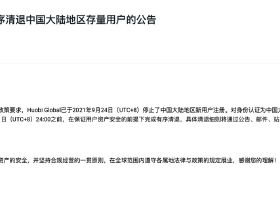《脫口秀大會》看到第四季,仔細回味,印象最深的還是第三季的何廣智,出場時李誕介紹他線上下已經講了一年多,但是在線上表演還是第一次。
初出場的何廣智,一眼看過去,純真樸實中似乎還帶著點土,總體給人感覺醜萌醜萌的。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的醜可攻可進,李誕的醜,可攻不可進。他的萌,更像是一顆未經雕琢的璞玉,一個人站在臺上,把自己的真實生活經歷掰開了,揉碎了,反反覆覆地講,引得臺下的觀眾鬨堂大笑,隔著螢幕也能感受到大家的共鳴。
第三季的第一期的何廣智,要參加一個“能讓我洗面奶洗臉的節目”,為了好看,去理個髮,結果頭髮理得不好,乾脆燙頭髮,就這麼一句話能說清的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事,居然貫穿了整場,笑點頻出。那個穿著明黃色夾克的他,看上去很是無辜,像故鄉隔壁的某個出遠門打工的鄰居小兄弟。
到了第二場,主題是關於錢的事,他說他住在寶山,一個地鐵終點站都到不了的地方,在地鐵的終端,還要騎共享單車,那個地方還立著“嚴禁捕捉野生動物”的牌子。月薪1500,跟年收入千萬的人差不了太多:都沒有壓力。還有一個共同點:都比較關注慈善事業,關注那個捐款名單上有沒有自己的名字。
也許是第一次出場太爆了,第二次出場他只得了兩盞爆燈。資深拍燈人羅永浩沒有給他拍燈,不過,我個人認為他的第二場遠比第一場精彩,除了語速略快了一點外,傳達的資訊要比第一場豐富了許多。從個人的困境,到在滬上交社保、買房以及慈善,涉獵的話題面很廣,引發的共鳴也更強。
不管是因為剪頭髮導致的燙頭髮引發的窘迫也罷,還是在魔都月收入1500房價漲個一兩萬我根本不關心也好,或者住在地鐵的終端“嚴禁捕捉野生動物”也好,說到底,都反映了普通人的生活最真實的一面。不是說中國還有六億人月收入不過1000嗎?倘若讓這月收入不過1000的六億人來看何廣智當時的脫口秀表演,一定是極其能夠引發共鳴的,他在臺上表演,坐在臺下看演出的人,或者隔著螢幕看演出的人,一定都會在想:他說的就是我呀!那個被託尼老師燙頭髮燙壞了從此頂著一頭尷尬的人,那個上下班單程要擠地鐵吣裡哐啷乘坐一個多小時的人,那個看看自己的銀行卡對買房根本就不作奢望的人,可不就是多數人生活的真實寫照嗎?
這也就很好理解,上一季的脫口秀表演中,李雪琴為什麼會脫穎而出。每當李雪琴往臺上一站,口裡吐出喪喪的一句“哎呀”的時候,可不就是我們生活中想要表述卻又時常無人傾訴的無奈嗎?儘管李雪琴北大畢業,早已成為網紅,收入想必也不菲,可是人家不說,拋開這一點,她的一聲嘆息,才是贏得更多人共鳴的地方:生活中的我們,有多少時候需要嘆息的?有多少時候希望有人聽到自己的嘆息,然後向你投來了一個意味深長的眼神,那眼神在告訴你:我懂的!不用說任何話,這就足夠了!
所以當那個凡爾賽女王蒙淇淇在網上橫空而出的時候,下面的評論幾乎是罵聲一片,上了《吐槽大會》,只獲得了最低票,當她走上臺的那一刻起,沒有開口,很多人在心裡面已經給她投票了。你明明不用費力,已經活得比多數人都好,那不是你自己的本事。當別人還處於吃不飽穿不暖的階段,你頻頻地向他人展示著朱門酒肉臭了。自己有肉,為什麼不能把肉埋在碗底吃?還要拿出來,在飢餓的人面前曬一曬,弄出一句“何不食肉糜”?這不是拉仇恨又是啥?
很多人也正是因為那句“我姓房,黃浦區兩套房的房”對Norah投了反對票,儘管大家都在說Norah很厲害,可以在脫口秀中用中文、英文和日文三種語言像母語般隨意切換,可是觀眾的票還是不願意投給她。倘若觀眾中多半是像何廣智那樣,住在地鐵的末端下來還要騎共享單車的青旅,每天要面對不同的人解釋至少七遍自己是什麼職業,你那黃浦區的兩套房對他們來說,又意味著什麼。
前些天氣溫驟降至零下,有學生問我有裘皮大衣嗎?我被他問得一頭霧水,怎麼突然問出這個問題?他告訴我,某某老師說有裘皮大衣。我看了一下自己,就衝著我這身高不足一米六的樣子,整個裘皮大衣在身上,恐怕非但穿不出裘皮大衣的模樣來,還把自己整成個球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