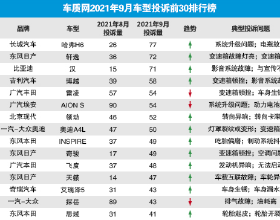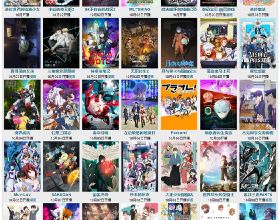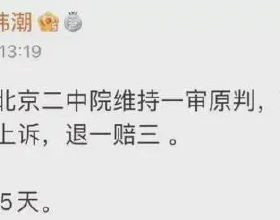在八部電影組成的哈利·波特系列中,第三部《哈利波特與阿茲卡班的囚徒》是承上啟下的一部,觀眾成功地由睡前童話故事般溫馨、輕盈的小巫師奇遇記過渡到陰森、緊張又殘酷的魔法世界傳奇。
也正是從這一部電影開始,哈利·波特系列擺脫了兒童電影的限定,邁向了影片全年齡、全球化的成功。
成功的改編
哈利十三歲的暑假過得並不如意,不堪忍受瑪姬姑媽對父母的侮辱,他違反了魔法部的規定,對普通人使用了魔法。然而魔法部非但沒有制裁他,相反,大家看到他平安無恙便個個如釋重負。
哈利得知,這是因為史上最兇殘的殺人犯小天狼星布萊克逃出阿茲卡班巫師監獄,正在追殺他。
在回校的火車上,哈利被阿茲卡班的守衛攝魂怪嚇到昏厥,幸得盧平教授出手相救。一次意外,哈利獲知布萊克竟是向伏地魔出賣父母的罪魁禍首,在尖叫棚屋,布萊克與盧平教授、哈利和他的朋友們遭遇,魔杖相對之際,暴露出的真相卻出人預料。
如果說改編歷史文學名著的挑戰在於還原歷史,那麼改編哈利·波特系列這樣的超級流行商業電影則是多重地“就著鐐銬起舞”。如何構造一個不存在的魔法世界?如何在不激怒粉絲的同時保持自己的導演風格?如何通俗而不媚俗?
好塢“墨西哥三傑”導演之一的阿方素・卡隆成功地在大眾與個性、商業與藝術之間找到了自己的平衡術。
完全不同的風格
與系列前兩部的粉絲型導演不同,在拍攝之前,卡隆並沒有讀過原著,他一改前兩部平實、穩重的影像風格,大膽使用黑色、藍色作為主色調,加入暗黑魔法元素,運用了複雜的鏡頭語言和剪輯技術。
以破釜酒吧客廳段落為例,哈利見到了為寵物爭吵的朋友、瞭解了韋斯菜一家的埃及之行,韋斯菜先生告訴他佈菜克在追殺他,一切發生在破釜酒吧的客廳內,短短的兩分鐘的段落,然而布光與音樂風格卻巧妙演變。
當韋斯菜先生開始勸誠哈利遠離布克時,此前好友團聚的環境氛圍已經為之一變,陰冷的光自拱廊外打來,布萊克的通令橫亙在二人中間的牆壁上,歡快的埃及風情音樂突然變奏成不和諧的噪音。在視覺效果上,卡隆也延續了他個人的陰鬱的影像風格。
於是,這一次,魔法世界從火燭通明的城堡向莽蒼的荒野和黑夜延伸,攝魂怪打人柳、尖叫棚屋、鷹頭馬身有翼獸展現了魔法世界危險的面向。
除了個別段落外,本片幾乎被冷色調覆蓋,在大片密集的黑色中,微弱的光源來自蠟燭、月亮或魔杖尖的微光。魔法世界沒有白熾燈,真相和危險藏在陰影中。
戰勝恐懼
類似的影像風格同影片的敘事彼此呼應。
在前往霍格沃茨列車上,當哈利沉思的臉龐透過被雨水打溼的窗玻璃出現在銀幕上時,我們知道,少年英雄的心靈旅程將取代魔法冒險,成為系列電影第三部的主旋律。
哈利要面對並戰勝的不僅是作為邪惡代表的大魔頭,也是自己內心深處的恐懼、軟弱和仇恨。卡隆多次使用鏡子水面、鐘表盤、車窗等道具,形成人物與自己的鏡中像兩兩相對的時刻,凸顯出敘事的內心維度。在魔法世界中感受自我與真實。
哈利不再是個全然無畏的小英雄,他將暴露了自己面對攝魂怪時的脆弱,得知布萊克是殺親仇人時的暴怒,這些人性的弱點讓哈利的形象有了心理深度,也讓全系列“成長的主題變得更深刻:成長不在於擁有更厲害的魔法力量,不在於獲得名聲和地位,而在於能直面自己內心的傷痛和軟弱並戰而勝之。
影片高潮部分,在攝魂怪密佈的湖邊,哈利期待著父親的守護神出現,許久之後,他終於領悟到,能召喚出守護神的只有他自己,而施咒的成功與否取決於他能否戰勝自己的心魔。他做到了。這正是羅琳嘗試傳達給讀者的。
今天英雄不來自上天神賜,不來自國王命名,一個人從擺脫對父輩的依賴,超越權威蔭庇的那一刻起,他便踏上了成就自我之途。哈利·波特系列的全球流行不只在於魔法世界有多酷炫奇異,而且在於它將青少年成長故事和瑰麗的奇幻想象奇妙地交融在一起。
尋找真相
奇幻文學中的常見主題,比如魔法與尋寶、正義與邪惡,化作羅琳筆下的哈利尋找魔法石、在密室中勇鬥伏地魔,《阿茲卡班》則多少溢位了奇幻文學的疆界涉及了紀錄與真相間的複雜糾葛。
在小天狼星一案中他的“罪行”有眾多的目擊證人,但眼見未必為實,所謂證人顯然為可以營造的障眼法所矇蔽,小天狼星一度成了幹夫所指的殺人狂徒,但那份社會論事實上只為公眾的恐慌心理所支撐。然而當哈利和他的朋友們發現了真相後,情勢卻沒有即刻明朗反轉:
魔法部的官員們意味推卸責任而非昭雪沉冤,小天狼星仍不能得到公正對待,這是縱有魔法也無助無力的時刻。但是,正如盧平教授所說,現實或許不需要真相,但歷史需要,真相是唯一能告慰受害者的東西,也是十三年絕望侵蝕下不會更移的東西。
在《魔戒》《地海傳奇》等優秀的幻想文學中,“真實”有著強大的魔力,喊出事物的“真名”即可征服它,這不僅是簡單地重申善惡真偽的古老寓言,更是要提醒人們要在迷惑紛亂的現實中保持清醒和勇氣,不畏懼直面並擔當真相。
作為一部奇幻電影,《哈利・波特與阿茲卡班的囚徒》沒有飛天遁地的絢麗場景,沒有奪人心魄的打鬥場景,這份來自導演的節制在動輒神奇特效的電影工業中顯得另類又透:我們被魔法吸引,不只於在它是一場浪漫無邊的幻夢,而且在於奇蹟的盡頭,我們或許會遭遇到自我與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