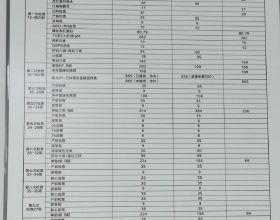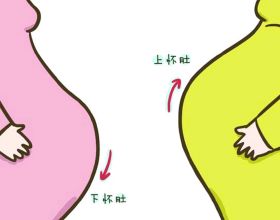幾年前,我在婦產科輪轉的時候,遇到了一個非常特殊的患者。和其他科室不太一樣,來產科入住的大多數人都只是普通孕婦,她們來醫院只是為了生產或者保胎,某種意義上來說,
她們稱不上患者。可是她卻不一樣。
她也是孕婦,懷孕有24周了,屬於中妊期間,可是我看到她的入院證上還填著“肝癌伴肝內多發轉移”這一突兀的診斷。
輪轉產科期間,雖然科室沒有安排獨立管床,但是一般的醫患溝通也是交給我們這些輪轉的醫生去做的。可眼下,我多少有些踟躕。
醫院裡從來都不缺各類年輕的絕症患者,工作久了我也沒空傷春悲秋。可她才25歲,這是她第一次懷孕,原本她該是滿心歡喜地等待新生命的到來,卻晴空霹靂的接到這樣的噩耗。同樣亟待“處理”的,還有她肚裡的孩子。
因為肝癌對母子倆的威脅都很大,胎兒只有24周,是很難等到足月分娩的。
我原本以為,這樣的醫患溝通註定是艱難的。可是在和她正面接觸的那一刻,我發現,她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樣。她的面頰、四肢都很消瘦,因為腫瘤的原因,腹圍卻明顯比正常的妊娠週數要大了一圈。和周圍那些面龐豐潤、精氣神十足的孕婦相比,她確實要顯得憔悴許多,不過那雙眼睛卻還是精氣十足,完全沒有一個絕症患者眼裡特有的灰暗和頹廢。
站在她旁邊小心伺候的是個50多歲的婦人,看著一臉憂心忡忡,卻又極度耐心體貼的模樣,便知道是這姑娘的親媽無疑了。在產科工作一陣,不用家屬特別說明,醫生很容易就可以從一些小細節裡分得出產婦的親媽和婆婆。
大部分的癌症患者都不是第一個知道自己病情的。家屬往往隱瞞病情,最後實在瞞不下去了,再選擇向患者本人攤牌。能被瞞住的,大多數都是老年人。姑娘只有25歲,她應該在家屬和醫生的欲言又止中猜到了自己的病情。
“怎麼發現這個病的?”
為了不讓這次談話那麼沉重,我索性在她床邊的凳子坐了下來,試圖拉近一些距離。我不確定她對自己的病情瞭解到哪個程度,所以也是小心試探,並揣摩著她可能的打算。
她之前可能沒怎麼和臨床醫生有過太多接觸,看得出她有些緊張,兩隻手不自覺地絞著被單,偶爾會和我對視一下,但很快又盯著自己的手指。“醫生......”她的母親打斷道,勉強擠出一絲笑容,衝我努力眨了眨眼。
“前兩天打彩超,醫生說孩子發育有些問題,我們就是來引產的。她沒什麼毛病,就是有點營養不良,貧血也重。我們住過來,順便也輸點營養液,再輸點血,給她調理一下。”
“我都知道了。家裡人一直沒和我說,但是我看到彩超單上寫的考慮肝CA,我知道那是啥意思,就是癌唄。”她的語氣很輕鬆。
她的媽媽有些尷尬,不再說話,從袋子裡翻出一個蘋果來削皮。大概是心事太重,她削得很慢,果皮斷了好幾次,直到露出的果肉有些發黃了,她才著急削下一塊,遞到女兒嘴裡。
“哎呀,你也別有那麼大負擔,現在得癌症的人多得很,醫療條件又比以前好多了。只要發現得早,治療及時,還不是有好多人治好的,和正常人一樣生活。”她的媽媽一邊寬慰著女兒,一邊繼續衝我使勁眨眼。
一時間,我沒想好怎麼接話。癌也分為很多種,是有一些癌症的預後相當不錯,比如說甲狀腺癌或者絨癌,很多患者單純經過手術、化療等常規治療手段就可以完全達到臨床治癒。可肝癌不一樣,和胰腺癌一樣,稱得上癌中之王,預後非常差,且五年生存率非常低。
當然,這些也還不是我們這次談話的主要內容,她現在入住到產科,我們需要直面的,除了她的腫瘤,還有她腹中胎兒的命運。
其實在上級醫生安排我來和她談話之前,科室的醫生們已經對她的疾病做了討論。
她的影像學檢查提示,肝臟多處的腫塊都伴有靜脈曲張,這也意味著,隨時都有可能出現門脈高壓引起消化道大出血,而且這些腫瘤也隨時有自發性破裂出血的可能,無論哪一條,都是可以在短時間就迅速致她於死地。好在她的肝功能尚可,凝血功能也還將就,科室商議後,給出的建議還是先儘快終止妊娠。
可這個胎兒才24周,按當年教科書上的標準,這樣的胎齡可以被定義成流產兒或者無生機兒。雖然這些年也有不少胎齡和體重均極低的新生兒存活的報道,但這並不能作為常規推廣。胎齡越小,體重越低,死亡率就越高。
哪怕即使勉強保下來,新生兒患有腦癱、膿毒血癥、肺炎、腦室出血等各類風險和併發症也是成倍地升高,救治的難度太大,而高額的花費也足以勸退很多普通的家庭。
所以所謂的終止妊娠,就是建議她直接引產。
這個話題我還沒有正式提到,可聽她媽媽的意思,也是要把這個來得不是時候的胎兒打掉,給自己的女兒爭取一點治療時間。
可是,畢竟還是得徵求患者本人的意見。
接下去的談話,我沒有刻意去問她本人的打算,而是選了一些相對輕鬆的話題聊天。慢慢的,她也放開了一些,不似先前那般拘謹。在閒談間,我對她也多了一些瞭解。
她家裡的條件並不寬裕,高中畢業就進廠裡工作了,還要供妹妹讀書,業餘的時間就在淘寶上鼓搗些小生意補貼家用。前些年,她談了個男朋友,兩人收入都不高,但一直節約慣了,兩方父母都沒幫上什麼忙,但也在房價大幅上漲前上了車,按揭買了房結了婚,年初又查出懷孕了,眼看著一切都往好的地方發展。
懷孕後,她也在醫院定期做產檢,每次產檢,也都沒發現什麼異常。只是從這兩個月開始,她發現自己的體重不增反降,每天都感覺有些噁心、厭油、精神萎靡,起初她一直當是妊娠反應,也沒重視。直到最近,她經常出現上腹疼痛,腹圍增大得有些誇張了,才讓她媽媽逼著來醫院做系統檢查,發現了這個病。
在國內,絕大部分的肝癌都是由病毒性肝炎或者長期大量飲酒導致,可是她沒有病毒性肝炎,也從不喝酒,甚至連家族史都沒有。我們也推測,她這麼年輕就得了這個病,或許和早些年在化工廠工作,長期接觸亞硝胺類化工原料有關。
聽到這裡,我有些替她惋惜。肝臟上沒有神經,很多肝癌早期都沒什麼明顯症狀,加上妊娠期也會出現噁心、厭油、腹部膨隆等表現,更加容易漏診。她做了好幾次產檢,都沒有哪個醫生想著給她的肝臟順便一起打個彩超。
聊了一會後,還是她先把話題轉移到這個孩子身上,“孩子還在我肚子裡,現在肚子裡又長了腫瘤,這個癌症不會傳染給孩子吧。”
她有些顧忌,但顧忌的物件卻不是自己。
“不會。”
“那我就放心了。”
在得知癌細胞不會直接傳染給胎兒,她明顯比先前放鬆了很多,那表情像是獲得大赦一樣。和正常的孕婦一樣,翻來覆去的,她提到的只有孩子的事情,她自己的病,倒是沒怎麼過問。接下來的治療方案,她也一點不關心。
我決定試圖轉移這次談話中她關心的重點,也就不便再閒聊,強行說到了重點。
我直接說:“在妊娠期間,由於母體內分泌增強,加之胎盤分泌大量的hCG、雌激素等,這些都可以加速癌細胞的生長繁殖,會加重病情並促進疾病惡化。胎兒現在還小,各方面發育都不成熟,現在勉強剖出來也很難存活。”
“那就先不剖出來,在我肚子裡先養著。把孩子養大一點再剖出來,我肚子裡雖然有瘤,但孩子待在裡面也比硬剖出來養不活的強。”
她的語氣和表情都很平淡。
“給你說了,不要了,先治病。”見她完全沒意識到疾病的風險,她的媽媽有些著急,“你這孩子咋這麼死腦筋呢,我們都聯絡到腫瘤醫院了,等孩子一打,就趕緊轉過去。後面還得接著做治療呢!”她的媽媽已經開始帶著哭腔。
“媽,這些天我就沒閒過!你們以為我什麼都不知道,其實我都想過了,不打算治了。我查過了,這個病沒得治,花錢拖時間而已。”
她的態度明確,我不好再說什麼。
我只能將病人和家屬的分歧轉達給上級醫生。沒多久,她的孃家人、婆家人陸續都來了醫生辦公室,兩家人的態度都很明確,不要孩子,先給大人治病,她丈夫的態度尤其堅決,就算賣房子,也要先給老婆把病治了。
都說醫院是世態炎涼、人性善惡的修羅場,那產科更是其中的集結地。在產科的這些日子,我們見多了那些滿心歡喜地圍著新生兒轉,卻將疲憊不堪的產婦晾在一邊的家屬,多少都為這個不幸患癌的姑娘感到些許欣慰。
雖然家屬一致要求不要孩子,但患者本人完全有自主決定能力,在兩方的膠著中,我們也不好給出接下去的治療方案,只能給她做一些營養支援措施,同時加強支援治療。
接下來的日子,每天早晨去查房,我都看到她平靜地端坐在床上,看一些育兒書籍。
有時候,她還放一些音樂給未出生的孩子做胎教。而她的身體以肉眼可見的速度一天天衰敗下去,可那雙眼睛卻始終看不出任何絕望和頹廢,甚至還像很多普通孕婦一樣,摸著肚皮,感受到胎動時也會流露出喜悅和希冀。
然而,這樣的僵持並沒有維持太久。
有一天夜裡值班,我聽到病房裡傳來激烈的爭吵,聽出是她的聲音,便前往她所在的病房。在吵鬧間,我聽出了她媽媽的意思,他們一家人還是決意先不要這個孩子,要選擇對她更好的方案,引產後去做介入治療縮小瘤體,想辦法買靶向藥。他們一家人也開始籌劃著賣房,考慮有機會了,就給她做肝移植。
她的媽媽哭紅了眼,“醫生都說了,就算現在硬剖出來不死,也要在保溫箱住著,花個十幾二十萬都沒個準,說不定還落個人財兩空。”
“所以我不治了,醫藥費留著給娃兒用,娃兒肯定拖不到預產期。”她回答得倒也乾脆。
“你要我跪地求你嗎,從小都那麼聽話,咋越大了就越不懂事呢。全家人都求你了還不成,這娃兒硬生下來不也是一輩子沒媽!”
說到“一輩子沒媽”,這位母親意識到自己戳中了女兒的痛處,趕緊住口了。
“你要救你的娃兒,我就得殺了自己的娃兒嗎!”她衝母親吼道。
這些天,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哭。
“我才打了四維彩超,都能看到娃兒的臉了,啷個能說不要就不要了。醫生每天來做胎心監測的時候你們不也都在場嗎,那是個活人的心,你們怎麼就能當這娃兒不存在的!”
末了,她幾乎是聲嘶力竭,發了狠話,“你們誰再讓我打了這娃兒,我就從樓上跳下去!”
在她的強烈堅持下,她的家屬終於斷了念想。
接下來的日子,家屬們都和她一起等著這個孩子在她的身體裡孕育。可這也是一場冒險,胎兒在生長,腫瘤也在生長。她的腹圍增長得很快,腹部膨隆得像一隻鼓氣的河豚,腹壁靜脈曲張得愈發誇張,像只巨型的蜘蛛匍匐在她的腹部。與她碩大的腹部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她日益枯竭的四肢,腫瘤和胎兒都在消耗她。
有次查房時,碰巧遇到她有胎動,她的腹壁被撐得很薄,胎動明顯,她歡欣雀躍地叫著,讓病房的醫生和家屬也來瞧瞧,看她還未出生的孩子有多麼活潑好動。也是在那天,她在家屬的攙扶下,到醫生辦公室裡簽署特殊溝通。
在醫生們反覆向她強調,肝癌結節破潰以及靜脈曲張破裂都有可能導致大出血,隨時危及母子倆的生命,建議及時終止妊娠,並積極治療腫瘤相關疾病,她淡然地寫下:要求繼續妊娠,只予以基本保肝、營養支援對症治療,後果自負。
“不再想想嗎?”我的上級醫生再次提醒她。
積極治療的話,再怎麼樣都比這麼幹等著好些。她的丈夫見醫生在這個時刻都還在勸導,像又看到了一絲希望,便又趁熱打鐵,“我們也在腫瘤醫院問了,還能吃靶向藥,也可以做介入,免疫治療什麼的。實在不行,不是還可以換肝的嘛,錢沒了能再掙,人在就好。”
她笑得無比超脫又釋然,“我看了那個米蘭標準,換肝也得符合條件啊,我肝上全是腫瘤,小的那個都超過3釐米了,你們就省省心,別打那房子的主意了。房子賣了,你們到時住哪,娃兒落地了,沒了媽難道還要沒了家?”
我們詫異於她還查了肝移植的米蘭標準,看樣子,這些天她也下足了功夫瞭解自己的病情和治療方法。做出這樣的選擇,並不是一腔孤勇的意氣用事,的確是她深思熟慮後的選擇。
不過這個米蘭標準是有些過時的,國內的肝移植標準可以放寬很多。但是肝移植對她家人來說也的確只是一個美好願景,合適的肝源太少,而且費用太高。就連她老公剛才提到的那幾種保守治療方案,也無一例外都很燒錢。
接下來,她竟像交代遺言一樣,“娃兒肯定挺不到足月生產,後面肯定還得花不少錢,我這個病也就別折騰了,把全家都搭進去就為了多換個一年半載的,划不來。往後這個錢都得用在刀刃上。”她雖然年輕,也沒在這個節骨眼去考驗親情和愛情的濃稠,只是儘可能給自己的家人和未出生的孩子做了價效比最高的安排。
既然如此,我們也尊重她的選擇。
之後每次查房,我們感覺得出她的焦慮。她也是在“賭”,如果腫瘤比胎兒長得更茁壯,或者她的病情發生變化,母子倆可能都保不住。
28周,在產科是個很特別的時間節點,因為28周後出生的早產兒通常具備良好的呼吸能力,存活機率較大。而她的情況也快到了極限,實在不適合繼續妊娠。在多科室協同會診後,科室決定給她做剖宮產取出孩子。
因為產婦的特殊性,參與那臺手術的都是各個科室的大拿,我只能在一旁觀摩。
麻醉起效後,產科主任用了最快的速度將一個皺巴巴的面板青紫的女嬰從她的子宮中取了出來。這個和腫瘤共生的新生兒只有1100克重,正常體重的三分之一。新生兒監護室的主任和護士立即用吸引器將其口鼻內的分泌物吸淨,在反覆彈了幾次腳底,嬰兒才發出微弱的啼哭聲,而她還被固定在手術檯上,嬰兒已經取出,被切開的腹壁和子宮還需要逐層縫合。
這臺手術,給每個人都帶來極大的震撼。
剛出生的嬰兒,特別是這種早產兒,身上都混合著血跡、羊水、胎脂,大抵都是醜陋的,她在看到自己的孩子時,眼裡蓄滿了淚水。
在手術前,她就和科室醫生說,術後還是回產科住著,產科的病房佈置得溫馨,而且是醫院裡唯一充滿喜慶的地方,待在這裡能輕鬆些,比待在腫瘤科互相比慘等死強,而且在這裡住了這麼久了,和醫生護士也都熟絡了。
而和我們預料的一樣,她身體的各項指標在產後出現了迅速惡化,腫瘤生長得非常迅速,開始壓迫膽道,她整個人都變得愈發枯黃。
我們知道,她所剩的時間越來越少了。
精神好一點時,她會讓家屬推著到在另一棟樓的新生兒監護室去,聽管床醫生講講孩子的現狀。萬幸的是,聽監護室那邊說,她的孩子狀況還不算太差,那些最可怕的併發症沒有盡數發生在這個讓她冒死保下來的孩子身上。
而她一天比一天虛弱和衰竭,慢慢的,已經完全下不來床,由於出現了肝性腦病,她昏睡的時間也越來越長,偶爾醒著的時候,家屬就會給她看手機裡她女兒的影片——都是監護室的護士專門錄下來發給她的。
早些時候,她還會對影片裡渾身綁著各類儀器的女兒笑,每天給她加油打氣。
到了最後,她的丈夫整日地把手機放在她的眼前,她卻幾乎終日耷拉著眼皮。
死亡,一天比一天接近,沒有奇蹟發生。
一天中午,她在家屬和護士的協助下,在床上排便,長期臥床導致她排便非常費力。那天排便後,她忽然滿頭大汗,痛楚難當,那會她已經說不了話,只是把手放在腹部。監護儀上,她的血壓急速下降,心率也跟著下降,應家屬的要求,科室沒再進行徒勞的有創搶救。根據她的病情和表現來看,應該是肝臟上的腫塊破裂,導致的大出血讓她迅速進入休克狀態。
所幸的是,她最後走得不算太痛苦。
她的女兒,在監護室並沒有住太久,恢復得相當不錯,不過這些,她也沒機會看到了。
—結束—
選自《全民故事》,如有侵權,聯絡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