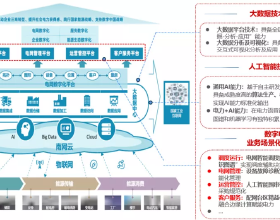畫以境出,幾朵微花,也別有風韻。
小小的曲廊所綰束的這個世界,竟然有浮空蹈影之感。
繚繞的雲,迴旋的山,清夏中消散的人,構成清幽曠遠的境界。
無風蘿自動,不霧竹長昏。
在中國美學史和藝術史上,境界往往作為衡量審美價值和藝術水平的標準而存在。
作為藝術鑑賞者,我們常說這個藝術品很有境界(在這個意義上,和意境同義),它說明了兩個問題,其一,境界是有差異性的,不同的作品有不同的境界;其二,境界是有層次之別的,有的作品沒有境界,有的作品有境界,有的作品的境界高,有的作品的境界低。由此二點,我們可以得出,境界是衡量審美物件規定性的一個標準,應該說在唐代以來的中國美學中,這是一個重要的標準。在中國美學中,衡量審美物件的標準概念有很多,如韻、味、格調等等,這些都和境界有一定的聯絡,但境界是一個與這些概念都不同的標準。
作為審美標準的境界到底有哪些基本內涵呢?用最通俗的話說,我以為,境界具有三個規定性,一是有內容,二是有智慧,三是有意思。
有內容
有內容,是說有境界的審美物件具有深刻的包孕性。用《文心雕龍》的一句話說,可以叫作“秘響旁通”——像悠揚的音樂,縷縷不盡,悠悠難絕。沈周題畫詩有謂:“松風澗水天然調,抱得琴來不用彈。”為什麼抱著琴來,卻不彈了,因為大自然就是絕妙的音樂,松風澗瀑中就是一個音樂的世界。這樣的詩就很有境界,用這樣的詩境作畫,非常有利於繪畫境界的提升。
中國藝術以“隱”為要則,強調象外之象,言外之意,韻外之致,景外之景,要含不盡之意如在言外。如梅堯臣所說:“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要超以象外,得其環中。強調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強調無畫處皆成妙境。言象是外顯的,是在者;言象之外是內隱的,是不在者。在在者與不在者之間,在者只是一個引子,一個將品鑑者引入到不在者的引子。不在者的世界愈廣大,愈豐富,在者的顯現就愈成功。因而在在者與不在者之間,不在者的重要性顯然要高於在者。
海德格爾曾經說過,人活動的是一個時間性的場地,或者叫在場,一切在場的“時域”——時空存在,都是由過去與未來構成的真正現實的現在。每個人目前的境界,就像一個“槍尖”,是過去與未來的集中點。在中國藝術的這一“引子”世界中,其實正強調的是其隱含性,藝術家所刻意經營的“引子”是一個最能顯現無限豐富世界的“時位”,它是一種凝聚,不僅在時空上凝聚過去與未來,在在者與不在者之間,充滿了一種意度迴旋,也就是中國美學所說的虛靈世界與質實世界的迴旋關係。如王維這首《書事》小詩,其雲:“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讀這樣的詩,感覺到無邊的蒼翠襲人而來,亙古的寧靜籠罩著時空,濛濛的小雨,深深的小院,蒼蒼的綠色,構成一個夢幻般的迷濛世界。詩人為我們創造了一個好的“引子”,為我們打開了通向迷濛世界的別樣通道。我們判斷“引子”的好壞,往往就是看它是否能調動品鑑者的想象力。
我們說這樣的不在者、這樣的無邊妙世界就是境界,或者叫作意境。它根源於象,又超越於象;境就是這象背後的世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美學的境界理論突出的一個思想,就是藝術創造的中心既不在“引子”,也不在這個“引子”背後所展現的全部世界,因為它沒有一個終極表達物件,而在於所提供的一個想象空間。中國藝術的造境,既不在創造者所獨有,也不會被品鑑者所窮盡,是一個永恆的可拓展的意韻空間。
有智慧
葉朗先生在論意境時,強調“意境”必須具有哲理性意蘊,誠為篤論。他說:“所謂‘意境’,就是超越具體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場景,進入無限的時間和空間,即所謂‘胸羅宇宙,思接千古’,從而對整個人生、歷史、宇宙獲得一種哲理性的感受和領悟。一方面超越有限的‘象’,另一方面‘意’也就從對於某個具體事物、場景的感受上升為對於整個人生的感受。這種帶有哲理性的人生感、歷史感、宇宙感,就是‘意境’的意蘊。”這裡沿著葉先生的思路再予申論。
境界的追求是為了超越具體的言象世界,言象會匯入概念,概念起則知識生,以知識去左右審美活動,必然導致審美的擱淺。以知識去概括世界,必然和真實的世界相違背。因為世界是靈動不已的,而概念是僵硬的,以僵硬的概念去將世界抽象化,其實是對世界的錯誤反映。
在西方哲學中,有所謂詩與思之別,以知識去說和以詩去說,是兩種不同的途徑,將呈現世界的任務交給詩。其實在中國,這樣的思想也有漫長的歷史,莊子哲學就強調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以知去言,只能得世界之小者,以自然去言,則能得天地之大全。而南禪的思路也與此類似,南禪接受道家之思想,其所謂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的道路,就是追求世界的原樣呈現。我們注意到,中國美學中境界論的大致形成是在唐代,其形成與莊禪哲學有密切的關係,在禪門的皎然、寒山和接近於禪道的司空圖、王昌齡、劉禹錫、張璪、劉商等是境界美學形成的中堅。他們以境去代替象,以境的言說方式去超越知識的言說,正是在詩與思之間向詩靠攏的反映。
知識是概括,境界是呈現,面對一個真實的靈動的世界,境界則成了最合適的途徑。境超越知,但並不意味放棄了智慧,它所超越的只是知識概念系統。思與詩二者之間在目的上頗有相似之處,都是為了顯現世界的真實相。詩的途徑非但沒有放棄對智慧的追求,而且將宇宙人生的穿透力作為其最高追求。也就是說,沒有智慧的境界是一種低等境界,缺少宇宙人生感的境界就顯得單薄了。
有意思
境界作為一種審美標準,除了具有內容的包孕性、思致的深刻性之外,還必須有韻味,耐咀嚼,有一種亹亹難盡的美感。有境界之作品擺脫了理智的拘束,任由世界自己呈現自己,讓世界說,還應以美的方式來說,缺少美感的物件,就不能稱為真正有境界。乏味地說,乾癟地說,單薄地說,都是一種說,這樣的說不能產生藝術的境界。
中國古代美學有喜歡用“味”來比喻美感的風尚,鼻之於香,舌之於味,是人的感覺器對外在世界的感覺,但它們與視覺、觸覺等感覺不同的是,其感覺是無影無形的,而且又有悠長的回味空間,故而為談藝者所樂道。《文心雕龍·隱秀》在論述隱秀的特徵時,就提出“餘味曲包”的重要觀點,司空圖在論述境界時,也以味來作比,他說,詩之妙,在“鹹酸之外”。有境界之好詩應該有“韻外之致”“味外之旨”。
境界是一個層深的結構,要在“曲”而“杳”,如人從羊腸道進入深山,慢慢領略山中的奇幻世界。第一境透過繁花綻放、落英繽紛、清暉散落的一群意象,意在創造一個迷濛奇妙、引人入勝的境界。如同人遠遠地望山,一座散發出無窮魅力但又暫時無法弄清的美的世界,使觀者無限嚮往。第二境所選擇的意象都富有力感和強烈震盪感,駿馬奔騰,鳶飛魚躍,瀑布三千尺,狂風捲巨浪,象徵著觀者深入這一世界,領略了無邊的妙境,感受到巨大的性靈震盪,物攝我心,此乃是走入物我相合境界的前奏。第三境是花開花落,雲捲雲舒,清月孤圓,獨鳥高飛,強調破除我執法執,解除物我之間的界限,觀者的角色消失了,一個外在的觀者,變成了世界的參與者、體現者,我就是白雲,就是清風,就是高飛的鳥,就是澄明的月,冥然合契也。從而進入第一義的上上之境。第一境是遠望有奇景,第二境是深入覺震盪,第三境是寄心明月自往還。第一境是我為物吸引,第二境是觀物識馨香,第三境是我融入物中,此境就是一個包含無邊妙境的深深世界,一個非悉心領悟而不能至的無上宮殿。
在中國美學中,人們感興趣的不是外在美的知識,也不是經由外在物件“審美”所產生的心理現實,它所重視的是返歸內心,由對知識的盪滌,進而體驗萬物,通於天地,融自我和萬物為一體,從而獲得靈魂的適意。中國美學是一種生命安頓之學,追求身心的安頓。它並不在意一般的審美快感,而力圖超越一般意義的悲樂感,所謂“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在超越的境界中,獲得深層的生命安慰。
(作者:朱良志,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北京大學美學與美育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