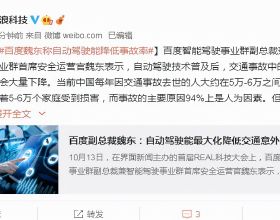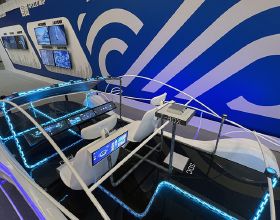1547年1月19日,莊嚴肅穆的克里姆林宮烏斯賓大教堂正在舉行隆重的加冕儀式,當滿頭銀髮的大主教馬卡里把鑲滿珠寶的莫諾馬赫皇冠鄭重地戴在年僅十七歲的大公伊凡四世(又被稱為伊凡雷帝)頭上的時候,俄羅斯歷史上新的一頁開始了。
伊凡四世加冕成為俄國曆史上的第一個沙皇,這決不僅僅意味著“稱號”的改變,而是代表著一個民族帝國意識形態的形成。從這時起,到十九世紀末的僅僅四百年時間,沙皇俄國從一個地處歐亞平原一隅的、面積280萬平方公里的小國,發展成為一個橫跨歐亞大陸、面積達2200萬平方公里的大帝國,這是一種何等驚人的擴張速度!
從伊凡四世起,象徵著沙皇統治的雙鷹旗幟,就開始在北半球的上空獵獵飄揚。
那麼,沙皇俄國為何如此擴張成性呢?它的內在驅動力和外部環境如何?擴張成功的因素是什麼?它本身所具有的東方基因,又是如何形成和助長了它在東方的擴張?另外,沙皇除了他手中高舉的軍刀以外,他還擁有什麼魔力和法寶,驅使那些好戰的哥薩克分子,像決了堤的洪水,向廣闊的歐亞平原沒有遮攔地傾洩而去?這一系列看似簡單實則頗費考究的向題,長期以來,引起了人們無限的興趣。
一架沒有欄杆的嬰兒車
俄羅斯發祥於歐亞大平原。它的四周,都是一望無際的平川大地,既沒有高山大川可憑,也沒有雄關要隘可守。對於一個剛剛誕生的國家來說,歐亞大平原是一架沒有欄杆的嬰兒車,毫無安全可言。因此,它飽受過侵略和奴役之苦,那些神出鬼沒的草原飛騎和金戈鐵馬的韃靼軍隊,就曾是酷愛自由與獨立的俄羅斯的大敵。在經過了長達兩個半世紀之久的血與火的洗禮後,俄羅斯終於掙脫了韃靼人奴役的枷鎖,但是,就像勝利來之不易一樣,要保衛勝利也是極不容易的。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們就不得不經常擴張邊界,以防止他們的敵人接近他們。
這其實只是一種簡單的生存規律,一種本能而已。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教授曾經指出:生存和安全是人的頭等需要。一個民族的心理也是這樣。俄羅斯咄咄逼人的擴張行為,也只是出自一個單純的慾望——繼續生存的本能,這是一種對地形所造成的危險的直接反映。
近代地理大發現認為,有沒有出海口和領海,幾乎成了判斷一個國家是否進入近代社會的重要標誌。在這一方面,俄國也有著先天的缺陷。因為瀕臨俄國北部和東部的海洋,儘管海岸線很長,實際上卻不能用於經濟上的需要。唯一起著海上大門作用的是阿爾漢格爾斯克——白海上的一個港口,但它一年也有9個月的封凍期。
鐵路時代出現前,一個國家沒有出海口,就等於與世隔絕,它的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將停滯不前,對外貿易也將仰人鼻息。因此,尋找出海口的願望,也是助長俄國向外擴張的一個重要因素,到彼得一世時期,向海洋擴張的願望就更為迫切了。馬克思曾經評論說:“‘俄國需要有水域’這句話,成了彼得一生的座右銘。”
此外,人煙稀少的亞歐大平原,還使俄國遠離當時世界上的商業和文化中心,這就導致了俄羅斯文化上的孤立,從而迫使它不斷地尋求與西方的一些中心對話。
俄羅斯的這種地理環境,一方面賦予了它對外擴張的內在要求,另外,也提供了它對外擴張的客觀條件。既然亞歐大平原只是一架沒有欄杆的嬰兒車,它沒有山川河流作為屏障來保護一個弱小的俄國,同樣,它也不會有障礙來阻擋一個野心勃勃而又日漸強大的俄國。遍佈於亞歐平原上的橫交錯的河流網,四通八達的連水陸路,無疑助長了它向南到黑海、向西到波羅的海的大移動。再加上廣闊的東部地區人煙稀少,這就給俄羅斯向東殖民提供了一個廣闊的空間和空前的機會。
有關地理環境引起擴張的觀點,在許多學者們看來也是成立的。尼古拉·伯狄阿耶夫在他的論文《論空間對俄國人精神的抑制》一文中,就清楚地寫道:“我雖然不是從亞歐平原成長起來的俄羅斯國家的同情者,但我也認識到它是為控制廣闊土地而鬥爭的產物。我認為是自衛迫使俄羅斯人趕走侵略者,並在他們居住的地方堅定地保衛自己,但由於居住的地方對他們幾乎沒有什麼自然保護條件,他們就不得不經常擴張他們的邊界·•••••”
從另外一個角度,比如說地緣政治的角度來說,儘管早期的俄羅斯就野心勃勃地極欲擴張它的版圖,但它畢竟還面臨著複雜的周邊環境。
西面,與俄國毗鄰的有立沃尼亞(約相當於今天的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立沃尼亞以南是立陶宛大公國。俄國的西北方則為瑞典(其版圖包括芬蘭)。這些國家是俄國向西方擴張的嚴重障礙。特別是立沃尼亞位於俄國進入波羅的海的咽喉之地。立沃尼亞原為日耳曼騎士團的領地,後來成為獨立國家。十六世紀時,立沃尼亞四分五裂,內戰頻仍,名義上是日耳曼帝國的組成部分,並受羅馬教皇的庇護,實際上成為它的鄰國瑞典、丹麥、波蘭、立陶宛長期爭奪的一塊肥肉,俄國也想染指其間。至於波蘭、立陶宛控制下的白俄羅斯、烏克蘭,早就成了沙皇俄國覬覦的物件了。但是,和當時的東北歐強國瑞典、丹麥、波蘭、立陶宛比起來,俄國還只是一隻初生牛犢,儘管勇氣可嘉,畢竟實力有限。不過,隨著俄國實力的發展,這些國家也都紛紛成了它的俎上肉。
南面,與俄國連界的是從金帳汗國的廢墟上站立起來的克里米亞汗國,再往南是土耳其人。土耳其人的前身為突厥人,它們於1453年征服拜占庭後建立奧斯曼帝國,它以伊斯蘭教為國教,以君士坦丁堡為首都,地跨歐亞非三洲,特別是控制著黑海與地中海相連結的咽喉要道——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達達尼爾海峽,克里米亞本身實力不強,但它得到了強大的土耳其的支援,不僅堵塞了俄國進入黑海的道路,而且還經常襲擾俄國。
東面,與俄國接壤的是位於伏爾加河中下游的喀山汗國和阿斯特拉罕汗國,以東則是諾蓋汗國,再往東就是失必兒汗國了,這些汗國都是從金帳汗國中分離出來的。伏爾加河地區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一向被俄國擴張主義者稱為“天下勝地”。喀山汗國的首都喀山城是通向烏拉爾一帶的必經之地,也是東歐、北歐同高加索、中亞地區貿易往來的衝要之道。如果俄國一旦佔領喀山,即可獲得東進和南下的基地。再加上喀山等諸汗國實力相對弱小,因而就成了俄國擴張主義者的首批祭品。
吉普賽式的斯拉夫人
如果說自然環境造就了俄羅斯的擴張主義的話,那麼,這種擴張主義的早期特徵則是斯拉夫民族對亞歐平原長達數世紀之久的移民過程。從許許多多生動的文學作品中,我們知道了一個喜歡遷徙的民族——吉普賽人。他們攜兒帶女,輕裝簡從,過著漂泊、流浪的生活。而俄羅斯人的祖先——東斯拉夫人,似乎也有著吉普賽人的習性,在廣闊的亞歐平原上漂泊、遊蕩,艱難地繁衍著他們的生機和文化。
據編年史記載,斯拉夫人對亞歐平原自願或非自願的移民,比俄羅斯擴張主義的所有其它表現要早出現幾個世紀。一般說來,斯拉夫農民的漂泊遷移,並不像吉普賽人那樣浪漫,而是因為三個方面的原因被迫不斷深入內地和向北或向東推進的:尋找沒有遊牧部落襲擊危險的土地;獲得自由土地的願望;希望躲避國家那些貪得無厭的稅吏和募兵官。早在六世紀東斯拉夫部落到第聶伯河起,他們就開始利用第聶伯河方便的交通條件來擴大他們的領域。他們順利地向南移動,遠達黑海南岸並且往北到達伏爾加河上游。
從十一世紀開始,斯拉夫人的移民進入第二個階段。波洛伏齊遊牧部落的蜂擁而至,使基輔周圍的南部草原生活變得日益不穩定,於是許多斯拉夫人逐漸向東北方向移去,其中許多人的遷移完全超越了過去斯拉夫人的定居線。這批移民的到來,使附近地區的弗拉基米爾——蘇茲達爾公國日益強大起來。這個公國位於蒙古人控制的羅斯地區的中心地帶,而後來的莫斯科公國,就恰好誕生在這裡。
在蒙古人統治的時代,斯拉夫人的擴張主義和移民傳統雖然被限定往北方發展,但決不能說它們移民的範圍縮小了,恰恰相反,數千逃難的農民逃往卡累利阿以躲避蒙古人的恐怖,因而給諾夫哥羅德共和國提供了一個要求合併該地區的機會。
斯拉夫族遷徙的第四次浪潮是從十六世紀中期開始的,這時俄羅斯國家已經建立,這次遷徙的浪潮成了任何官方的政治合併的先聲,併為俄羅斯後來的邊界擴張奠定了基礎。當時,立沃尼亞戰爭在進行,為了反抗無休止的戰爭加諸農民的橫徵暴斂和拉楓徵兵,也由於響應回到南方肥沃土地去的多年夢想的召喚,數千莫斯科國的農民向南方遷徙,其中大半遷入頓河流域和頓涅茨克河流域渺無人煙的土地。隨著最初的農民進一步向南移動,他們建立起一些新的哥薩克社群,這些社群正好處於莫斯科政府的代理人力所不及的地方。因此,俄羅斯向黑海擴張最早的事實就是半逃亡的農民偶然的推進,如果沒有他們的先期移民,那麼征服和兼併黑海地區的程序就會被大大地推遲了。農民成了俄羅斯擴張的先遣隊。斯拉夫農民最後一次遷徙的浪潮發生在十六世紀後期和十七世紀初,這是對開墾擁有誘人的自由土地的西伯利亞的響應,也是再次為反對壓在莫斯科國全體農民身上越來越重的橫徵暴斂的一次無聲反抗。提起“西伯利亞”,一般人會感到毛骨悚然,在他們的想象中也許會湧現出沼澤密佈、冰雪茫茫的蠻荒景象。人們也許還會認為這裡除了偶爾出現幾個原始的土著外,就是滿山遍野的野狼,間或有幾個手持火槍的哥薩克······當然,這只是一般人的想象而已。其實,在一代又一代的拓荒者看來,這裡是一片絢麗多彩的土地,到處是美麗的自然風光,這裡的生活充滿艱辛也富有自由。無論是寧靜夏日貝加爾湖陽光明媚的景緻,或是西伯利亞土著居民的純樸熱情,都令許許多多的拓荒者們心向神往。
但是,無論怎麼說,這最後一次農民遷徙的浪潮卻大大地促進了政治的統一。這次遷徙嚴格說來是隨著皮貨商人之後的,可是,在政府推行它的殖民政策之前,農民遷徙在數量上遠遠超過了以商人和教士為代表的俄羅斯官方人士,而且總是在數量上大大超過由國家遣往的移民。十七世紀初,羅曼諾夫王朝建立後,由於農奴制度的強化,自發移居的農民的數量大大減少了。以後,沙皇政府又嚴格地規定了農民流入西伯利亞的比例,從此,斯拉夫農民的移民浪潮基本停止。
但是,回顧十七世紀以前的歷史,我們發現,俄羅斯農民幾乎在一切情況下都是走在國家官吏之前的,因此,他們才是亞歐大草原上真正的拓荒者。為了尋求肥沃土地或為了免遭遊牧民的襲擊或為了逃避國家的兵稅,冒險的俄羅斯農民以他們勇敢而不畏艱辛的行動,擴大了俄羅斯人對於自然界的不幸的是,他們勇敢的行動,反倒給他們力求逃避的那國家開闢了擴張的道路。他們越是走在政府的前頭,他們就越是助長了俄羅斯擴張主義加快速度。
金錢的誘惑
在促使向外擴張的諸因素中,貿易是最恆久不變的因素。早在俄羅斯統一國家出現之前,這種商業與擴張互為推動的情況就已經出現了。北歐海盜出身的瓦良格人首先發現了斯拉夫人地區巨大的商業意義:他們的領土能夠用來連線巴格達和君士坦丁堡的市場與加羅林帝國的市場之間的貿易路線。於是,瓦良格人南下征服斯拉夫人,建立起基輔羅斯,為了實現他們建立商業大帝國的夢想,最初的幾個基輔大公執行著擴張主義的對外政策。尤其是在處理同拜占庭帝國的關係方面,基輔把對外擴張作為對外貿易的補充,幾次發動了對拜占庭帝國的戰爭。最終迫使後者接受屈辱的條約,為基輔羅斯的商品和奴隸貿易進入拜占庭市場打開了方便之門。
俄羅斯國家統一以後,莫斯科商人控制並且主持著羅斯地區的貿易事業,伊凡四世時,因為貿易衝突而引發的國際爭端達到了嚴重的關頭。1552年對“天下勝地”喀山的迅速征服被偽裝成為一次反對伊斯蘭教徒的基督教十字軍,而1554年和1556年征服阿斯特拉罕時就公然以給莫斯科的貿易開啟整個伏爾加河流域為目標。1558年,為了不使俄羅斯被排擠到歐洲貿易活動的外圍,伊凡四世冒著極大的危險,發動了耗費巨大的立沃尼亞戰爭,以求在波羅的海海岸為莫斯科獲得一個港口。因為在伊凡四世看來,只要他保有哪怕是最小的一個港口,這個戰爭就證明是一項有利可圖的事業,但由於波蘭、立陶宛和瑞典三方都反對伊凡插足波羅的海,因而伊凡四世最終一無所得。
在彼得以前莫斯科國領土擴張的最後階段多半是為貿易事業推動。這種由於經濟上的貪婪而引發的對外擴張在俄國征服西伯利亞的過程中達到了高峰。前面說過,西伯利亞的自然條件是艱辛的,但是那裡也埋藏著淘金者的夢想。許許多多希望發財致富的商人和哥薩克分子,冒著生命危險,在西伯利亞尋找著發財的機會,他們中間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則長眠於此。
對於商人們的冒險和擴張,沙皇政府是完全同意的。它先是授予大商人斯特羅幹諾夫家族一項政府專利權,允許他們在西伯利亞進行殖民掠奪。對於那些自發前往東方的人們,沙皇政府則透過一種納貢效忠(以毛皮、牲畜等納貢)的制度把他們管理起來。到1590年,沙皇政府又派出軍隊永久駐紮西伯利亞,用來鎮壓地方的起義。
沙皇政府與商人的緊密合作,不僅鞏固了它在西伯利亞的勢力,而且主持了不斷向東尋求皮貨的探險。這個殖民擴張程序於1648年達到了頂點,在這一年裡,謝苗·迭日涅夫透過白令海峽自歐亞大陸的東北角到達了美洲大陸。
因為貿易的關係,沙皇政府除了在東方冒險外,還在西方與南方進行了長期的戰爭,在西方主要是爭奪通往波羅的海的出海口,在南方則是為了打通由黑海到地中海的商路,這一切都在證明,是金錢和貿易的巨大誘惑,促使沙皇政府進行著全方位的擴張戰爭。貿易與擴張,有一種極為密切的關係,用馬克思的話說:“佔主要統治地位的商業資本,到處都代表著一種掠奪制度,它在古代和新時代的商業民族中的發展,是和暴力掠奪、海盜行徑、綁架奴隸、征服殖民地直接結合在一起的。”俄國的商人階級也是這樣,為了保證貿易道路、商業利潤以及殖民掠奪,不斷地支援和推動沙皇政府向外擴張。
正教的光輝
宗教原則雖然從來沒有靠犧牲政治的利益而收到預期的效果,但它卻常常成為一個有用的理論,因為它能掩蓋擴張者為掠奪金銀財富而發動戰爭的凡俗動機。從988年羅斯軍隊皈依羅斯人的生活方式,鼓舞和發展了他們個人的和公眾的活動,更重要的是東正教賦予俄羅斯人一種世界觀,使他們可以向其周圍的人們-東面的伊斯蘭教徒和西面的羅馬天主教徒-定出自己的方針。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伊斯蘭教徒和羅馬天主教徒都對他們的政治生存因而也對他們的宗教生存擺出了一種威脅姿態。
基輔和莫斯科公國反對信仰其他宗教的國家的大多數軍事行動,都是在宗教的外衣下進行的,並且以十字軍的形式出現:奪取新的領土以擴充東正教的邊界。因此,我們除了看到由地理限制引起的咄咄逼人的擴張主義和經濟慾望引起的貪婪外,我們還能看到俄羅斯擴張主義的另一方面,即由宗教的救世主義產生的熱誠。既然俄羅斯被信仰其他宗教的列強長期包圍,那麼東正教在彼得以前俄羅斯的征服理論中就成了堅定不移的信仰。
伊凡四世征服喀山和阿斯特拉罕就是以宗教的名義完成的,有些為了追求商業利益的征服和擴張有時也假借宗教的名義。莫斯科特列基雅科夫畫廊展出的著名聖像《教會的得勝》,就充分說明了伊凡四世是如何假借宗教的名義進行他的擴張事業的。這幅聖像表示沙皇伊凡與大天使米哈伊爾和德米特里·頓斯科伊並列,表示在崇高的東正教征服者的神聖傳統中,伊凡乃是神聖的後裔。當伊凡在勁頭十足地與立沃尼亞人進行戰爭時,就把他們都當做是不信上帝的人。他還三番五次地把自己描繪成基督教的監護人,因而被賦予了統一基督教世界的任務,以便與他的偉大前輩康斯坦丁皇帝媲美。
就俄羅斯教會來說,它在配合莫斯科當局擴大邊界方面也是毫不示弱的。從1328年俄羅斯的總主教移居莫斯科起,他們對莫斯科大公們日益增強的野心就更加給予道義上的支援。1453年,當東正教的中心君士坦丁堡陷落使莫斯科國成為唯一自治的東正教的政治體系時,教會在努力發展莫斯科國的帝國意識形態方面的呼聲變得更響亮了。瓦西里三世時期,僧侶弗洛菲正式提出了“第三羅馬”的理論。他在給瓦西里三世的檔案中闡述了這一理論,他寫道:
“至高至貴的君主,基督教正教的沙皇,大公陛下······您將取代羅馬和君士坦丁堡的地位。
“第一個羅馬因信奉異端而垮臺,第二個羅馬一君士坦丁堡的教堂之門也被伊斯蘭教徒的戰斧所劈開。現在這裡是新的第三羅馬,保持您的皇位以及神聖使徒的教會,使宇宙之內、普天之下,永遠照耀著正教信仰的陽光。
“尊敬的沙皇啊!因為一切信仰基督教的王國將統一於您的王國,您也將成為普天之下基督教的沙皇。
“尊敬的沙皇,請自尊自愛吧!全部基督教王國將統一於您。兩個羅馬已經垮掉了。第三個羅馬屹立著,而第四個羅馬永不會有。”
這種呼聲就是要莫斯科取代君士坦丁堡的地位,全世界的基督教王國要統一於沙皇俄國,而沙皇將成為全部東正教徒的沙皇。
雖然都主教和教士們在直接影響莫斯科國的領土野心方面並不成功,但他們能夠把救世主和宗教使命的生氣勃勃的情感灌輸進莫斯科國的外交政策。到伊凡四世統治時,整個朝廷受到一種基督教優越感和自以為是的氣氛的影響,這種氣氛一方面增強了把新教徒趕出波羅的海的慾望,另一方面在東方穆斯林地區加強了基督教廣泛殖民的政策。
在十七世紀初,當弗拉萊特總主教與他的兒子米哈伊爾·羅曼諾夫沙皇共同統治時,教會有更多的機會指導莫斯科的外交政策。到1633年弗拉萊特死之前,他擬訂了計劃,以便有朝一日羅曼諾夫王朝的俄國能夠進行反對波蘭的戰爭,不僅要報復在混亂時期波蘭的干涉,而且要使好戰的東正教與好戰的波蘭天主教打仗。他這樣做的時候得到了老百姓的有力支援,因為他們把波蘭看成是反對基督的化身。隨著1652年尼康總主教的就職,俄國更加轉向信奉東正教的東方,並且擬就瞭解放那個地區信奉同一宗教的人們的計劃。一旦波蘭被迫宣佈中立和東烏克蘭被兼併,這種野心就與莫斯科現實主義的計劃相吻合,即與土耳其打仗。從十四世紀以來,侵略成性的基督教君主的原則與俄羅斯東正教會的世界野心已經結合起來,到1700年他們終於完全合拍了。這時,沙皇認為,俄羅斯強大到足以向土耳其人挑戰了。巴爾幹半島的關鍵是信奉東正教的各族人民,這給俄羅斯提供了一個進入巴爾幹地區的絕好口實-解放巴爾幹。這最終使俄羅斯人的貿易有一個透過戰略要津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出口。
沙皇-帝國意識的象徵
在對外擴張的過程中,俄羅斯的統治者開始把自己說成是羅馬皇帝的後裔和拜占庭帝國的繼承人,甚至把自己描繪成金帳汗國的大汗繼承人。這種努力把自己裝扮成正統繼承人的做法,在中國歷史上也曾出現過,但這種情況在西方似乎更多。
就俄國曆史來說,早在伊凡·卡利達時期,這位號稱“錢袋”的大公在取得“弗拉基米爾大公”的稱號後,就把它(指稱號)擴大為“全俄羅斯之王”。伊凡在這樣做的時候宣告說:我們是偉大的留裡克家族的後裔,留裡克王朝的世襲權起先確定在基輔,後來移往弗拉基米爾和蘇茲達爾,現在已經在莫斯科確立起來了。這種宣稱自己為某一個偉大家族後裔的做法並不僅僅是為了一種表面上的虛榮,而是反映出莫斯科公國所逐漸形成起來的帝國意識形態。因為他們的所追求的目標是收回他們的“世襲領地”(遺產),也就是世世代代擴大領土的幻想。
1473年以後,伊凡大帝在許多場合都用“沙皇”這一稱呼號,這是莫斯科公國在帝國意識形態方面採取的一個象徵性步驟。“沙皇”一詞來源於古羅馬皇帝的稱號“愷撒”,意思是“皇帝”。這個至高無上的稱號原來是俄國人用來稱呼拜占庭皇帝的,後來,俄國人也以此來稱呼蒙古可汗。
伊凡大帝的這一舉動,關係到下列的事實,即留裡克家譜把莫斯科公國的家族上溯到古代羅馬皇帝。為了給日耳曼皇帝(他也把自己當作羅馬統治權的繼承人)以深刻的印象,伊凡還使用了雙頭鷹的國徽(這原來是拜占庭帝國的國徽),對此,恩格斯曾經形象地指出:“當君士坦丁堡剛落入土耳其人之手,莫斯科大公就把拜占庭皇帝的雙頭鷹加入了自己的國徽,從而宣稱自己是羅馬皇帝的繼承人和復仇者;大家都知道,從那時起俄國人就力求佔領沙皇格勒即沙皇城(他們在自己的語言中是這樣稱呼君士坦丁堡的)。後來小俄羅斯的富饒平原又引起了他們吞併的慾望。”
1547年,伊凡四世正式加冕成為“沙皇”,這表明,他也成了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皇帝。總之,莫斯科的統治者們採用和從戰略意義上運用種種稱號以及為這些稱號附加上意識形態,這不僅想要表示與其他統治者平等,而且等於公開宣佈了擴張主義計劃,這對於莫斯科的一些敵對國家來說,還是起了一些作用的。
莫斯科在向東擴張的過程中,還日益覺得他們是金帳汗國的遺產繼承者,並把金賬汗國曾經擁有的全部領域作為俄羅斯帝國政策的一種最終目標。在俄羅斯統治者看來,只有它才最有資格提出在前宗主的區域內充當領導者的要求。在對伏爾加河中、下游的兩汗國進行征服的過程中,儘管莫斯科曾策動信東正教的俄羅斯人作為一支基督教十字軍而進行戰鬥,可是,莫斯科國的統治者卻是以充當早先金帳汗國舊址的當然繼承人來進行這次東方戰役的。在俄羅斯的思想裡,把沙皇的稱號與羅馬愷撒的概念聯想起來以前,沙皇這個稱號同“汗”這個稱號早就是同義語了。在伊凡三世取得喀山戰役勝利之後,他才第一次採用了“沙皇”的稱號。當伊凡四世以“沙皇”之尊征服喀山和阿斯特拉罕時,他乃是作為金帳汗國的汗的真正繼承人而這樣做的。在向東征服的過程中,沙皇政府利用許多土耳其部落和蒙古部落把它當做可汗繼承人的這種感覺,為它的征服活動創造了心理上的有利局面。直到十八和十九世紀,對於加爾梅克和布里亞特人來說,沙皇還是他們心目中的“白汗”。
這樣,“沙皇”這一明顯表露俄羅斯帝國心跡的稱號,就成了一個萬能的法寶。在向西方推進的時候,俄羅斯的統治者就把自己看作是羅馬皇帝的後裔和拜占庭皇帝的神聖繼承人;在向東方推進的時候,他又是金帳汗國的繼承人了。東正教的俄羅斯儘管曾打著“維護正教信仰”的旗幟對外用兵,但它卻是心甘情願地承認偉大的穆斯林統治者的威望的。實際上,它只不過是利用了自己輝煌的過去——由基輔羅斯以及羅馬帝國和蒙古帝國——所提供的一切可能的條件,為它的勃勃野心添上一層美麗的謊言罷了。但是,從俄羅斯發動的歷次戰爭的動機來看,我們又幾乎可以說,正是這種妄想至高無上的勃勃野心,構成了俄羅斯擴張主義的最大動力。
參考資料:《俄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