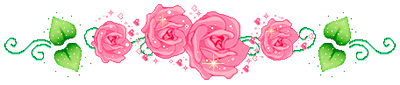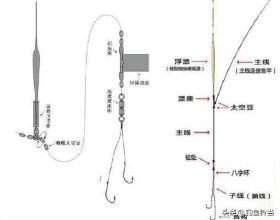蘇聯紅軍進駐小平島見聞
喬世楨 旅順口大型畫傳 今天
紀實文學
上)
喬世楨
1945年8月22日,蘇聯紅軍西伯利亞方面軍第三摩托化集團軍,在東北完成對日軍最後一戰,殲滅關東軍戰役結束後,奉命揮師南下。他們日夜兼程,長驅直入開赴大連和旅順。由該軍一個炮兵團則直接開拔到小平島,駐紮在一個當地人稱為“小山”的地方。該團下屬的一個炮兵連在上尉連長的帶領下,來到島南頭一個當地資本家逃走時丟棄的一棟二層粉色樓安營紮寨,從此開始了十年駐軍。於1955年11月撤軍。
那年我10歲。親眼目睹了那些大鼻子藍眼睛的蘇聯紅軍與當地居民頻繁來往的一件件動人的往事。儘管60多年過去了,那些情景依然像黑白老電影一樣,在我的腦海一幕幕浮現……
炮連營房放電影
當年蘇軍經常在部隊營區裡放映電影,每當這個時候,連隊領導都會安排士兵到駐地附近的老百姓家裡通知看電影。那時候的島上人,都沒見過電影,第一次看到掛在牆上的大白布裡出現聲音和活動的人及景物時,都不知所措地發出陣陣驚呼聲。幾個老漁民甚至踱步到銀幕前,試圖用手抓住裡面人。引得正在觀看電影的蘇軍士兵不時發出善意的笑聲。
炮連放電影的日子,就是我們這幫小孩子最快樂日子,甚比過年。放電影這天,我們小孩子都早早吃完晚飯,每人提溜著個小板凳,結伴來到蘇軍營房,占上個看電影最佳座位,(當然不能佔據炮連士兵畫好的位置),然後翹首以盼等著開演。那個時期我們看了無數部電影。小孩子最愛看的是反特片和打仗片。有幾部電影我至今記憶猶新。如《勇敢的人》、《堅守要塞》、《斯大林格勒保衛戰》、《深山虎影》、《夏伯陽》等。尢其影片裡那個夏伯陽,戴個哥薩克式的高筒皮帽,揮舞著亮光閃閃的戰刀,騎著駿馬在草原上馳騁的英姿至今難忘。
雖然我們看了不少電影,但一句話也聽不懂,因為裡面的對白全是俄語。儘管如此,透過觀看電影,使我們這些生在海邊,長在海邊的島里人看到了外面世界的浩瀚和多彩。
士兵與少年
在我九歲那年的一個秋日上午,那是個星期天。閒著無事,我領著7歲的弟弟來到炮連訓練場看蘇軍士兵踢足球比賽,正當我倆站在場邊看得興高采烈的時候,突然飛出一隻足球結結實實砸在我弟弟臉上,頓時鮮血湧出,蓋住了眼睛。蘇聯人用的足球和我們的不太一樣,是黑色膠皮球,皮厚,硬梆梆的,痛得我弟弟嗷嗷大哭。幾個踢足球計程車兵趕忙跑了過來,檢視傷勢,用毛巾擦拭弟弟臉上的血。一名士兵飛一般朝連隊營房奔去,回來手裡捧著藥棉花,碘酒,為我弟弟臉上消毒,上藥,止血。連比劃帶說“對不起。”
這時,一個蘇軍軍官走了過來,看到這個情景後,頓時大發雷霆,訓斥那幾個惹禍計程車兵:“吆比多一麻,比溜溜達外”。這是一句罵人話,按中國話的意思,就是媽拉個巴子,你們想找揍啊。當年我們和蘇軍接觸較多,知道軍隊等級森嚴,官大一級壓死人,從不慣毛病。一次炮連兩個士兵去營房附近的小食雜店以買毛殼(瓜子)為名,把小店糖罐裡的糖豆偷個精光,店主發現後,跑到炮連報案。連隊領導很重視,立刻集合全連,把那兩個還沒來得及分贓計程車兵揪了出來,只見一個軍官抽出腰間的皮帶,不由分說朝這兩個士兵身上抽去,打得這兩個兵嗷嗷叫喚,最後押進馬廄裡關了三天禁閉。
這時,只見軍官一邊吼著,一邊叫士兵把我弟弟領進連隊醫務室又認真處置一番。看看無大礙,這名中尉軍官安排士兵到飯堂拿一個黑列巴,兩瓶牛肉罐頭,和幾根香腸送給我們,算是補償。把我們小哥倆打發得高高興興走出營房。弟弟破涕為笑,傷口也不那麼疼了。
美麗的女軍醫
那時島里人的生活還是很窘迫的,離市區較遠,看不起病。家中有小孩子患病的話,無錢醫治,只能眼睜睜看著死去,然後湊幾塊板,釘個小木匣子,把死去的孩子裝進去,扛到南山或者北山,挖個坑穴埋掉,有的連墳頭都不留。
當年,我有個姐姐才四歲,得了天花,因無錢治療眼看著死在媽媽懷裡。我五歲那年,因感冒發燒,、渾身出疹子,高燒一直不退,而家裡又一時拿不出錢送我到市裡醫治,只能用土方,眼著病情越來越重,到了死亡邊緣。父親朿手無策,母親和奶奶只能以淚洗面。就在走投無路的時候,蘇軍炮兵團知道了這個情況,炮團首長立刻派一名女軍醫帶一名衛生兵,一路打聽著找到我家,進家後,立即為我做病情檢查,為我打針吃藥,經過兩天細心治療,把我從死亡線拉了回來。把我們全家人感動得一個勁的鞠躬致謝。
等我上學後,我的父母告訴我,是一個女軍醫救了我的命。還說為我治病的女軍醫,穿著合體的軍裝,套著白大衣,長得端莊文靜、漂亮得就和蘇聯電影裡的明星一樣,肩上是一槓三花(上尉)。我萌發了要見這個女軍醫的念頭。一天放學後,我沒回家,揹著書包徑直來到炮兵團駐地,去找那位女軍醫,想當面表達謝意。團部門崗哨兵不讓小孩進,我只得比比劃劃說要找那位女軍醫,哨兵聽明白後,也比劃著告訴我,那位女軍已在一年前就調回國內了。聽到這個訊息,我當即哭了,心裡很是遺憾。後來聽島裡的大人們說,這位女軍醫當年才三十歲左右,在小平島治好了無數個大人小孩病,挽回了很多人的生命。可大家一直不知道她叫什麼名字。
愛和孩子玩耍的蘇聯兵
當年,我們幾個小孩子,經常在蘇軍炮兵連旁邊的火神廟大殿門外的空場地上玩耍,那時玩的遊戲主要是彈玻璃球,打小紙牌。這時候就有炮連計程車兵,三三兩兩圍攏過來看熱鬧,看著看著,乾脆蹲下身來和我們打玻璃蛋比賽,結果往往一個也打不著,氣的直跺腳,嘴裡嘰哩哇啦聽不懂說什麼,可能是說,我的炮打得那麼準,為什麼一個小小玻璃蛋就打不著呢。
到了冬天季節,我們這幫孩子就常常聚集在炮連跟前一個叫南泡子的結了冰的冰面上打呲溜滑,溜冰板,打陀螺,玩的不亦樂乎。這時只見炮連計程車兵溜溜達達過來十多個,開始圍在旁邊看熱鬧。後來又憋不住,先和我們打呲溜滑比賽,因為他們穿著長筒皮靴,底厚皮硬,防滑差,一摔一個跟頭,敗下陣來;又比打陀螺,雖然他們都是十八、九歲的小夥子,比我們有勁,但不會用巧勁,結果一鞭子下去,能把小小陀螺抽上天;不服氣,又要滑冰板,他們穿著棉軍服,顯得很笨拙地坐在冰板上,滑了不到二步遠由於平衡沒掌握好,冰板往後一撅,把他們摔個仰巴叉,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蘇聯士兵好摔跤,但在小平島遇到了硬茬子,就是我的本家四叔。當年四叔十五歲,小夥子血氣方剛,是一個摔跤高手,在我們全島無敵手。這個訊息炮連不知怎麼知道的,就派人來約我四叔比試比試。一天,他們一個排長帶來幾個連隊裡的摔跤高手,同我四叔一起來到小平島西海邊沙灘上比武。開始一對一,不到兩個回合,我四叔就把那個對手放躺。他們又上來兩個和我四叔對陣,四叔一個掃蹚腿把前面那個整趴下,接連一個躬背摔,把身後那個抱腰的扔出丈八遠,圍觀的人直拍巴掌叫好吆喝。那個排長一看,這個小孩子了不得呀。就叫上四個士兵一齊上,兩個抱腿的,一個抱後腰,一個在正面。我四叔面不改色,沉著應戰。幾個回合下來,把這四個兵全撩倒。在場的人看得目瞪口呆。那個排長拍著我四叔肩膀,伸出大拇指,嘴裡直喊:“哈拉少,哈拉少。”幾年後,我四叔參軍,成了一名空軍戰士。
那時候,炮連士兵都非常喜歡我們這群住在他們營附近的孩子們,經常從連隊飯堂拿黑列巴,奶油和其它食品給我們“狗食,狗食的。”
軍艦上的“半日遊”
一年夏天,十幾艘蘇軍各種艦艇,在小平島外海訓練完後,有幾艘駛回旅順基地,其餘幾艘依次駛進了小平島西口海域臨時錨泊。島上的人都跑到西海邊沙灘上,駐足觀看這些從未見過的龐然大物。我們這些個小孩更是好奇,在我的鼓動下,我們七八個剛中午放學的同學,連家也不回,飯也顧不上吃,把書包堆在沙灘上,只穿一個褲頭,下到水裡向軍艦方向游去,想看個究竟。有兩個同學水性不太好,就從停在沙灘上的舢板上,一人抽出一塊黃板(墊板),跟在我們後頭一起游去,岸邊上的大人們大聲喊著,要我們注意安全。有個同學家長不知什麼時候過來的,直喊著我那同學的名字,叫他回來,但他沒有理會,和我們一起前行。其實我心中有數,從岸邊到最近錨泊的軍艦距離不到1000米。這都是我們在海里經常遊的距離。將近40分鐘的時間,我們游到了離岸最近的一艘軍艦大約20米的距離停下來,往艦上觀望著。這艘軍艦甲板上已站滿了好多水兵,他們一邊喊著,一邊揮手,意思叫我們靠近些,我們毫不猶豫的遊了過去。他們把一根軟梯從甲板艦舷上放了下來,叫我們上去,這時我們有些猶豫了,心想,不能上去把我們拉走吧。我們在水裡這麼長時間也累了,大家商量一下,都說怕個球,上就上,看能把我們咋的。我是第一個抓著軟梯爬了上去,其它人依次上來,艦上有人順根繩子下去,叫那兩個趴在板子上的同學把板子綁好,拴在軟梯上,然後他倆也爬了上來,
這時甲板上的水兵把我們幾個團團圍住,有的拍著我們溼漉漉的腦袋,伸出大拇指,不斷比劃誇我們勇敢,這麼小的小孩能遊這麼遠到這裡來。這時有兩個老兵,領我們到軍艦各個部位參觀。這下子我們可開了眼,這裡瞅,那裡摸,看什麼都好奇。經過這兩個老水兵比比劃劃地介紹,我們才曉得這是一艘獵潛艦,60多米長,屬於小型艦,別看艦小,可威力大,在二戰中,曾在波羅的海的一次海戰中,擊沉過德軍一艘大型驅逐艦。真了不起啊,我們對這艘戰功卓著的戰艦肅然起敬。
兩位老兵又帶我們觀看艦尾的魚雷發射裝置,把我們領到艦首主炮位置,這是一門雙管機關炮,按照他們教的操作要領,我們每人上去擺弄一番,只見我們手握操縱炳,使炮管上下左右飛速旋轉,樂得我們嗄嗄大笑。這時一個水兵拿來一架望遠鏡,讓我們觀景,我第一個端起來往遠處望去,只見遠處山巒一下子跳到我的眼前,清清楚楚,我驚住了,險些失手把望遠鏡掉到甲板上,逗得水兵們哈哈直笑。
時間過的真快,幾個鐘頭過去了,由於中午沒吃飯,我們一個個飢腸轆轆。得知我們沒吃飯,兩個老兵領我們進艦上的飯廳,這個廳不算大,一次估摸能裝40幾個人就餐,但佈置得溫馨別緻,牆壁上貼著幾張俄羅斯風情的風景畫,還有幾盆安放在固定架上開著不知名的鮮花。這樣的佈置,也許是這些長年在大海里馳騁,遠離大陸,而尋找一種鄉土氣息的吧。
正在我們東張西望時,兩名水兵端著個托盤,上面放著白列巴,奶油,香腸,水果等食物,放在餐桌上,又提溜幾瓶飲料(按現在看,就是嗄瓦斯一類)過來。兩位老兵示意我們用餐,我們這幾個八、九歲的孩子,從出生以來,成年都是和苞米麵餅子,苞米麵稀飯打交道,何時看到這樣的精美食品,這時也顧不上那麼多了,風捲殘雲的大嚼起來。正低頭吃著,只見進來兩個衣帽整齊的軍人,三十多歲模樣,抬頭望去,肩章都是二槓一花,是少校,估計是艦上的艦長和政委。我們幾個挺懂事的,齊刷刷光著膀子給兩人敬了一個標準的少先隊員禮,他兩人也嚴肅地為我們回了個軍禮。然後用俄語向我們說了幾句熱情的話,意思是歡迎你們到艦上游玩之類,然後對士兵們交待幾句就出了艙門。我們又接著繼續大嚼,一個個連吃帶喝撐得直打嗝。
這時太陽偏西,時候不早了,怕家裡人不放心,我們要回去了。這時艦上的水兵也催我們回去。來到甲板上,我們和他們一一告別,他們逐一擁抱我們,戀戀不捨的惜別。之後,我們從甲板上一個個撲咚撲咚跳入水中,鑽出水面後,又和艦上水兵們揮手,他們也向我們揮手,嘴裡還直喊著,大概是叫我們注意安全吧,等著那兩個同學板子解下後,我們一起往回遊。這時正好有幾隻從海外釣魚歸來的舢板路過、一看都是鄰居,便把我們捎上。上船後,望著漸漸遠去的軍艦,我的兩眼模糊起來。親愛的蘇軍水兵們,以後可能再也見不到你們了,但你們的友情將永遠牢記心中。
熱情善良的蘇聯人
那個時候,每到夏天,成群結隊的遊客彙集到小平島西海潔白的沙灘上旅遊避暑,這些遊客以蘇聯人居多。他們當中除了駐紮小平島炮兵團的軍官們外,大部分來自市內的蘇軍駐地軍官和蘇聯專家及家眷們。他們進島乘坐的大客車,黑蓋子小驕車,軍用吉普車,塞滿了西海邊各個道口、道邊。連當地居民大門外也被大小車輛堵滿。
小平島西海口海岸線地貌有個奇特現象,2公里多的海岸線不長,令人費解的是,海岸沙灘最南面的沙子只有小米粒大小,而到沙灘最北面的沙石競是鵝蛋大小。而我們家住的海岸正好在中間地帶,沙石不大不小,有拇指蓋大小。這種沙石大小適中,人走在上面不硌腳,躺在上面不硌腰。所以,遊客都喜歡到這個沙灘安營紮寨。他們有的在沙灘上支上帳篷,躺在裡面乘涼,有的在潔白的沙灘鋪上涼蓆,躺在上面愜意的來個日光浴。更多的則是扎進清澈的海水裡游泳戲水。
每到這個時候,我們這些家住附近的小孩子就會跑到沙灘湊熱鬧,在人群堆裡鑽來跑去,互相追逐戲耍著。說來也怪,這些蘇聯遊客對我們這些中國小孩,不但不厭惡,反而很喜歡,常常喊我們過去,叫我們和他們的孩子一起玩。並拿出很多食品與他們一起進食。別看我們小,也懂得禮數。這時,我們就趕緊跑回家裡,把我們平時積攢比較珍貴好看的貝殼,螺殼拿出贈送給這些蘇聯遊客,樂得那些胖胖的“瑪達姆”伸出大拇指直誇我們“哈拉少,哈拉少。”一天,我鄰家個七歲的小姑娘一人在海邊玩水,不慎被一個破碎的酒瓶子把手指割破,傷口深見骨頭,血流不止,染紅了眼前水面。附近游泳的一對四十多歲夫妻發現後,立即遊了過來,女的把碎瓶撈出來送到不易傷到人的地方,而男子立刻把小姑娘抱到岸上停車的地方,從車裡拿條潔白的手巾,把小姑娘手包住,兩人衣服也沒換,就開著吉普車把孩子送到島北面一個蘇軍醫務所。由於治療及時,小姑娘手指保住了。幾天後,小姑娘的父母來到醫務所送上一份千恩萬謝的感謝信。因為那對夫妻是從市裡來的蘇聯遊客,以後再也沒找著這兩個恩人。
如今,當年被救治的小姑娘已年愈七十。她經常唸叨著,唉,要不是當年那兩個蘇聯人,我右手這根手指頭可就保不住了,咱一輩子也忘不了好心的蘇聯人啊!
蘇聯紅軍進駐小平島見聞(下)
喬世楨
山崖遇險
那年一個秋日的星期天上午,從蘇軍炮兵連營區裡走出兩個士兵,兩人手裡提著個草綠色帆布水桶(專門給馬飲水用的水桶),徑直來到一戶平時交往不錯的當地老鄉家裡,去借了兩掛釣魚線,然後順著門前小路,向南山方向走去。爬到半山坡時,每人折了根棉槐枝子,擼去樹葉,折斷梢子當釣魚竿用。他們登上南山一個叫小樓的地方停下(此小樓是蘇軍之前廢棄的觀通站),這裡的山頂離底部有50多米高,山崖陡峭,十分險峻。這兩個士兵站在山頂四處觀望察看下崖底的線路,開始順著這個崖面一步步小心翼翼攀巖下去,由於手裡提著帆布水桶,又拿著釣魚竿,再加上腳上穿著長筒軍靴,很是不方便。他們一點一點往下挪步,當他們下到離崖底還有七、八米高的地方,一個士兵一腳踩空摔了下去,另一個沒拽住他,也跟著掉了下來,兩人重重摔在崖底礁石上,身下流出的鮮血染紅了眼前的礁石。這時正好有幾隻在附近的海面上釣魚的漁船,當船上的人發現這裡出事後,立即拔上漁線,飛快地搖著小船靠近礁石,幾個人把兩個兵抬到船上,立刻飛快地向小平島西口搖去,靠岸後,大家七手八腳地把兩個因失血過多,已奄奄一息計程車兵抬到200多米遠的炮連。衛生兵經過一番處置後,又用汽車將這兩個兵送到四五里地遠的蘇軍療養院進行進一步治療。兩個土兵因救治及時,傷情轉危為安。
一天,連隊領導帶著這兩個士兵,拿著禮品到幾個參與搶救他們的漁民家中答謝。而我們的漁民卻說:“我們更應感謝你們,你們給我們當地人看病療傷,救了那麼多人的命!”
寒海冬遊
寒冬臘月的一個上午,烏雲蔽日,北風呼嘯。我在家閒著無聊,透著玻璃窗,往外探望觀景。只見天空中飛揚的小青雪,還未落到地面,就被風吹得七零八散。往不遠處的西口海上望去,只見被西北風撩起的浪花湧向南山崖底的礁石上摔得粉碎,濤聲轟鳴。正在我看得入神時,耳邊傳來陣陣蘇聯歌聲,不一會兒,從炮兵連方向走來一隊排著整齊隊伍計程車兵,大約一個排規模,徑直來到沙灘上,然後排成三列橫隊。只見一個戈比蛋(蘇軍軍官別名)來到隊前喊口令,無非是稍息,立正,向右看齊,報數之類,然後訓話,最後一個口令,只見士兵們摘帽脫靴,脫下大衣,令人目瞪口呆的是,他們脫到身體一絲不掛,白晃晃的耀眼。只聽他們一齊吶喊著,一窩蜂似地向海邊衝去,跳入水中。看到這裡,我不由地打了個寒戰。這時只見水性好的以優美的自由泳泳姿游出近百米距離。水性差計程車兵就順著水邊用小狗扒姿勢撲通著。大約二十多分鐘時間,那個站在岸上的軍官一聲令下,士兵們聚集在海邊齊腰深水裡開始騎馬打仗遊戲。就是一個人騎在另一個人脖子上,分兩幫交戰,一幫把另一幫打倒在水中,就算獲勝。我在窗裡看得仔細,這不是我們小孩經常在海里玩的遊戲嗎,怎麼他們也會,嘿,不會是偷學我們的吧。
過了段時間,軍官又喊了一嗓子,只見水中正打的不可開交計程車兵們,立馬跑上岸邊放衣服的地方,拿出毛巾渾身上下擦拭己凍的彤紅的身體,然後迅速穿上衣帽,站好隊形,隨著軍官口令,向右轉,齊步走,這會兒沒唱歌,可能凍得唱不出調了。而是喊著整齊的佇列口令:“得爪是利”。大概是一、二、三、四的意思。聽著漸漸消失的口令聲。我還在玩味著蘇軍士兵在冰冷海水裡冬遊戲耍的情景。心想,這是鍛鍊意志啊,這些北方來的兵可真抗凍啊。
士兵與年夜飯
我家前街有個劉姓大叔,年方40多歲,以倒賣魚貨為生,因為經常到炮兵連營房賣魚,一來二去,和這裡一些當兵的混的較熟,尤其有幾個老兵關係處的有如鐵哥們。這年大年三十,他決定請這幾個兵到家中吃頓年夜飯,讓他們體驗一下中國年的味道。為了備好這頓飯,他在年前乘著去市內販魚的機會,購置了雞,鴨(魚家裡有)和豬肉,特別多買些牛肉,因為蘇聯人對牛肉情有獨鍾。還買了幾瓶二鍋頭,啤酒等,做好了一切準備。我們島上有個風俗,每到大年三十晚上,大人小孩提著個小燈籠來北山一帶自家墓地請神。(就是把先人請回家過年)因為要請客,大叔年三十下午,太陽還掛在半空,他就一人拿著燒紙和幾柱香匆匆來到北山自家墳地,把香點上插好,又燒了幾刀燒紙,叩幾個頭,嘴裡嘟嘟囔囔幾句,把老祖宗請回家,然後急三火四往家趕。到家後,把外屋供桌把祭品擺上,香點著。便和家人一起忙活晚上請客這頓大餐。劉大叔廚藝不錯,他常年到市內賣魚,經常下館子,品嚐了不少名家大菜,也能整出幾個象樣的佳餚來。一會兒工夫,各種菜餚的香氣已瀰漫整個小院落。
晚上六點整,炮連五個老兵按時赴約,個個穿戴整齊。還別說,他們挺懂中國人的習俗,入鄉隨俗每人都帶來禮品,有的拿著黑列巴,有的拿著奶油,香腸,有的拿著雪魚罐頭,還有個兵拿著一件新發的內上衣。把劉叔一家樂得合不攏嘴,一邊接過東西,一邊往屋裡讓。幾個兵進屋後,發現供桌上供著老祖宗的宗譜,趕忙立正站好,給老祖宗們敬個軍禮,還不忘上柱香。這時裡屋飯桌上已擺滿了豐盛的酒菜。幾個兵進裡屋後,劉大叔叫他們脫衣摘帽褪下皮靴上炕,由於他們不會盤腿就座,就一人給個小板凳坐著。這時劉大叔把每個人的酒杯斟滿,然後自己先端起酒杯說起了開場白,用半生不熟的俄語說到,感謝你們來家中做客,中蘇兩國人民都是好朋友等,完後自己先乾為敬,一口把一杯白酒啁進肚裡。又倒一杯酒和大家一起喝下去。他又叫大家吃菜,蘇聯人哪見過這麼豐盛的佳餚,便開始吃喝起來。他們不會用中國筷子,笨笨磕磕的把菜弄的到處都是,引得家裡人笑出聲來。這時劉大叔叫女兒把已準備好的刀叉拿了過來,一人一套,這可得心應手,幾個兵熟練使用刀叉下手,大口咀嚼起來,一邊吃著,一邊還哈拉少,哈拉少誇個不停,直稱讚你們中國菜太好吃了。酒過三巡,三瓶60度的二鍋頭早已下肚,一個個喝的酒酣耳熱。這時外面街上響起了噼裡啪啦的鞭炮聲,時候不早了,幾個人都有點醉意。他們怕耽誤回軍營時間,穿好衣服,踉蹌地走到外屋,就在他們和主人寒暄著告別時,有兩個兵瞅著主人不注意時,把供桌上的供品全部劃拉劃拉裝到大衣兜裡。等全家人送完客人回屋,才發現供桌上已經溜光了。劉大叔苦笑著說:“這些騷撻子(蘇軍士兵的別稱)可真能作”,只好又拿出一些果瓜梨棗,點心之類重新擺上。
蘇軍撤離小平島
1955年初冬的一個上午,天空蔚藍,豔陽高照。這天我們解放軍和蘇軍進行交接儀式,蘇軍要撤離小平島了。我們都早早地出來,在現場觀看。只見一支穿著嶄新的棉軍裝,肩扛各種輕重武器的隊伍,唱著嘹亮的軍歌,邁著整齊的步伐,由小平島北面向島的南頭挺進。他們就是第一次踏上這塊土地的我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邊防團的一個連隊,他們奉命到這個島接管蘇軍炮兵連營地和進行交接任務。
這時街道兩旁已聚滿了當地居民,他們揮動著手中的小國旗,不斷高呼: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人民解放軍萬歲。爭相目睹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的人民子弟兵的風采。行進中的解放軍官兵們也揮手向老鄉們表示致意。
在歡迎的人群中,有一個姓邵的老漢,十多年前,他唯一的兒子,離開家鄉,隻身到北面參加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隊伍打鬼子,一別多年,杳無音訊。直到兩年前,市人民政府送來烈士證書,方知身為志願軍團長的兒子,已英勇犧牲在抗美援朝的戰場上。今天這位老人看見這些年輕的解放軍戰士,就象看見久別的親人,不由地老淚縱橫。
此時,蘇軍炮兵連官兵也穿著新軍裝,整齊列隊在營區前的空場地上,等待解放軍的到來。訓練場上排列著的十幾輛軍車和十幾門火炮,擦拭得錚明瓦亮的炮身在陽光下熠熠發光。隨著一、二、三、四的口令聲,只見我方邊防連官兵威武地來到場地,和蘇軍炮兵連官兵面對面列隊。這時,交接儀式開始。雙方各走出一名軍官,相互敬禮,握手致意。首先我方軍官說到:“從今天開始,你們下崗,我們上崗,祝你們一路平安。”然後是蘇軍官致詞:“歡迎你們的到來,我們把營區完整地移交給你們,望你們盡到保衛祖國的使命。”
然後升降國旗。首先蘇聯那面鐮刀錘子的國旗慢慢降下來,緊接著兩名解放軍升旗手,雙手捧著國旗,正步走向旗杆下。把我們國旗徐徐升起。當鮮豔的五星紅旗在旗杆頂端迎風緩緩飄揚時,現場的戰士和群眾,發出陣陣的歡呼聲和熱烈的掌聲。有幾位年愈古稀的老漁民看到眼前的情景,感概萬分,思緒萬千,他們曾經歷過在日本統治下的四十年毫無尊嚴亡國奴的悲慘日子,後來蘇軍光復大連,進駐小平島,人們的生活況才慢慢得到改善。但那畢竟是別國的軍隊,今天,我們國家自己的軍隊進駐,才使人們真心感受到當家做主的揚眉吐氣。
交接儀式結束後,只見兩國士兵們熱烈地擁抱在一起,有的情不自盡地把軍帽拋向空中,只聽到蘇軍士兵高喊著:“烏拉”。我方戰士則高呼:“萬歲。”
11時整,蘇軍士兵列隊分別登上十幾輛牽引著火炮的軍車,在汽車引擎的隆隆聲中,依次向北駛去。這時街道兩旁的人們在歡迎解放軍隊伍後,又變成歡送蘇軍隊伍。他們揮舞著中蘇兩國小國旗,高呼著中蘇兩國人民友好的口號,在和蘇軍士兵做最後的告別,而車上的蘇軍士兵看到車下熟悉老鄉時,拼命揮手,並致最後一個軍禮。這時我和我的小夥伴們發現一輛軍車上兩個平時最要好計程車兵,一個叫瓦西里,個子不高,長個娃娃臉,臉上還有幾粒斑雀,另一個叫阿廖沙,個子高點,長得比較壯實,都是十八、九歲,是去年初從國內調來輪換的兵。
我小時候因感冒,鼻子受病,因此說話有時囔囔的。這兩個兵就學我說話腔調,氣得我直罵他倆,他們不但不惱,還哈哈大笑,並故意逗我。不打不成交,日後我們成了好朋友,鐵哥們,閒時經常和我們這幾個半大小子在一起玩耍,有時還到我們家中串門。在一起時間長了,我們還跟他學會幾句簡單的蘇聯話,他們也跟我們學會幾句漢語單詞。一次瓦西里還從懷裡掏出一張老照片,是全家福照片,他指著其中一個穿著軍裝的帥小夥,比比劃劃對我們說,那是他大哥,是個坦克兵,在二戰後期攻打柏林戰役中壯烈犧牲。阿廖沙也告訴我們,他的一個姐姐和一個叔叔也在二戰的戰場上為國捐軀。看來德,日兩國法西斯是世界愛好和平國家的共同敵人。
這時車上的瓦西里和阿廖沙似乎也看到了我們幾個,用勁地向我們招手呼喊著,還不時用手背擦拭眼睛。我們也不斷向他們揮手,高喊著他倆的名字,並追著車跑了好長一段。望著漸漸遠去的車輛和消失的人影,心中湧上難掩的不捨之情,兩行淚水奪眶而出。再見了,親愛的蘇軍老大哥,再見了,親愛的朋友,祝你們一路平安,早日回到你們遙遠的祖國和久別的家鄉!
作者簡介
喬世楨,男,歷任大連水產養殖集團中高層管理者。喜好文學寫作,作品散見於大連日報等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