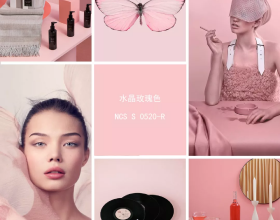那一年生產隊的穀子長得特別好,穀穗向大地跪拜很虔誠,沒有東張西望漫不經心的姿態。在手心上搓搓穀穗子,一粒粒金光閃閃映著光芒。社員們臉上笑出了褶,裝著秋收的一汪汪汗滴。
“馮大煙袋”胳肢窩夾著一把鐮刀,笑眯眯地望著如人一樣高的谷地,心裡盤算著分紅後給兒子過“二茬禮”,樂呵呵地當老公公的事。
打頭的“高粱馬”看見社員來差不多了,毫無表情地喊了一句:“今年割穀子,捆都整小點兒,別他媽的捆成‘累死爹’”
習慣了,隊里人說話多少都帶口頭語兒,好像不說口頭語兒,話就從嘴裡摳不出來。這句“他媽的”其實不是罵人,大家聽了不但感覺不刺耳,還覺得挺舒服、親切、情感距離更近了。
“高粱馬”說得“累死爹”,是車老闆子拉穀子咬牙切齒罵出來的話。割穀子的時候,有人偷懶,捆大捆谷個子。割穀子人減少了捆穀子的個數,可累壞裝車的人。裝車的人用垛叉往車上挑谷捆子,剛開始還行,車越裝越高,裝最上面,挑谷捆子的人費勁特別大,大個谷捆子,怎麼也挑不上去,把“吃奶”的勁都使出來,弄不好,反作用力,弄老闆子一個腚蹲,不罵捆穀子的人才怪。
我又是和“馮大煙袋”挨鋪子(壟)。頭一次割穀子,不知道深淺,以為比割黃豆輕巧。不料,一伸刀,傻眼了。這穀子長得太壯實,一壟穀子,鐮刀根本掏不透亮,抓一把穀子稈,別人割一刀,我非割兩刀才能夠割下來。不一會兒,“馮大煙袋”就拉我好幾十米遠。他不慌不忙地在那抽菸,看天空上遠飛的雁。
社員們割到半截地,我才在地邊開個頭。“馮大煙袋”走過來,看看我割的茬口,很不高興地說:“你留這麼高的茬子,生產隊的馬吃啥,我不是隊長,要我是隊長,非踢你幾腳不可.....”
看看自己割過的壟,“馮大煙袋”說我也不屈,是比別人割的茬口高出很多很多,真是“鶴立雞群”。
“馮大煙袋”瞪我一眼走了,扔下一句話:“就會叨咕書本上那幾個字”。“馮大煙袋”說的是我每天上工前,完成隊長交給的任務:“天天讀報”。
過了很久,我呼哧帶喘割到“馮大煙袋”剛才抽菸的地方,有些驚異:他幫我割了兩根壟。此時此刻,我的心如打翻了五味瓶,不知道酸甜苦辣鹹啥滋味。
割穀子有竅門,老農民都知道,割在最前面最輕巧。輕巧就在碼谷碼子上,穀子割下來捆成捆後,不能馬上運到場院去,需要碼成碼子,晾曬一些日子,再運回場院碼大垛,省得焐垛。在割地的時候在地裡碼谷碼子,一般是三個人一趟子,第一人最省勁,谷捆子直接放在地上,第二人接著往上碼,第三個人碼最上面,谷碼子已經碼很高,然後,還要把谷碼子做成草帽狀,免得秋雨澆。可想而知,我當然是最後一個人。
秋天,天黑得早,收工的社員陸陸續續夾著鐮刀回家,有的人根本看不出來累的樣子,哼哼著二人轉小段悠悠自在走進炊煙中中。當我碼完最後一碼子時,已經累得眼前冒金花,身不由己地癱在地上。
老隊長從別的地塊拐過來,看見我累的那個“熊”樣,望望我割的穀子茬子直拌腳,有些疼愛又生氣地說:“你真是不是幹莊稼活的料啊,明天你去割麻籽吧!”
老隊長不理我了,走了。
我孤零零站在空曠的谷地裡,真找不到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