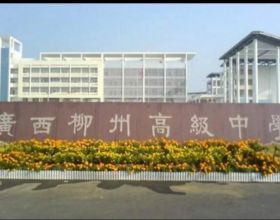“電視劇主要透過人物的臺詞來推進故事,帶出節奏;電影主要透過氛圍來帶節奏,它更強調光線、色調、鏡頭轉換以及背景音樂的重要性,拍《紅燈記》我們做了很多這方面的嘗試。”習辛說。
正是基於習辛及其「鐵軍」在拍攝過程中傾注的強大創新,《紅燈記》於2021年初與李路導演的《巡迴檢察組》共摘「2020年度最佳導演」桂冠。
又是一年九一八。
這一天,防空警報像噴火的蛟龍在空中怒吼,馬路上望不到頭的汽車駐足雙閃嘶鳴。
每當這個時候,演員張立君胳膊上的汗毛就會豎起來。
對於一個從哈爾濱話劇院退休的資深表演藝術家而言,他有足夠地自信去塑造任何一個角色。
然而在紅色經典電視劇《紅燈記》裡,張立君飾演日本軍官鳩山時卻說:“我這輩子最不想演的就是日本鬼子。”
以至於在劇組的時候,他不願多看一眼鏡子裡自己的妝容。
一方面,在內心深處他非常感激導演習辛的起用,後者多部經典作品裡都有張立君出彩兒的身影;另一方面在進入角色的過程中,他委實痛苦不堪。
“尤其在揣摩鳩山的心理和舉止形態時,氣得我後背冒汗。”張立君說。
瞭解張立君的人都知道,這是一個為人和善、性格溫和且帶著幾分學者氣息的智慧型演員。這樣的人物感覺能否和日寇的窮兇極惡匹配得上?
在我看來,導演習辛就是要運用張立君身上的這些特質,讓其和鳩山身上的狡猾陰騭、老謀深算,有一個顛覆性的連線。
這樣的神來之筆不止一處。
反向選角
2019年3月,習辛邀請於洋出演《紅燈記》時,於洋的第一反應是興奮的:“我下意識地想,李玉和這個角色太經典了,儘管從年齡上看我略顯嫩,但也沒有問題。”
電話那端傳來習辛的聲音“你演王連舉”。
於洋的腦袋“嗡”的一聲:“這可是在所有叛徒、漢奸形象中,能排進前三名的人物啊!”
於洋在《外交風雲》中飾演外交官喬冠華,在《大秦帝國之裂變》中飾演景監。
讓這樣一個神采奕奕、風度翩翩、一身正氣,且在顏值上近乎完美的「男神」飾演叛徒王連舉,習辛究竟是怎麼想的?
“在一部作品裡,戲劇的衝突性非常重要,它不只體現在故事的線索和節奏裡,更體現在人物性格和形象的塑造過程中。”習辛說。
說白了,一個看上去越不可能做叛徒的人,最後卻出賣了自己的革命同志,它的前後反襯效果越不是一般的強。
從觀劇的角度看,越是讓老百姓恨得牙根癢癢的人物身上,越是具備警醒的意義。
深層警醒
恨其表更要恨其裡,尤其要從中找到警醒的價值和戰勝考驗的力量。這是導演習辛在王連舉這個「反面教材人物」身上,埋著的對人性轉變、善惡抉擇的一支伏筆。
在真實的歷史人物中,大漢奸汪精衛也長著一張耐看的臉,其早年身為革命黨人行刺清末攝政王未遂被捕後,在獄中寫下絕命詩:慷慨歌燕士,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這個人從什麼時候開始棄明投暗,一定有其至軟時刻和某種人性漏洞。
所謂千里之堤,潰於蟻穴;堡壘不是一天攻破的。
那麼,王連舉身上的漏洞是什麼,他的革命意志由堅強滑向軟弱的原因是什麼?
相較於樣板戲,這可能是劇版 《紅燈記》較為深刻的不同之一。
也就是說,王連舉的堡壘是如何被敵人破防的,他的死穴在哪裡。
他也曾有過「引刀成一快」的瞬間壯舉:為了救李玉和曾往自己身上打過一槍。用飾演者於洋的話說,王連舉並非貪生怕死之輩,“他做了那麼多年的地下黨,腦袋每天都拴在褲腰上執行任務,在邏輯和主觀意志上,他肯定不想當叛徒。”
這決非為革命同志投敵當叛徒做合情或合理化的解釋,而是在犀利的正視其背後的深層原因。比起那些抗日神劇,這才是源自現實主義的客觀警醒。
既然王連舉不怕死,他為什麼還是做了叛徒?
是情感上的折磨。只要他肯投敵,鳩山就放生他心愛的女人,讓他們過上富足的日子;否則,愛人必死無疑。
這樣的脅迫或誘惑即使在當下也依然存在。在電視劇《人民的名義》中,蔡成功對發小侯亮平說「要想腐蝕你,我用的是票子、女子、房子」,就是對某些現實情況的反照。
在現實中,脅迫通常都是誘惑的預備隊,有些人能守住前者的持久包圍,卻未必能敵過後者的閃電戰。
可以說,在王連舉身上的這支重筆,寫下的是對歷史和現實的雙重警醒。
就這樣,王連舉由一位曾經的熱血男兒終變叛徒敗類。
“革命意志是要能經受得住任何考驗的。相形之下,李玉和、李奶奶、鐵梅身上的大無畏革命精神和堅強的鬥爭意志,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必備的優秀品質。”習辛說。
從藝術創作的角度看,習辛及其「鐵軍」為王連舉增設的這條感情線,相當於在他身上劃開了一道人性的口子,它使得這個人物更生動、更具象、更具有警示意義。
倘若沒有這道口子,某種程度上,劇版《紅燈記》就容易重蹈樣板戲版《紅燈記》的「三突出」覆轍。
「三突出」是指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倡導的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文藝創作模式。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即中心人物"。「三突出」的文藝創作模式違反生活的真實性和多樣性,人為地神化英雄人物,使英雄人物脫離群眾,宣揚了歷史唯心主義,也使當時的文藝作品中人物形象千人一面,人物關係千篇一律。
說白了,就是在藝術創作中,讓「英雄天生就是英雄,讓叛徒從小就是叛徒」。這其實是選擇性忽視了正面人物的成長曆程、經受住考驗的鬥爭力量和經驗,以及對負面人物走向墮落的防微杜漸層面的警醒。
原中央電視臺臺長、現為央視專家審片組成員的張華山看過《紅燈記》後指出:劇創在遵守原作的基礎上有昇華、有情節、有突破、有高度;服化道非常有質感,光感線條流暢,節奏輕重緩急到位;演員搭配成功,每位藝術家都是用心在創作;不「三突出」,但人物的形象更豐滿、更細膩、更準確。
硬骨頭
我們看一個正劇領軍人物,一個長期主義奉行者,是怎樣透過二十餘載的積澱,在一部又一部膾炙人口的作品中構建自己的「家國情懷」。
《二叔》《三妹》《繼父回家》《回家的路有多遠》《孃親舅大》聚焦的是「一個個小人物身上的人間大愛」,這屬於「家」的維度;《正是青春璀璨時》《紅燈記》《當祖國需要我們的時候》宣揚的是「為國奉獻、熱血擔當」,這屬於「國」的維度。
“一個導演在自己作品《孃親舅大》一舉打破CCTV8九年收視記錄後,沒有在自己的舒適區內繼續暢遊,而是轉向紅色、軍旅劇的創作和拍攝,這本身就是一種極具勇氣和擔當的作為。”一位電視臺高層這樣說。
這部《紅燈記》,就是習辛及其「鐵軍」在《孃親舅大》後創作的「正、當、紅」三部曲裡的第二部。
《正是青春璀璨時》和《當祖國需要我們的時候》的創作難度有兩個共同點:故事背景的時間跨度都在幾十年之巨;拍攝的自然條件都極其艱難。
雖然《紅燈記》的拍攝條件也面臨了「三伏天拍攝 三九天戲份」的挑戰,但與「正、當」相比,它的最大難度首先在於「如何落地」。
“舞臺上的戲劇橋段和可以實拍的鏡頭化語言之間,其實隔著一條鴻溝。”習辛說。
這非常考驗一個創作團隊的原創能力;很大程度上,它比重寫一部作品還要有難度。
“這是一罈至少影響過兩代人的老佳釀,它的知名度、醇厚度,本身也是最大的難度。”習辛說。
這可能正是先前幾波拍攝團隊選擇放棄的原因:步子邁小了容易被罵守舊,步子邁大了容易被批胡扯。
如何讓這部經典大作在保證本色原味的基礎上,變得更好看、更符合當下老百姓的觀感體驗,尤其是年輕人的審美。這是一個極具挑戰的難題。
“要知道,這部《紅燈記》的最終落點在「傳承」,即「革命自有後來人」,讓更多的年輕人觀看這部劇,是它重要的使命之一。”習辛說。
既知守正,以何創新。
「鐵軍」團隊經過密集的論證,得出了答案:既然原作的故事架構、人物關係、相關線索都不能改,我們就在鏡頭和氛圍感上下足工夫。
所以,《紅燈記》開篇即是驚豔:
一個長鏡頭,由遠及近,沿著滿洲里的青石街道,帶著陰冷的光線、隱晦的氣息,一點點地向一座劇場推進。
它就像是《諜影重重》裡的馬特達蒙,在用狙擊槍向暗處搜尋目標。
鏡頭“掀開”劇場棉厚的門簾,近處是一席青幽的色調,遠處的戲臺樁上,掛著血紅的燈籠。
青紅之間,鏡頭“瘮著人”的繼續向戲臺推進,沿途是幽暗的座位,以及那些看著就覺弔詭的人。
這個時候,鼓點響了,大戲開場了。
懸念,殺機。導演用一個長鏡頭,就把緊張地氛圍迅速的營造出來,觀眾瞬間就被“抓住了,帶進去了”。
習辛說:“電視劇主要是透過人物的臺詞來推進故事,帶出節奏;電影主要是透過氛圍來帶節奏,它更強調光線、色調、鏡頭轉換以及背景音樂的重要性。這次拍《紅燈記》,我們做了很多這方面的嘗試。”
「鐵軍」的製片主任程建波告訴我,這個鏡頭從晚上7點,一直拍到凌晨3點。
那些刺殺、戰鬥的場面,導演採取了極其凌厲的手法,決不拖泥帶水。甚至從一些鏡頭的切換中,可以看到真人CS的感覺。
“我以往的作品,主要圍繞親情戲展開,那裡面的人物之間也有衝突,但不存在生死存亡的危機瞬間。所以在《紅燈記》的拍攝過程中,我們始終強調‘張馳有度’。”習辛說。
他要的“張”,是千鈞一髮、電光火石;他要的“馳”,是綿綿不絕、九曲迴腸。
正是基於習辛及其 「鐵軍」在拍攝過程中傾注的強大創新,《紅燈記》於2021年初與李路導演的《巡迴檢察組》共摘「2020年度最佳導演」桂冠。
行業不會辜負一個真正的匠人,因為他們「都有一顆紅亮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