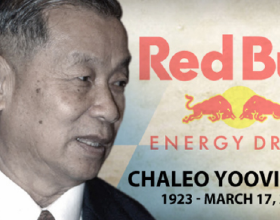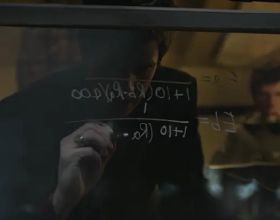提起張瑞芳,人們便會將她與電影《李雙雙》聯絡在一起。這部電影的成功使她名聲大噪,斬獲百花獎最佳女演員,一躍成為當時的“四大名旦”之一。
電影中她性格潑辣心直口快的喜劇形象深入人心,可現實世界的她在感情上卻是一波三折。
世人都知她歷經三段婚姻,都未能終老,而她始終沒能忘記曾經的初戀,令她牢牢放在心上七十載。
關於張瑞芳的初戀——鄭曾祜,她很少向外人提起,或許是曾經的白月光逐漸成為了心中的硃砂痣。直到快去世的時候,她才將這段年少的愛戀公之於眾。
1935年,17歲的張瑞芳考入了北平國立藝專主修西洋畫,她希望能夠延續父親未盡的事業,用自己的畫作喚醒國人的意識,為民族的獨立儘自己的一份力量。
她的父親張基,曾是陸軍大學的炮兵教官,擔任過北伐軍團炮兵總指揮。在張瑞芳十歲那年,張基因為指揮戰鬥失敗,而英勇就義。
父親的死,猶如一顆火種,深深地埋進了她的心中。
1935年,華北事變,當她看到報紙上那些血淋淋的照片,自己的同胞一個個躺在血泊中,她的眼淚在眼眶打轉,她狠狠地咬緊了牙齒,好似要把牙咬碎了。一頭扎進畫室將敵人的所作所為都畫進了畫裡,也將她的一腔恨意融進了畫裡,正當她思緒泉湧時,樓下傳來叮叮噹噹的敲擊聲,擾得她無法專心創作。
她氣呼呼地衝到樓下的教室,正當她準備對著那人問責時,卻發現一個身穿白襯衫的男孩子正滿頭大汗地敲擊著一塊木頭,一時她看得出了神。
這個男孩子便是鄭曾祜。
鄭曾祜注意到門外站立的女子,走上前來:“那個是不是我吵到你了 ,真是不好意思。”
面對對方的提問張瑞芳竟刷得一下臉紅了,回過神的她連忙說:“沒有沒有,我只是無意間應聽到聲音,過來看看。”
男孩微微一笑。
“你好,我叫鄭曾祜,雕塑系的。”
“你好,我叫張瑞芳,是西洋畫系的,我的畫室就你的樓上。”
從那之後二人開始漸漸熟絡,每到吃飯的時候,張瑞芳便會用她的高跟鞋在地上狠狠地踩幾下。收到暗示的鄭曾祜,便會放下手中的事情,和在走廊等他的張瑞芳一起去餐廳吃飯。
他們互相分享自己的創作靈感,談論夢想,兩顆熱愛藝術心在慢慢地靠近。
不久,北平國立藝專掀起了學潮,為了推翻舊校長,學生們推舉張瑞芳和鄭曾祜為代表與學校談判。
鄭曾祜的發言讓張瑞芳更加肯定他就是和自己志同道合的夥伴。
之後每天放學,鄭曾祜都會先把他送到家,再掉頭回去。兩人也常常約著一起外出郊遊。
張瑞芳的母親也開玩笑似地說:“乾脆等你們畢業了就結婚吧。”
張瑞芳永遠記得那段輕鬆愉快的日子。
後來,張瑞芳經朋友的引薦加入了“愛美劇團”,開始出演愛國話劇。
1937年七七事變,面對日本人無情的親率和殺戮,滿懷愛國熱血的她加入了“民族先鋒隊”,根據上級的安排被調往重慶。
臨走前她與鄭曾祜見了一面:“我馬上要去重慶了,投入到抗日救亡的運動中去,去完成我們共同的理想,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
鄭曾祜肯定地點了點頭。
他們相約三日後在碼頭碰面,適時一起乘船去重慶。
到了相約的時間,碼頭的張瑞芳怎麼也等不到他,只好獨自趕往重慶。
後來鄭曾祜來信說:“親愛的瑞芳,我本已經決定隨你一起到重慶去,一起完成我們的理想,但不曾想出發那日,我被父母發現,強行鎖在家中。終是無法同你一起了。”
19歲的張瑞芳與鄭曾祜分開,一個在重慶投入到抗日愛國的宣傳中,一個在北平繼續學習。
起初的兩人一直有著信件的來往,可隨著時間的推移,鄭曾祜在父母恩安排下前往美國留學,自此兩人斷了聯絡。
1939年,21歲的張瑞芳隨中華劇藝社輾轉來到北平的一所私立女子中學排練劇目《心病者》,認識了她的第一任丈夫導演餘克稷。
餘克稷早在1937年在重慶創辦了怒吼劇社並導演了《保衛盧溝橋》這一愛國劇目,一聲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喚醒了還沉溺在安逸生活中的中國人民。
排練劇目期間,餘克稷常常單獨與張瑞芳講戲。她被他的創作才華所吸引,隨著話劇《心病者》的大獲成功,兩人的感情也漸漸升溫,走在了一起。
陰差陽錯,鄭曾祜學成歸國再次見到心心念唸的初戀時,她已嫁作人婦。兩年後,迫於父母的壓力無奈他也與別人成婚。
《歲月有情——張瑞芳回憶錄》中提到:“我從未見過他的妻子,但從朋友的耳中聽說,她長得有些像我。”
婚後張瑞芳和餘克稷兩人一同投入到了愛國劇目的宣傳中,他們是志同道合的夥伴,卻終究不是能夠相互陪伴的愛人。
晚年的張瑞芳回憶起他與餘克稷的這段婚姻時說:“他將所有的熱情和心血都投入到了話劇創作中,當我和他一起探討話劇時,他像是一團火,無比的熾熱,但除了話劇以外我們幾乎沒有任何的溝通,生活裡的他就如同一塊冰,怎麼捂也捂不熱。”
在婚姻中碰壁的張瑞芳,在事業上迎來了新的發展。
她受到郭沫若的邀請出演歷史劇《屈原》中的嬋娟一角。結識了羅曼蒂克式的“話劇皇帝”金山。
此時的金山剛剛與王瑩分手,正處於失戀期。情感豐富且細膩的金山很快陷入了屈原的角色,無可救藥的愛上了張瑞芳,他毫不遮掩地向張瑞芳表露心意。
作為有夫之婦的張瑞芳有意地與金山疏遠,想要擺脫這段本不應該存在的情感。
恰逢張瑞芳的姐姐懷孕寄住在她家中,忙於演出的她無暇陪伴姐姐,臨近生產的那段時間,他囑託丈夫:“一定要照顧好姐姐。”
一日她排練回家發現姐姐不見了,便詢問丈夫緣由。餘克稷告訴她:“姐姐有些不舒服,自己叫車去醫院了”。
她大聲斥責道:“你怎麼能讓姐姐一個人去醫院?她隨時可能要生了”
她急忙趕往醫院,果然姐姐難產,好在司機送的及時,才保住孩子。
因為姐姐的事情,她的心裡一直對丈夫有心有怨言,但礙於身份的原因兩人一直維持著婚姻關係。
直到一次她看到母親寄來的書信,信中寫道:“年幼的弟弟身染瘧疾去世了。”得知訊息的她失聲痛哭,一旁的丈夫詢問後只回了一聲“哦”。
冰冷的一個字擊碎了她內心的最後一絲希冀。也許她從未真正走進他的心裡。
1945年,張瑞芳與餘克稷辦理了離婚。
或許命運就愛作弄人。她恢復了單身,他卻已為人夫、人父。
金山得知張瑞芳離婚的訊息後,對於張瑞芳的追求更加熱烈。
她喜歡看電影,他便主動邀她一起,帶她去舞廳跳舞,介紹他的朋友給她。但這些都被張瑞芳婉拒了。她想到了離開,想要擺脫現在的處境和心態,換一個地方開始新的生活。
儘管她能感覺到,這個男人正在努力地融入她的生活。
不料,金山找到了鄭曾祜來當說客:“金山是一個情感熱烈的人,他也和你一樣在感情上受過傷。他的性子是一旦陷進愛情便會全心全意的投入進去的,如果你也對他有感覺,不如成全彼此。”
此時的張瑞芳眼裡噙滿了淚水。他都已經放下了,我還有什麼放不下的。
在鄭曾祜的勸說下,她不再處處躲著金山。
一日排演結束,金山叫住了轉身要走的她:“我們找個安靜的地方談談吧。”
兩人來到了走廊盡頭的樓梯間。
“那天晚上,我看到你了,我喜歡你,不僅是因為我迷戀和你在一起的那種感覺,更是因為我們有著共同的信仰”。
聽到這話的張瑞芳震驚了,早在1938年她就已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而作為杜月笙弟子他自然也是自己的同志。
兩人在杜月笙的見證下結為夫婦。鄭曾祜看到張瑞芳有了一個愛她護她的人,便放心前往臺灣工作。
婚後金山給予了張瑞芳無微不至的關愛。
逛街時看到好看的飾品,會細心地幫她試戴,還會大聲地讚美她。每次出差都會帶禮物給她。
在金山的呵護和陪伴下,她心裡的傷口漸漸癒合。
都說七年之癢,隨著時間的流逝兩人的感情漸漸歸於平淡,可金山是一個需要情感澆灌的人,他就是為浪漫而生的。
抗戰勝利後,她隨金山一同進入北京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工作。並參與演出了劇目《保爾·柯察金》,導演是剛從蘇聯回來的女留學生孫維世。
隨著抗日戰爭的勝利,一系列宣揚愛國主義的抗戰大劇開始籌備。
1951年,《南征北戰》的導演找到張瑞芳希望她能出演女游擊隊長趙玉敏一角。拿到劇本後,她驚喜地發現這不正是我想成為的樣子嗎?隨即爽快答應了邀約。
為了能夠塑造好這個角色,她背上行囊來到鄉下一住就是八個月。每天和村裡的農婦學習編草鞋、納鞋底,就連導演都說:“這不正是我們的女游擊隊長嗎?”
這八個月,成就了她的事業,也給了有心之人可乘之機。
她從劇組回來後發現丈夫與孫維世舉動親密,關係異常。面對金山的出軌,張瑞芳選擇了退出,兩人辦理了離婚手續。
1956年,張瑞芳出演巴金的話劇《家》,扮演覺新的妻子瑞珏,當她面對覺新和梅說出“我願意成全你們”這一句臺詞時,她猛然間似乎理解了金山與孫維世的情感。
經歷過兩次失敗婚姻的張瑞芳離開北京來到了上海,遇見了他生命中的第三任丈夫嚴勵。
初到上海電影製作廠的張瑞芳對很多事情都不適應,忙於工作的她根本不知道怎麼照顧好自己。
正好有一對夫婦就住在裡離廠子不遠的地方,由於要照顧小孩子,便專門請了一個阿姨做飯,廠裡的很多“光棍”都在那裡包飯。漸漸地張瑞芳和嚴勵便成了長期飯友。
深入瞭解之後,她發現原來嚴勵雖然其貌不揚,但也是極有才華的。
他曾經做過編劇,對演戲有自己的見解,喜歡畫畫,還寫得一手好字,為人也十分親和,更重要的是他與鄭曾祜長得竟有幾分的相似。
她的朋友秦怡曾勸她:“總是這麼一個人也不行,你又不會照顧自己,還是找個知心的人吧。”
朋友們都建議可以考慮一下嚴勵。
此時的張瑞芳不想再追求什麼熾熱的愛情,只想平穩踏實的生活,演好每一個角色。
嚴勵是上海電影製作廠的廠長,一個老實憨厚的中年男子。他不像餘克稷那麼冷漠,也沒有金山那麼多情,是個適合過日子的男人。
在朋友的撮合下,兩人決定在十月革命節結婚。
結婚當天恰逢張瑞芳收到中蘇友好聯歡的邀請。兩人商議後決定先去參加聯歡,回來後再結婚。
這邊中蘇友好聯歡隆重地舉行,人們載歌載舞,另一邊嚴勵緊鑼密鼓的佈置著婚禮的各項事宜。
聯歡中途張瑞芳提出要提早離開,朋友們攔著她:“你可不能走,還有好多外賓排著隊等著跟你跳舞呢?”
“不能不走啊,我今天結婚。”
“啊!你結婚啊,那你快走吧”
兩人的婚禮在這場在嬉鬧中結束。
1987年,鄭曾祜從臺灣回大陸探親,回國的後的他第一時間找到金山打聽張瑞芳的訊息,卻聽說金山移情別戀兩人離婚的訊息。他對著金山便是一通斥責。
經過多方打聽後找到了在上海的張瑞芳。
他看著眼前的這個女人,心裡是又氣又疼。
一日,鄭曾祜來到張瑞芳家做客,一進門他便激動地握住了嚴勵的手:“謝謝你照顧她,給她幸福。”
嚴勵笑著說道:“瑞芳是我妻子,我自然是要照顧好的。”
鄭曾祜意識到了自己的失態,連忙抽回手。
兩個已經耄耋之年的七旬老人,一見如故,相談甚歡。
對於鄭曾祜來說,張瑞芳從白月光變成了他的硃砂痣,現在的他只希望她能過得幸福健康。
他們誰也沒有想到,這次的見面會是最後一次。
此後的每一年春節,鄭曾祜都會第一時間打電話給她,詢問她的生活和身體狀況。
每隔一段時間都寄來幾身臺灣新款的衣服給她和嚴勵,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寄來的衣服都出奇的合身。
突然有一年春節,張瑞芳照例接到了鄭曾祜打來的電話,但電話的那頭只傳來了嚶嚶的哭聲,她的心咯噔了一下。
詢問後才知道原來鄭曾祜因為中風再也不能說話了,今後再也聽不到他的那一句:“你在上海還好嗎?”
張瑞芳淚如雨下。
1999年,丈夫嚴勵因病去世。面對丈夫和摯友的接連離去,張瑞芳悲痛欲絕。
退休後的她用自己所有的積蓄修建了一座叫“愛晚亭”的敬老院,她常常拿出著自己與鄭曾祜的合照一看就是一個下午。
那張合照是在北平平國立藝專時的一次同學聚會時,在大家的起鬨中拍攝的,是兩人唯一的一張合照。
2012年,張瑞芳在上海離世時,只有養子嚴佳陪在他的身邊。
彌留之際的她,緊緊地抓著養子的手,嘴裡喃喃道:“曾祜、曾祜。”
可能世上最悽美的愛情不是生離死別,而是不管你屬不屬於我,你就在那裡,只要能遠遠地看著你幸福,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