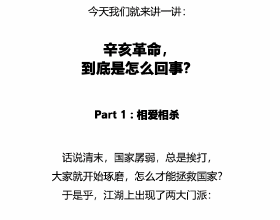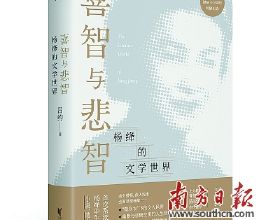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 張瑾華
1911年7月17日,是楊絳先生的誕辰日,如果活在世上,楊絳先生今年正好110歲。而先生離開我們,也已經5年多了。
她穿上”隱身衣“飄然而去,可我們不會忘記她。
作為對楊絳先生誕辰110週年的特別紀念,《喜智與悲智——楊絳的文學世界》新近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作者呂約,因為熱愛楊絳,所以研究楊絳。
呂約,詩人,文學博士。生於湖北,先後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現居北京。曾任《新京報》編委,現任十月文學院執行院長。作品發表於《人民文學》《十月》《作家》《現代詩》等海內外刊物,入選《中國新詩百年大典》等。主要作品有:詩集《呂約詩選》《回到呼吸》《破壞儀式的女人》,專著《喜智與悲智——楊絳的文學世界》,批評文集《戴面膜的女幽靈》等。曾獲首屆駱一禾詩歌獎,入選“百年新詩人物”。作品被譯為德語、義大利語、英語、西班牙語、日語等,並曾應邀參加柏林詩歌節等國際活動。
本書是一部文學評論專著,也是呂約的博士論文,原題為《楊絳論》。作為融貫中西的文學大家,楊絳先生以睿智、精純、真誠、曠達的文字俘獲了萬千讀者的心靈。本書深入淺出,詳盡解讀楊絳的全部戲劇、小說、散文作品,抉幽發微,引領讀者體察楊絳作品獨特的審美特徵、精神意蘊與文化內涵,進入這位身披“隱身衣”的智者的內心世界,領略其幽默與悲憫交織、理性與感性並舉的智慧魅力。
2014年夏,博士論文完成後,呂約的最大心願是能送到楊絳先生手上,表達她對楊絳先生的敬意與祝福。後來論文和小札一封終於送達三里河楊絳先生家中,呂約算是完成了一樁心願。呂約回憶說,其時已聽聞先生身體欠佳,唯有默默為她祝福。2016年暮春,楊絳先生與世長辭。
在呂約看來,楊絳先生只是離開她“暫住”百年的人世“驛站”,踏上她所珍視和神往的靈魂“歸途”。
【她穩健,因她總是以自我之“常”來對抗時代之“變”】
楊絳(1911—2016),原名楊季康,作家,文學翻譯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她一生經歷了“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歷史時期,創作生涯跨越“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邊界。楊絳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前期開始散文和小說創作;四十年代上海“淪陷”時期,以喜劇作家身份登上文壇;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斷文學創作,轉向外國文學翻譯和研究;八十年代以來,重新進入創作高峰期,持續不衰,影響日增。從1933年發表散文《收腳印》開始,到2014年出版小說《洗澡之後》為止,在八十餘年之久的創作歷程中,楊絳創作了戲劇、小說、散文等多種文體的作品,還有翻譯作品和研究論著,其涉及文類之廣,在二十世紀中國作家中並不多見。她的主要作品有《喜劇二種》、悲劇《風絮》、長篇小說《洗澡》、散文集《幹校六記》《將飲茶》《雜憶與雜寫》、長篇紀傳散文《我們仨》、長篇思想隨筆《走到人生邊上——自問自答》,等等。作為翻譯家,其翻譯的《堂吉訶德》《小癩子》《吉爾·布拉斯》《斐多》等西方經典名著,產生了深遠影響。作為學者,其《菲爾丁關於小說的理論》《論薩克雷〈名利場〉》《李漁論戲劇結構》《藝術與克服困難——讀〈紅樓夢〉偶記》等論文,也是學術精品。這些作品均收入八卷本《楊絳文集》之中。
以上是本書“緒論”中,關於楊絳的介紹文字。
作為融貫中西文化的民國一代作家中所剩無多的代表之一,楊絳是一位具有二十世紀文學或文化標本意義的作家,這似乎早已成為文學界的定論。
北大教授、著名學者陳曉明這樣評價楊絳先生——
楊絳先生深受一大批文藝青年熱愛,她早已是一種文化象徵,一種精神規格,一種歷史僅有的存留。2016年暮春,楊絳先生與世長辭。新聞媒體一時喧囂,紛紛聚焦這位百歲老人的愛情故事,並將其定義為“最賢的妻,最才的女”。我想,這是有偏頗的——對文學研究者來說,楊絳首先是一位具有貫通意義的中國文學家。
“現有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形塑了一種對女作家的刻板印象:她們是內心剖白的、感性的、失控的、抗議的、身體的……楊絳恰恰站在了她們的反面,她的智性、含蓄與節制讓我們看到了女性靈魂的寬度,她身上既有古代中國的隱士風流,也有現代中國的啟蒙意識,她足夠複雜,正因為她足夠真誠。”
陳曉明給《喜智與悲智——楊絳的文學世界》寫了序言,而此書脫胎於作者呂約研究楊絳的博士論文。
基於女性知識分子的共同立場,呂約首先將楊絳的創作特徵總結為“智性”,這也是楊絳與蕭紅、張愛玲、丁玲等女作家的本質區別。然而,楊絳的“智性”卻又是有溫度、有關懷的,那不是純然的客觀理性,而是理性對感性沖淡中和後的動態平衡。
陳曉明說,“呂約讀楊絳先生,是讀到書裡面去了,讀到人的心裡和風格氣韻裡去了,那都是她所向往的。呂約無疑是極為崇拜楊絳先生的,她想標舉那種人品,那種潔淨的氣質,那種心靈的自然樸實。就為文來說,楊絳先生的文藝粉絲都喜歡她的自然清雅、靈秀安靜。這點呂約也是極為著迷的,不過,作為一次理性的、理想性的把握,呂約要發掘出楊絳作品更內在的意蘊,更理論化地表述那些內涵。”
對中國文學史而言,楊絳的文學形象是相對穩健的,她總是以自我之“常”來對抗時代之“變”,而作為研究者的呂約再度發掘了楊絳的“常”中之“變”。這一正一反的兩重“變”數,打開了楊絳的闡釋空間。屢遭苦難,楊絳何以安之若素?可以想見的是,其內心必存在一種強大而有效的自我情感轉化機制:有“變”才能“通”,悲喜之間方見豁達,這自然是楊絳先生的智慧。
【試圖揭開她所珍視的隱身衣,窺見其真身與靈魂】
曾經是風生水起的媒體人,卻一個轉身做起了學術研究,成為潛心做學問的女博士。詩人呂約,又為何會完成這樣一次轉型呢?
“與自己內心的持久對話導致了我的人生道路的轉向。在體驗閱歷社會多年之後,在人生的中途,我越來越感到尋覓歸途的迫切性。我決定重新選擇,告別從事多年的新聞工作,踏上自己夢想已久卻一直若即若離的學術之路。”呂約說起自己的人生轉型。
所謂“以學術為志業”,不過是“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潛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是返璞歸真以求自我完成。呂約說自己選擇從社會重返書桌,進入一個與現實世界互補的精神世界,是返璞歸真途中的一次新生。
“文學是新生的力量來源之一。文學本來就是人生的精神伴侶,儘管二者時常發生爭執。我所理解的文學精神,是一種超越現實侷限的精神自由與語言創造,它不是消極的空想,而應該是一種充實生命的積極實踐。感謝文學賦予我的精神力量。”這是研究楊絳,書寫楊絳的呂約的內心。
作為一名研究者,呂約坦言,身處“軟紅塵裡”,塵埃蔽目,時有憂世傷生之思。此時更能體會,面對現實世界與人生的不完美,面對天人之際永恆的衝突與和解,“喜智”與“悲智”,作為人在面對自身與世界時理性與情感的雙重智慧,恰如綵鳳雙翼,缺一不可。她以為《喜智與悲智》作為書名,也是寄託了自己對某種存在境界的一種“企慕”。
對於呂約來說,研究楊絳這樣一位具有獨特詩意與文心的女性作家,是發乎性情的選擇。呂約說,“楊絳其文其思其人,深厚蘊藉而氣韻生動,是一個我希望潛心探究的語言之謎、精神之謎和文化之謎。”
呂約認為,在喧囂的當代文壇,楊絳披上“隱身衣”,將自己隱藏在一種精純蘊藉的語言文字背後。在文學史上,這一類的作家作品,雖可超越時代而流佈久遠,卻難以成為一時之熱點、競相追逐之顯學。
“在我看來,探究這樣一位作家的畢生創作,讀解其中隱藏的精神資訊,就像試圖揭開她所珍視的隱身衣,窺見其真身與靈魂,並探查其精神文化淵源。解謎的過程,就是從各種可能的角度與研究物件展開深入持久的對話。論文的寫作,即對話的結果。言有盡時,詩無達詁,而真正的對話不會終結。”呂約說。
正如學者陳曉明提到,呂約此書真正試圖提出的問題是:作為一位女知識分子,楊絳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究竟有何意義?
“我認為,楊絳的‘觀世’與‘察幾’或可成為我們觸控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另一種方式:有情卻不濫情,理性卻不功利。這本應是現代知識分子共享的基本立場,而絕非女性的性別特質。”陳曉明和觀點,與呂約形成了呼應。
當下,我們已迎來了一個空前的女性主義時代,楊絳的“智性”卻呼喚著一種更為平等的觀察視角,它直面“人性”,從而超越了“性別”,也使得任何關乎“性別”的信條都不再僵化。

本文為錢江晚報原創作品,未經許可,禁止轉載、複製、摘編、改寫及進行網路傳播等一切作品版權使用行為,否則本報將循司法途徑追究侵權人的法律責任。
來源:錢江晚報·小時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