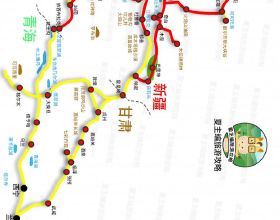我叫飛飛,今年14歲,是隻深山中的狼犬,據說我的父親是隻屢建奇功的警犬。一提狼犬,難免有人把我與齜牙咧嘴的惡犬相提並論,其實我長相蠻可愛,也沒有到垃圾堆裡搞發掘的愛好,除了有點不修邊幅,本領並不比腦圓腸肥的都市狗差。都市狗會幹啥?除了吃喝拉撒就是跟在別人屁股後瞎溜達,我實在看不慣它們那副無所事事百無聊賴的樣子。
主人可能當過兵,他一直對我進行軍事化訓練,如今我對“起立”、“臥倒”“稍息”、“立正”、“拿左手、伸右臂”之類的動作口令稔熟於心,還掌握了“取拿翻撲刨”等多項“狗技”,為了達到訓練有素的目的,主人常常帶我翻山越嶺,累得我伸著舌頭直喘粗氣。
我的主要職責是守夜,憑著我常年積累的經驗和敬業精神,家中安全基本萬無一失。我從不以衣貌取人,不管來人是蓬頭垢面還是衣冠楚楚,我都一視同仁地狂吠亂叫,直到一天晚上,我差點咬壞主人朋友而遭到嚴厲訓斥,我的那股認真勁兒才有所收斂。這世道,太認真也不是什麼好事。
我的另一職責是護園。那年秋天地裡的花生突然不翼而飛,主人懷疑是獾作的孽。表現的機會終於來了!我蹲點守候了一夜,最終將這個罪魁禍首捉拿歸案。受到肉骨頭獎賞的我從此更加留意來犯之敵,有次我追捕一隻小山喜鶓,被老喜鵲發現,那廝竟把主人的莊稼肆虐一空。對此事我一直隱瞞不報,我不會那麼傻,那不是自去討罵嗎?我的強項是狩獵,曾經捕獲野兔無數,這讓主人很引以為榮,我則在一旁扮出一副酷樣,表示這樣的雕蟲小技,不足掛齒。
最近家中來了一個城裡女子和小孩。那小孩對我似乎不懷好意,不是用水槍朝我噴射,就是用小枝戳我的黑鼻頭黑嘴圈,就算我嘴臉醜,可並不礙他,他何以如此待我?我不想得罪那媽媽,畢竟我非常需要她餵我肉鬆,所以只好忍氣吞聲,裝出一副男子漢的大度樣,小不忍則亂大謀嘛!可孩子竟趁我睡覺時踩我可愛的尾巴梢,這下我不能不給他點顏色看,否則還把我當病貓呢。我一口咬在他腳踝上,孩子立即驚怖地,哇哇地逃掉。
那女子聞聲風馳電掣般的跑來,我並沒有覺得自己有什麼不對,用眼神向她申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道理,她卻無視我無辜的眼神,不容我辯解,打斷說,他是個3歲孩子,你大他10歲,難道還與他一般見識?我素日認為你與眾不同,是隻通人性的狗狗,誰知你獸性難改!一番話說得我無地自容。
人類的事我不太懂,但從這件事,我真正明白了一個道理,女人這東西是不能輕易冒犯的,她是最能讓男人滋生勇氣的動物。主人看到現狀,毫不猶豫地一個箭步躥到廂屋,操起那個讓我觸目驚心的大掃把--那是我軍訓的專用家法,我顧不得內疚,一溜煙絕塵而去。主人鞭長莫及,在身後罵罵咧咧的恐嚇著,說回來讓他逮著就剝我的皮,悔不該把我訓練的這般疾跑如飛。那怪誰呢,誰叫我是飛飛呢!
我並沒逃遠,我還要靜觀事態發展,隱隱約約看見他們叫車去醫院。看來我的禍闖大了,真是追悔莫及。認識錯誤是需要過程的,我現在知道了,無論如何我都不應該下口咬人,那女子罵的對,我是江山易改,獸性難移。人家說的還是好聽的,我是狗改不了吃屎呀!都是我的錯!我的錯!
我不敢回家,怕他像剝兔子那樣剝我的皮,可在村裡我也算系出名門,混成個無家可歸的流浪兒,實在不甘,真不知該何去何從。直到第四天肚子餓得打內戰,才慢吞吞磨蹭回家。我審慎地察言觀色,發現主人嚴肅裡夾雜著寬恕,那女子也如釋重負地說回來就好,我吊在嗓子眼的心才放回肚子裡。
當天晚餐格外豐盛,餐後我又享受到了肉鬆,那小孩子也沒有再踩我尾巴稍兒,遠遠地躲在他媽媽身後呢,看來是曉得我的厲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