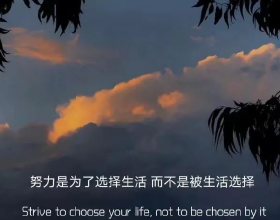《我讀齊白石》 (韓羽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6月版)中的多篇文字都曾在筆會率先發表


齊白石的畫作和韓羽手稿的運用令《我讀齊白石》裝幀設計極富中國特色和文人氣質

《白石老人自述》是一本極薄的小書。雖薄雖小,我卻以為,這是走近齊白石最重要的一本書。羅家倫的話講得好,“這是一篇很好的自傳,很好的理由是樸實無華,而且充滿了作者的鄉土氣味”。他甚至以對《史記》一般的態度講,“最動人的文學是最真誠的文學。不掩飾,不玩弄筆調,以誠摯的心情,說質樸的事實,哪能不使人感動?”
羅家倫文章的末尾,記敘其長清華大學時與陳師曾等幾位朋友訪過白石老人,對白石老人張貼畫的潤格頗有反感;讀了這篇自述,他見識了老人為生活艱苦奮鬥的情形,才將這反感“消釋於無形了”。
一部字數不多的自述,讓暮年的羅家倫(作這篇感想時他已六十六歲了)時隔三十多年(其1928年長清華大學,1930年辭)才覺出了白石翁的“好”。不過,他認為的“好”,是自述中讀到的白石老人的艱苦奮鬥,是其反覆說的自述文字的真誠與白石老人為人的厚道。於白石老人的藝術之美,羅家倫卻持有保留讚美的態度,“至於他說他的畫‘學八大山人’冷逸一路也不能說是到家。八大的畫筆奇簡而意彌深;白石殊有未逮。白石畫常以粗線條見長,龍蛇飛舞,筆力遒勁,至於畫的韻味,則斷難與八大相提並論。但在當今,已不容易了!”
其實,一個“不容易”,是無法概括白石老人藝術成就的。也許,這僅僅是歷史學家羅家倫跨界對藝術家齊白石的見仁見智的獨特理解。不過,如果真是要道出白石老人繪畫藝術的“好”,卻真真正正還是“不容易”的。
這個“不容易”,我以為只考驗著如我一般喜讀書而不懂作畫的藝術愛好者。殊不知,這個類似的問題也一直糾纏著如韓羽先生這般的藝術家。最近,從韓羽先生處“討”來一冊他的新作:《我讀齊白石》,卷首“小引”便是:“‘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是我讀白石老人畫作時必興之嘆。”如此看來,韓羽先生也長期地苦苦琢磨著白石老人繪畫的“好”與“好處”。他繼而又說:“嘆之,復好奇之,橫看豎看,邊想邊寫,有冀覓其端倪;斷斷續續,記之如下,以莛撞鐘,能耶否耶?”於文學創作、水墨藝術均有非凡實踐和傑出建樹的韓羽先生,如此彬彬自謙,如此孜孜以求,讓我這個白石老人藝術的愛好者,對他的這本小書,也有了欣欣然的特別的期待。
要說“好”,確乎是應有一個“尺度”和“標準”的。在《我讀齊白石》的“跋語”中,韓羽先生對白石老人的“定位”是從他對中國繪畫藝術史的理解開始的。他以自己“雜七雜八的印象”,把中國繪畫史分為三期:遠古時期“類似現下的裝飾圖案”的“紋樣繪畫期”;秦漢至宋元時期,“存形莫善於畫”,“明勸戒,著升沉”,描摹客觀物象,記錄現實生活,“以形寫神”“形神兼備”;到了明清時期是第三個階段,繪畫的教化功能轉向欣賞功能,畫家自我意識升階入室,由“我描畫別人”改換為“我描畫我自己”,“聊寫胸中逸氣”。韓羽先生認為,“西方,也大率類此,只是說法不同,對第三個階段,他們命曰‘現代派’,我們名曰‘文人畫’。”關於中國繪畫藝術史的分期,鄭午昌所著《中國畫學全史》(由黃賓虹作序、被餘紹宋視為“實開畫學通史之先河”,1929年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分作“實用時期、禮教時期、宗教化時期、文學化時期”。其中“禮教時期”“宗教化時期”如若合併,即是韓羽先生所謂的“教化功能”時期。而最早激賞、鼓勵、提攜白石老人的陳師曾所著的《中國繪畫史》(1922年濟南講座記錄,1925年濟南翰墨緣美術院初版),其“上古史”“中古史”“近世史”的分期與劃代則與韓羽先生幾乎完全一致。此外,陳師曾還有《文人畫的價值》的專題文章,考究起來,韓羽先生關於文人畫的體認與其觀點近乎是同氣相求的:“畫中有我”意味著“人”的覺醒,意味著畫家“自我”表達的強烈願望:既求物象之形神兼備,更強調畫家之“自我”與畫中物象融為一體。我所舉鄭午昌與陳師曾的觀點,確乎想說明,韓羽先生的藝術史觀斷不是他所言的全憑“雜七雜八的印象”。他的觀念與鄭午昌、陳師曾的不謀而合,恰可證明他的“尺度”與“座標”的合理。正是在中國繪畫史的座標上,正是在對文人畫價值的確認下,歷時數百年間,真正地體現了“既求物象之形、神兼備,更強調畫家之‘自我與畫中物象融為一體’的完美作品”,韓羽認為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明末的人物畫家陳洪綬,一個是現代花鳥畫家齊白石。
如果說,“小引”中反映了韓羽先生數十年求索探秘白石老人偉大藝術的謙謙狀態,那麼,“跋語”中這幾段一改韓公蘊藉文風的斬釘截鐵,則可看作韓羽先生數十年求索之後對於白石老人發自真心的悟知與認定。我猜想,如若沒有他悠長的文學創作實踐,如果沒有他豐厚而光彩照人的藝術成就,他的這一論斷,會不會真被當作黃口小兒的“以莛撞鐘”呢?藝術最見人心、真心、慧心,讀罷“小引” “跋語”,走進《我讀齊白石》中,讓我們一起看看韓公是如何以積數十年之功煉就的四兩撥千斤之“莛”來撞白石老人百年藝術之“鍾”的吧。
《我讀齊白石》的正文,共五十篇文字。其中五篇,曾經收在2017年北嶽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畫人畫語》中。除卻這五篇,其餘主體,都是近三年韓羽先生的新作。文字篇幅,有話則長,無話則短,伸縮自如,靈活灑脫;除兩篇專談日記與詩的文章外,均採取正面進攻的“打法”,即“看畫說話”,用韓羽“小引”裡的話是“橫看豎看,邊想邊寫”,用文學研究的專業說法,大概即是文字細讀法。
正文之外,韓羽先生與編輯一道工作,儘可能配了他所談論的白石老人的畫作。這些畫作,由中國知網檢索可以看到,自上世紀五十年代起,即廣泛地見諸於各類報刊,且為藝術同道與研究論者反覆提及或論述。以《王朝聞文藝論集》所收其不同時期寫作的齊白石的專題文章看[王朝聞的三篇文章,一為《傑出的畫家齊白石——祝賀齊白石的九十三歲壽辰》,《王朝聞文藝論集》(第一集),157—167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79年4月第1版,文末注“發表在一九五二年一月八日《人民日報》”有誤,時間應為“1953年”;二為《再讀齊白石的畫》,《王朝聞文藝論集》(第二集),63—74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文末有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號《美術》發表”;三為《齊白石畫集》序,《王朝聞文藝論集》(第三集),240—256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1月第1版,文末有注:“《文藝報》一九六二年第十二期發表”],韓羽談論的齊白石畫作的大部與王朝聞文章提及(舉例)的白石老人的作品大體也是一致的。只是王朝聞所談極為簡約,而韓羽先生則是一路窮追猛打,刨根問底。面對業已經典化的白石老人的作品,韓羽先生的細讀雖顯得“笨拙”,然經其妙手抽絲剝繭之後,白石老人畫作的新鮮美好才恍然如出水芙蓉般展現在了我等一般的藝術愛好者的面前了。
王朝聞不同時期所作的三篇文章,在齊白石研究的歷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和價值,可惜的是,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其重要在於,其整體研究齊白石的開創性,作者本人的權威性和文章的時代性,以及其齊白石藝術研究諸多問題提出的首創性。在這三篇文章中,為佐證其藝術觀點,王朝聞引出了白石老人的多幅作品,但因立論的“緊迫”,談得都極為“簡約”,對這些作品未作“深度的解讀”。
同為文學創作與藝術創作的兩棲實踐者,我認為韓羽與王朝聞的心氣是相通的。不同之處在於,王朝聞旨在宏觀立論,無暇細分縷析,而韓羽重在“看畫說話”,招招皆為文字精讀。在《壯氣溢於毫端》一文中,韓羽專門談論了王朝聞所提及的齊白石的殘荷、秋荷,引《秋聲賦》作一通描摹之後,他總結道:“這是筆勢墨痕構成的形式感,使視覺、聽覺打通而形成的錯覺,是由不同感官相互暗示而獲得的心醉神迷的審美感受。”至於王朝聞提及的白石老人的“柴耙”,韓羽先生以《說柴筢》一文對白石老人這幅經典作品作了極為全面也極為深刻的解說,並進一步引申到“畫什麼”“為什麼畫”“如何畫好”以及“書”與“畫”之關係等等重要問題。對於王朝聞多次提及的“鉤絲剛一著水群魚就來”的畫面以及老舍先生《蛙聲十里出山泉》的“命題作畫”,韓羽先生都是緩緩道來,作了獨到的藝術解讀。由以上的舉例,似乎可以這樣說,王朝聞所作論齊白石的文章,如同“藝術概論課”,講的是“一般與抽象”,而韓羽先生所作的“看齊白石畫說自己話”的文章,則如同“作品賞析”,講的是個別(特殊)與具體。王朝聞、韓羽兩位先生如此的對話,超越了時空,確有一種別樣的“相談甚歡”的美好。
要說,韓羽著眼的,只是個別與具體的作品,只是一味地想“看畫說話”,覓尋白石老人作品的真正的“好”和“好處”,就這本書直接的閱讀效果,是這樣的。但透過這些文字,去體察韓羽的內心動因,我以為,他仍然是有他的問題意識和理論抱負的。白石老人的畫作,向他提出了挑戰,提出了問題,在追問與探索的過程中,也滋養了他自己的藝術,或者說,在潛意識中,他既是白石老人畫作的一般欣賞者,也是白石老人“畫論”的探求者。多年積累下來,由這一本小書,他最終完成了對中國畫藝術問題的總結提煉與自我藝術生命的強烈激發。在此意義上講,韓羽的《我讀齊白石》,其實也是一次獨具韓羽藝術個性的理論創新。
比如,對齊白石多次提及的“似與不似”論,“作畫妙在似與不似之間;太似為媚俗,不似為欺世”。王朝聞在1953年的文章中指出,“這句話是他怎樣塑造形象的主張,也是他那優美形象的確切的註解,是他那豐富的創作經驗的最好的概括”。因為他認為,“如果說中國古典繪畫的優良傳統的特點之一,是服從抒情的要求,不機械地模寫自然而又不脫離自然,重視和善於運用洗煉的筆墨,塑造比自然形態更精粹更單純(不是簡單)更具魅力的形象,那麼,齊白石的作品就是這些特點的具體體現”。在1957年的文章中,他又強調:“可是他不把自然的如實的模仿當成創作的最高境界,原因就在於畫家力圖表現人的精神。熟悉物件和擁有高度藝術修養的老人,敢於提出容易被庸俗觀點所僵化的人誤解的主張:‘作畫妙在似與不似之間。太似為媚俗,不似為欺世。’這種說話,和石濤的‘至人無法,非無法也,無法而法,乃為至法’的說法是相通的。孤立地看齊白石的這一句話,唯心主義者可能強調‘不似’。只要聯絡他的作品,從他自己的實踐來考察,可知他所主張的‘不似’正是為了‘似’。‘不似’其實是在‘似’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決不是不準確的‘似是而非’,而是比一般的模擬更高階的‘似’,也就是形象更有概括性。他的這種‘妙在似與不似之間’的主張,既反對依樣畫葫蘆的攝影主義,也反對脫離實際的形式主義。”在1962年的文章中,王朝聞將“似與不似”擴充套件到了繼承傳統的話題,他說:“齊白石和歷代勤勞、勇敢、智慧的藝術家一樣,懂得‘若無新變,不能代雄’的真理,他不把別人的成就當成自己的成就,沒有使學習和因襲的界限混淆起來。他十分尊敬前人,也十分相信他自己。‘絕後空前釋阿長,一生得力隱清湘。胸中山水奇天下,刪去臨摹手一雙。’這是對前人石濤的頌揚,也是他自己創作信念的流露。他在臨摹中為自己的創造性創造了條件,而不以貌似前人作品的面貌為臨摹的目的。當他已經有了較高的藝術造詣時,儘管他仍然崇拜前人,卻十分重視自己的藝術個性,創造的內容和形式都強調‘變’而不甘於‘似’。他用‘我行我道,下筆要我有我法’來激勵自己,同時他也不願意自己成為盲目崇拜的偶象,成為後人裹足不前的障礙,因而又用‘學我者生,似我者死’來警告崇拜他的後人。”
王朝聞對齊白石“似與不似”的解讀,重點在於客觀物象的似與不似,以及繼承傳統繪畫藝術傳統的“似與不似”;韓羽基於自己的現實生活經驗、文學閱讀感悟以及藝術創作實踐,對“似與不似”則有他自己的發明。《我讀齊白石》的書中約有五篇文章或直接或間接地談到了這個問題。
在《“似與不似”絮語》中,他所提出的,是其有關“似與不似”的總體性的論點,即:“‘作畫,妙在似與不似之間’,就字面看,似是繪畫之法,遠非如此,實是已關聯到作品與欣賞、作者與讀者兩相互動的更深層面,由‘技’而‘道’了。”他進而得出,“‘妙在似與不似之間’的‘間’,也就是讀者想象力馳騁的活動空間”。他又進一步分析了“是”與“似”兩個近音字的不同意味,由張潮之“情必近於痴而始真”的“似痴”,到《藝概》之“似花還似非花”“不離不即”的悟解,結語以絕對的語氣說道:“齊白石的‘作畫,妙在似與不似之間’,就是‘似’,而不是‘是’,這話雖不是他首創,但自古迄今明此理的畫家多矣,而能以天才的多樣的繪畫典範驗證之發揚之者,首推齊白石。”
另有一文《“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有關“似與不似”的見解亦極為獨特。此一篇與上述文章堪稱姊妹篇。他說,齊白石的“似與不似”論,“人人云雲我亦云,數十年,仍無異於終身面牆。”“恰好有他一幅畫稿,試窺蛛絲馬跡。”他引了這幅畫稿的跋語,“畫存其草,真有天然之趣。”正是這個“草”,引發了韓羽“似與不似”的思考,正是這個“天然之趣”,使得韓羽揣摩到了,“‘天然之趣’是何趣,有一點可以肯定,是他所熟悉所喜愛的‘趣’。”接下來的話語,雖是對白石老人的領悟,我看則實為韓羽藝術創作的自況:“或謂,畫畫兒,看畫兒,何得如此囉嗦,答曰,人之與人與物與事,總有好、惡之分,親、疏之別,人的眼睛也就成為本能,總希望從物件中看到自己之所喜好所熟悉所向往的東西,或者說,就是‘發現自己’。觀人觀物如是,藝術欣賞活動尤如是,藝術欣賞者最愜意於從欣賞物件中發現自己所熟悉所喜愛所向往的東西,不如此不足以愉悅。而藝術創造者也竭盡所能將自己所熟悉所喜愛所向往的東西融入藝術作品之中,唯如此方得盡情盡興。這是出之人的本能,飢則必食,渴則必飲,不得不然也。”如是,韓羽探測到,“似與不似”實為中國傳統繪畫藝術的普遍規律,以及這一規律如何發生作用的隱秘。最後他說:“如謂這‘似與不似’的鳥兒是白石老人就磚地上‘畫存其草’,不如說這隻鳥的影兒早就儲存於他胸中了。偶爾相遇,撞出火花,就像《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初見林黛玉,‘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你看,韓羽的博學與幽默悄然而出了。
《鏡內映花 燈邊生影》所發明的,則是“似與不似之間”的“畫理”。這篇文章由白石老人無題無跋、就筆墨論不能算作上品的“母雞馱小雞”畫而引發。“先說‘母雞馱小雞’未必有其事。”“再說‘母雞馱小雞’當必有其理。”再問,“這小雞雛是怎地到了母雞背上的?我思摸八成是白石老人助了一臂之力,是畫筆起的作用。”“比懂鳥語的公冶長更善解鳥意的老頭兒的一顆心,正是這顆心,使整個畫面暖烘烘起來。”再下來,就是韓羽公獨有的妙悟了:“這幅畫把生活中的‘本來如彼’的‘彼’,畫成了‘應該如此’的‘此’,說是‘無中生有’固然不可,說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似也卯榫不合。不妨以他自己說的‘作畫,妙在似與不似之間’對對號。母雞馱小雞,未必有其事,不亦‘不似’;母雞馱小雞,當必有其理,當然是‘似’了。正是這‘似與不似’的間隙裡,才得以作出了這妙文章。”
《再說“蛙聲”》篇談的是白石老人的經典名作《蛙聲十里出山泉》。於此,韓羽發明的獨特處至少有三。一是他認為的美和美的由來,“美,總是躲躲閃閃,‘藏貓兒’。若想和它照面,還需‘緣分’,要看有緣無緣了”。蛙聲何以言美?不只關聯著眼睛和耳朵,也關聯著心態。二是繪畫的“合理的虛構”,蛙聲的由聽入畫可視可看,異體而同化,“蝌蚪起的就是‘藥引子’作用……既不能把它畫得太像,也不能畫得太不像,約略像個蝌蚪樣兒,方恰到好處,這不妨叫作點到為止”。由此,他對“似與不似”的藝術實操概括為:“畫中物象,不等同於生活中的真實事物。生活中的事物,一旦進入畫中就具有了‘假定性’,換個說法,也就是合理的虛構。”三是繪畫的“推敲”功夫,韓羽由其創作的體會思考得就更深了,“點到為止”之“止”,也是有條件而存在的:畫題“蛙聲”的暗示,以及畫面山間溪水的急流,調動起欣賞者的不同感官,互相打通而“視形類聲”;“知止”“止於至善”,如要“點”到“至善”之恰到好處之“處”,“並非率爾揮毫就能信手拈來”,而真是要下如賈島般的“推敲”功夫。
“似與不似”,是一個大問題,卻也並不是韓羽關注的唯一的問題。在這本小書中,基於白石老人的畫作與詩作(日記),韓羽公對其他傳統繪畫的老問題也都有極個性而深刻的思考。比如,筆墨的問題,雅俗之辨的問題,詩與畫的關係問題,畫跋的問題,意中有意味外有味的問題,寫意與寫生的問題,諸如此類普遍的常識性問題,由白石翁的畫作,他都“讀”出了不凡的見解;於白石翁繪畫的理解,於繪畫藝術的實踐,均有不凡的啟發意義。
對齊白石的妙解深讀,可見韓羽有其獨具自我的新的發明和利器。這一個利器,即是他古典文學的修為與修養。這一個發明,我以為是他對齊白石“痴”之性的體味、突出與強調。說起古典文學的修為,在這本小書中真是顯而易見了。在他的文章中,典故、詩詞信手拈來,與畫的解讀天衣無縫,有詩眼的準確,有意境的深遠,文章的節奏舒緩有致,一派生機與活力,可以說,篇篇匠心,篇篇皆為完整的好文章。而對於白石翁“痴”性的著重強調,在這本小書中也有許多的體現;我以為,如此的強調,為拓展齊白石研究的路徑與空間,亦提出了重要的思路。
羅家倫言白石老人的自述是“不掩飾,不玩弄筆調,以誠摯的心情,說質樸的事實”,並言“白石具有中國農村中所曾保持的厚道”。這些都是我極認同的話。韓羽的這本小書,不知何故,卻未曾提及《白石老人自述》這本小書。不過,從韓羽這本小書的多篇文章中,我們真可清晰見到他對白石老人人性幽微之處的探察,對白石老人偉大人格魅力的崇仰,以及,那種莫名的惺惺相惜之情。
談到齊白石跋《穀穗螳螂》“牆角種粟,當作花看”時,韓羽言:“耐人尋味之‘味’,不離文字,不在文字。文人雅士,有愛梅者,有愛蓮者,有愛菊者,有愛蘭者,似未聞有以谷‘當作花看’者,即種穀之農民雖愛谷亦未聞有以‘當作花看’者。”“‘當作花看’,就是審美之極致。”“審美之極致,就是古人說的‘神與物遊’‘物我兩忘’。”這些體恤的話語,是可以從《白石老人自述》中找到印證的。
《誰能忍住不笑》談白石老人畫的“也該歇歇”的禿頂老頭兒,傻得有趣,真得動人。韓羽一再提及“情必始於痴而始真”的道理,白石畫之人情、世情,實出於白石老人之人情與世情。《看圖識“畫”》提及的“牧牛圖”,韓羽認為實是“親情圖”,如此的定評,與《白石老人自述》中對其少年經歷的敘寫,是極為吻合的。不能斷言韓羽公從未讀過《白石老人自述》這本小書,但他有言,“沒有生活,也讀不懂這樣的《牧牛圖》”。《“跋語”的跋語》,韓羽談他對“草間偷活”四字跋的體悟,我相信韓羽“似是詼諧,逗人慾笑。咂摸咀嚼,竟眼中生霧,心中酸楚”的閱讀體驗,決不是文字的虛與委蛇,而是內心的真實疼痛了。更有韓羽多次提及且屢作發揮的談白石翁《小魚都來》的文字:“白石老人畫‘釣魚圖’,大筆一抹,將那‘釣鉤’抹去,換上小魚喜愛的吃物。只這一抹,何止抹去一‘釣鉤’,直是‘一掃群雄’,使所有的‘釣魚圖’都為之相形見絀了。為何這麼大力量,善心佛心也,‘民胞物與’也。”“這幅‘釣魚圖’,雖沒有人,但有一巨大身影從那沒有‘釣鉤’的釣竿顯現出來,那就是畫家的‘自我’,就是釣竿之‘形’與畫家之‘神’的兼備。”
韓羽的這部小書,我在半年多的時間裡,陸陸續續讀了約四遍。又由他的這一部小書,讀了關於齊白石的其他一些書,還透過知網,瀏覽了自王朝聞第一篇文章以來的許多許多篇的文章或論文。我深深地感到,韓羽先生的這部小書的獨特價值,真是太過於貴而重了。他的文字,是一如既往的深入淺出;他的角度,是如詩歌少年般的機敏;他的思考,仍然是如其水墨畫一般的活潑可愛。他時而靜,時而動,時而哀,時而笑,時而歌,時而嘆,時而深沉,時而婉約,真是為我們活潑潑呈現了一個可感多姿、豐富而深情的齊白石的藝術世界。“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也許,這就是他最大的心思吧。
白石翁有一幅以兩隻小雞為主角的《他日相呼》,韓羽先生特別喜歡,私下裡經常談及。每每撫及此書,我總在想,這是多麼的像,隔了時空許多年的兩位同是童心與稚氣滿滿的老先生。那條被銜來拽去的蚯蚓,也許正是傳統繪畫藝術何為好的“好”字。白石老人曾為工筆草蟲冊題“可惜無聲”。我想因了韓羽先生的這部書,白石老人在天之靈是可以得到許多許多的慰藉了。因此,我堅定地以為,《白石老人自述》已是一部讓我們走近白石翁的小書,韓羽公的《我讀齊白石》,將是讓我們走進齊白石的一部極重要的小書。
來源: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