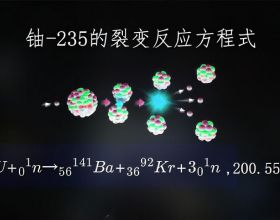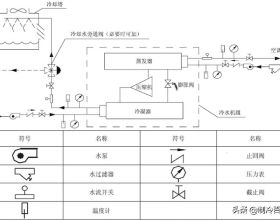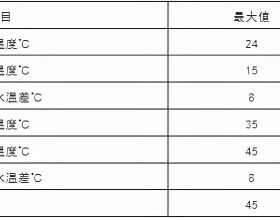非洲象有一種特別的警報聲,彷彿是它們的語言中的“蜜蜂!”它們聽到蜜蜂的嗡嗡聲就會逃跑,邊跑邊搖晃著腦袋。哪怕只是聽到了一段大象奔跑著躲避蜜蜂時的叫聲錄音,它們也會搖晃著腦袋逃跑。搖晃腦袋是它們躲避蜜蜂時特有的行為,這是為了避免在逃跑時讓發怒的蜜蜂鑽進耳朵或鼻子。但在美國動物園裡的大象從未遭遇過東非蜜蜂,它們對蜜蜂的聲音沒有反應。
在非洲,年長的大象會作出反應,幼年個體會觀察模仿長輩們的反應,這是它們學習的一種方式。
猴子的“語言”
1967年,人們意識到青腹綠猴的叫聲有著不同的含義。
如果發現了一隻危險的貓科動物,青腹綠猴發出的叫聲會讓大家都跑到樹上。當一隻猛雕或非洲冠雕飛過的時候,警戒的猴子發出的雙音節鳴叫會讓其他的猴子望向天空,或者鑽進較厚的地面隱蔽物中(而不是爬到樹上)。它們是敏銳的觀鳥者,但他們對黑胸短趾雕和非洲白背禿鷲沒有反應,因為這兩者都不捕食青腹綠猴。如果發現了危險的蛇,青腹綠猴會發出帶顫音的鳴叫聲,其他猴子聽見後會用後腿站起來並掃視地面。
安博塞利(肯亞與坦尚尼亞交界的邊境城市)的青腹綠猴的詞彙中有“豹子”“老鷹”“蛇”“狒狒”“其他肉食哺乳動物”“不熟悉的人”“首領猴”“從屬猴”“監視其他猴子”“發現敵對部落”。在出生6個月到11個月之間,青腹綠猴可能對報警鳴叫聲作出錯誤反應,比如聽到老鷹警報時跳到樹上。直到兩歲時,青腹綠猴還可能對沒有威脅的鳥類發出“老鷹”的警報,對小型貓科動物發出“豹子”的警報。在成長的過程中,才逐漸掌握正確發音,這與人類有些相似。
其他一些猴子也有針對具體威脅的不同報警鳴叫聲。伶猴、大白鼻長尾猴、疣猴等猴類不僅有著包含不同成分的鳴叫聲,還能透過鳴叫聲的順序傳達額外的資訊。(一些小型鳥類也會這麼做,比如金翅蟲森鶯和歐亞鴝。)
坎氏長尾猴會透過改變叫聲的次序表示它是看到了還是僅僅聽到了捕食者,這有點像語法,語序會改變語義。如果危險離得較遠,坎氏長尾猴會以某種類似形容詞修飾成分的鳴叫開始報警,這是一種低頻的“咚咚”聲,其大意是:“我看見遠處有一頭豹子,小心點!”如果沒有這種咚咚聲,意味著情況緊急,“豹子——那邊!”坎氏長尾猴表示豹子的報警鳴叫聲有3種,表示冠雕的有4種。
戴安娜長尾猴會對坎氏長尾猴的報警鳴叫作出反應——在面臨風險時,它們可無法承擔語言的障礙帶來的損失。
長臂猿會將至少7種不同的鳴叫聲組合成歌曲,這些歌曲能擊退進攻的長臂猿、吸引配偶和警告捕食者。
黑猩猩的鳴叫聲有近90種不同組合,某些情境下還會加上敲擊樹幹。一頭熟悉的雌性黑猩猩的“高聲氣促”(pant-hoot)聲可能向整個群體宣佈它的到來,但在它最終接近首領雄性黑猩猩時,它發出的聲音變成了“低聲氣促”(pant-grunt)。它實際上可能在說:“大家好!——現在我要這麼做。”
動物交流時使用的“語法”
小象有兩個非常特別的“詞彙”,用於表達滿足或憤怒。它們在受到愛撫的時候會發出“啊哦哦哦哦”的聲音,不高興時會發出“吧羅歐歐歐”的聲音,比如在被推擠、被象牙戳到或者被踢到的時候,以及被母親拒絕餵奶的時候。有時候,母親發出的隆叫聲能讓一頭遊蕩的小象馬上回到它的身旁。這種叫聲似乎可以被翻譯成“到這兒來”。
大象互相理解對方在說什麼,無論那是具體的資訊,還是僅僅表達情感,這可能是我們所理解的語調,比如“我等不及了!快走吧!”。語義通常取決於語境。因為傾聽者瞭解語境,它們能夠理解資訊。
有時人的語言也如此,用友好或者刺耳的聲音說“嘿!”,你會明白我要傳達的是問候還是警告。
對於大象來說,一頭隆叫的大象聽起來可能就像一個人在喊“嘿!”,傳送者在其中添加了更微妙的意義,並能被接收者所理解。
兩頭大象互相接近時會發出一陣柔和、簡短的問候隆叫。當飼養員呼喚一頭孤兒象的名字時,被叫到名字的那頭也會以問候隆叫進行回應。(飼養員說英語,大象用大象語),這種叫聲的意義近似“你好,很高興又見到你了”,或者也可能是“你對我很重要”。
在人類的語言中,“你對我很重要”(You are important to me)的意義與“你對我很重要嗎?”(Are you important to me?)並不同。語序改變了語義,這就是語法。許多研究通訊的專家認為語法是真正的“語言”的決定性特徵。
海豚研究員路易斯·赫爾曼在夏威夷研究圈養海豚,他發現海豚能夠理解“從約翰那裡拿到戒指遞給蘇珊”和“從蘇珊那裡拿到戒指遞給約翰”之間的區別。
大多數動物不具備的其實是複雜的語法。海豚也許會在野生環境中使用一些它們自己的簡單語法。某些猿類能夠學會使用一些人類的語法,尤其是倭黑猩猩。
這是很有意義的,意味著這些物種有能力使用人類語法的某些部分,並作出正確回應。馴獸員訓練它們的這種能力,使其表達為人類能夠觀察的形式。
如果另一種動物能夠對人類使用語法,卻不對同類或者自己使用語法,這是說不通的。真正的問題在於:人類可能還沒有完全理解這點。
有可能是動物使用語法的方式略有不同。很多動物能不動聲色地收集資訊,以理解對方的意圖,比如分辨“如果我攻擊你,我能贏”和“如果你攻擊我,我就要輸了”之間的區別。
對於複雜的社會性動物而言,社會地位極大程度上取決於年齡和經驗,也許其中也有某種語法用來表示比較,比如“我能勝過她,但他能勝過我”。數百種社互動動都依賴於正確評估這些關係的能力。
想象一下,無論是大象還是猿猴都要對社交和策略的決策進行風險收益評估,它們不僅要三思而後行,還要清楚自己獲勝的可能。它們的心智必須足以在可能的不同場景中轉換角色,判斷結果。在某種意義上,挑選、選擇和分辨的行為是否體現了一種生存的語法?是不是就出於這個原因,它們的心智慧夠理解詞彙順序的改變也就改變了它們之間的關係,就像人類一樣?也許是有關係的。
有人可能會總結說:人能用句子說話,而其他動物用的是短語。“我想去池塘邊散步,我們還要去見見其他的狗”這句話,可以輕鬆被縮減成人的詞彙“散步,池塘,狗”。如果是動物,只要把鼻子衝著門,搖搖尾巴就夠了。不管用哪一種方式,表達的想法基本相同,並引發同樣的預期結果。成千上萬的生物沒有使用一個副詞或動名詞,就表明意圖。
在對待其他動物的詞彙上面,人類偷懶了。我們只說狗會“吠叫”或是“嗚咽”。其實你很容易分辨狗站在門前要求出門時的叫聲,以及當一個陌生人出現在門前時它的叫聲。其實,狗叫的音高、音色和音量都是不同的,很容易進行區分。對其他動物的詞彙,我們幾乎是個“耳盲”。
舉個例子,看看兩頭大象是如何對話的。一頭象開始發出“接觸問候”(contact calls):“我在這裡,你在哪兒?”另一頭象聽見了,作為應答,它發出一陣爆裂般的隆叫,意思是:“我在這。”
接下來,最初發出訊號的大象的姿勢放鬆下來,彷彿在想:“好,你在那兒呢。”它可能會回應,彷彿在確認收到了應答。旁邊的家庭成員可能會插嘴,一唱一和。當大象互相靠近的時候,這樣的問候可能持續幾個小時。
雙方見面了,對話走向高潮,它們的詞彙變成了一系列強烈的、相互重疊的問候隆叫。接下來,對話再次轉向,變成了更柔和的隆叫,結構與前者大不相同。這部分通常持續許多分鐘。
就算大象沒有複雜的語法,它們也有詞彙。它們的交流工具包裡配備了幾十上百種動作、聲音及兩者的組合。
人類目前為什麼沒有更好地理解它們?人類第一次試圖研究其他動物如何交流僅僅是幾十年前,這段時間太短了,研究大象溝通交流的先驅者們仍在工作著。
大象通訊的奇聞逸事
大象能隔著很遠的距離進行交流,沒人知道它們是怎麼做到的。
大象的隆叫中低頻的部分遠遠低於人耳的感知範圍,這些叫聲的音量卻很大(115分貝,與搖滾音樂會現場相當,後者大約在120分貝)。理論上,憑藉這麼大的音量,大象能在6英里之外聽見這樣的聲音。大象腳上有特別的接收器,叫環層小體(paciniancorpuscles),能夠捕捉透過地面傳播的大象的隆叫聲。它們是否還有其他的方式,能夠感知來自更遠處的呼喚?它們是否會接力,就像人類玩擊鼓傳花一樣?
在辛巴威的一傢俬人野生動物庇護所裡,生活著大約80頭大象,它們常常在一處旅行者住宿點附近閒逛。而在離這裡約90英里的萬基國家公園(Hwange National Park),工作人員決定“處理”幾百頭大象,降低公園中大象的密度。方法是用直升機驅趕大象走向埋伏的槍手,然後殺死整個象群。
遠處的屠殺開始後,閒逛的大象突然消失了。它們被發現聚集在庇護所裡遠離萬基公園的一角。相關研究人員說:“大象能在很遠的地方聽到痛苦的呼叫,它們意識到同類正在被殺害。”但這是怎麼做到的?
相似地,在“大象耳語者”勞倫斯·安東尼(Lawrence Anthony)去世後不久,曾被他營救並在他的大型庇護所中生活的20多頭大象分成兩組,在兩天內先後聚集到他家,在那裡徘徊了兩天。它們先前已經一年沒去過那裡了。我們知道大象會哀悼,但是,為人類哀悼?12小時路程以外的這些大象如何得知某個人的心臟停止了跳動?誰也不知道。
被大衛·謝爾德里克野生動植物基金會(David Sheldrick Wildlife Trust)救助的孤兒象,會在內羅畢國家公園(Nairobi National Park)的保育所裡接受人工哺乳,然後送到察沃國家公園(Tsavo National Park),與其他先前接受過救助、如今處於野生狀態的大象生活在一起。它們將在一個更加正常的、年齡分佈更廣的大象社群中開始新的生活。
保育所裡的飼養員朱利葉斯·施瓦亞( Julius Shivegha)說:“剛剛到達察沃的時候,它們會過來問我們,‘我在哪兒?為什麼要把我們帶到這裡來?’它們用的不是我們的語言,但我們走到哪裡,它們就跟到哪裡。後來,用自己的語言和其他小象交流之後,它們就明白了一切。”
如果年齡較大的象確實記得孤兒院的經歷,以及自己是怎麼到了察沃,它們明白新來的小象遭遇了什麼,這意味著它們記住了自己的經歷,並且知道自己能記住這件事情。那些懷疑論者在看到孤兒象在察沃會面的場面之後,往往會相信他們目睹了一些無法解釋的東西。而為這些孤兒象工作的人對此沒有任何疑問。
達芙妮·謝爾德里克有著幾十年和大象相處的經驗,她堅稱當一群新的孤兒象被卡車載著送往這裡時,察沃的大象能夠察覺。她說,成年象會迎接新來的小孤兒象。她將其稱為“心電感應”。
人類似乎普遍相信一種假設:每個物種都只有一套叫聲,不像人類語言那樣擁有不同的方言、不同的語言。這裡似乎又存在一個假設,即它們的語音系統是天生的,不需要透過學習來掌握。但是,從小被帶離野生環境的個體,比如動物園裡的猿類、馬戲團裡的大象和虎鯨,可能始終無法掌握如何用它們的方式自然地依靠聲音、動作、語境和其他細微的差異進行交流。
許多鳥類有地域性的方言。虎鯨也有一些詞彙在某些群體中被大量使用,卻不為其他群體所掌握。類似這樣的區別在我們周圍無處不在,人類還在為這樣的行為進行分類,並描述動物的叫聲。儘管如此,翻譯和理解動物的交流也許就像試圖撓一處夠不著的癢癢。目前為止,動物們所說的、所想的都比我們所理解的更為複雜。
文源:《無言的呼喚:動物的感知、思考和表達》,略有刪改
作者:[美]卡爾.沙芬納 (Carl Safina )
部分圖片來源於網路
版權歸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