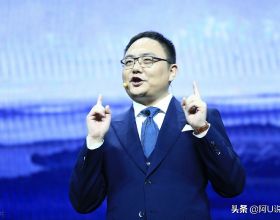一部經典講的就是一個道理。在王弼看來, 《老子》(又名《道德經》)講的道理可以用“崇本息末”四個字來概括。本是無,無形無名;末是有,有形有名。作為《老子》最偉大的解釋者,王弼確實把握到了老子思想的精髓:在“有無之間”思考。
老子是一個具有高度想象力和創造性的哲人,當所有人都在“有”的世界中展開其思考的時候,一句“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把中國思想帶進了嶄新的有和無之間的世界。這個世界一直在那裡,但只有當有人看見了它,說出來之後,更多的人才注意到它,併成為自己的世界。
所有人都在說有,老子說了無,世界呈現新貌
老子在事物中發現了有和無,並特別強調此前被思想家們忽略的無的作用。沒有虛空,車不成其為車,器和室也不成其為器和室。從這個發現出發,世界呈現出不同的樣貌。
首先,存在於事物和世界中的對待關係被揭示出來,並具有永恆而普遍的意義。 “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恆也。”對待無處不在,且互相依賴、互相生成。自然世界如此,人間世也是如此。以禍福為例,“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無論我們是否願意,是否意識到,對待的他者就潛伏在自身之中。在這種理解之下,一就不僅是一,還是二。二也不僅是二,還是作為一體的二。“一生二,二生三”,其意義正在於此。生成萬物的道也不例外,大方無隅,大象無形,它是有和無的對待,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對待。
其次,事物的對待促成了變化,從一物成為另一物。禍變為福,福化作禍。正復為奇,善復為妖。老子稱之為“反者道之動”,事物會向相反的方向變動,這是道的內涵。但變化有其條件,發展到“盈之”的極端處,變化會更容易發生。如“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等。
第三,瞭解了對待和變化的法則,就可以控制變化的發生。 “反者道之動”的運用,便是“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所以老子主張守柔、處下、不爭、光而不耀等,倡導節制的精神。以“有無相生”為例,這個命題既包含了有生無,也包含了無生有。如果要保全有,就必須回到無,從中很容易得出王弼所說“將欲全有,必反於無”的認識。老子看重無、貴無,用意是保全已經擁有的一切。貴無並不是追求虛無,恰恰相反,無是有的世界的根基,萬物存在的根基。
這個認識,集中地表現為“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天下萬物有形有名,但有形有名卻是出自無形無名,後者比前者更根本。用第一章的話來說,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萬物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現代人看這句話已經習以為常,在春秋戰國時代,卻是石破天驚。拿名來說,一般認為是很神聖的東西,物憑藉著名才被定位,才變得清楚明白起來。孔子的正名說自不必言,墨家、法家等也都完全生活在名的世界。無論是禮樂秩序,還是法的秩序,事物和名已經完全捆綁在一起。在這個時刻,老子突然提出無名來,名和事物之間的縫隙就出現了,等於給事物鬆了綁,獲得了從名中解放出來的可能。
老子肯定無名的同時,給有名保留了空間
一個觀念就是投射到世界之中的一束光。有了無名的觀念,人們就會思考,名和真正的事物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如果事物從根本上是無名的,那麼名能否完全呈現真正的事物?名的意義到底為何,是揭示事物的本質,還是透過給事物命名的方式,將其納入到某種人為的評價或秩序中去?很顯然,老子意識到了名和事物之間的距離,意識到了名對於事物的束縛和控制。作為萬物本原的道是“恆無名”的,如王弼所說: “至真之極,不可得名,無名則是其名也。”道如此,事物其實也是如此。但物畢竟不是道,人間世雖然保留著和道相連線的臍帶,卻也努力地彰顯自己的獨立性。
老子的深刻之處在於,在究竟意義上肯定無名的同時,也給有名保留了空間。在“道恆無名”之後, “始制有名”似乎也有其不得不然的理由。於是,讀者很容易看到存在於其中的無名和有名之間的張力。在這種張力之下,名的存在部分地被肯定了下來,卻也僅限於此。 “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它更像是不得已的工具,如果把工具變成了目的, “任名以號物”,那就是“爭錐刀之末”了。
世人對A Thing和That Thing的無從選擇
但這個世界似乎更在乎名,更在乎命名。 《鳥人》(Birdman)2015年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等四項大獎。主人公年輕時靠扮演超級英雄“鳥人”而風靡一時,以至於他想撕掉“鳥人”標籤,去追求真正自我時發現揮之不去,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電影中主人公憤怒於懶惰的批評家們不在意真正的藝術,他們只是用標籤捧人或踩人。但反諷的是,想要擺脫標籤的主人公也被困在標籤之中, “不可解於心”。這部電影的成功之處,就在於揭示了人的永恆困境:我們拼命想擺脫的,其實是永遠無法擺脫的東西。就像希臘神話中的伊卡洛斯,想要靠飛翔擺脫大地的束縛,卻毀滅於溫暖的陽光。
畫龍點睛的是電影中的一個句子:A thing is a thing;not what is said of that thing。我一直認為這是對“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最傳神的翻譯。事物本身是無名的“a thing”,在現實世界中卻成為貼上標籤的“that thing”。從悲觀的方面說,生命就是“a thing”和“that thing”之間的掙扎。自樂觀的方面看,在一個有名的世界中自覺到無名,意識到“a thing”和“that thing”、有無之間的分別,畢竟讓生命和世界擁有了更大的空間。我想,《老子》直到今天仍然被很多人喜愛,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發現了這個道理吧。(作者王博系北京大學副校長、哲學系教授)
來源: 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