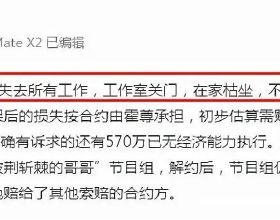小時候,我記得那座古鎮的經濟很不發達,交通也相當落後。出遠門時,大人們總是乘坐沱江上的“烏篷白帆船”,到達縣城後再上成都、或下五鳳溪去坐火車。古鎮上的人家,每每煮飯時都燒柴草,那裊裊炊煙升騰時,古鎮上總是雲裡霧裡、有神仙界外的感覺。柴草多是山民們從炮臺山麓下挑來賣,或有云頂山下的山民,肩挑柴草,扁擔閃閃悠悠地穿過同興壩子,來到沱江邊,再過擺渡船去鎮上豬市壩賣。古鎮居民家中需要柴草,就去豬市壩柴草市場,挨個兒挑揀柴草的成色,看起了,就慢悠悠地和賣柴的山民侃價,大塊木柴最好的也就角把錢1斤,山草2——3分錢1斤,說好價錢後,山民就把千擔(兩頭尖的青岡木)或扁擔一穿,擔起柴草去了“市管會”的公秤,每次公秤收取2分錢,過完秤,山民就挑起柴草送到買主家。那時候,古鎮正在發展,燃料供應可是個大問題。沱江碼頭上的“烏蓬船”多,就有烏篷船桅杆上扯掛一張寬大的白帆助力,艄翁掌舵,或有數十名船工拉縴,一根長長的竹篾纖繩連線到船頭的木樁上,長聲吆吆地吼起“杭育……杭育……”的川江號子,從五鳳溪火車站朔江運來了煤炭。鎮上就有了煤炭公司。當燒蜂窩煤的藝術傳到古鎮,烏篷船又運來了無煙煤,鎮上也就有了蜂窩煤廠。鎮上按戶口發放蜂窩煤票證,家裡人多的就供應100個,人少就供應60個,定價5分錢1個,都是自家挑著籮筐去煤廠買。自有了煤炭和蜂窩煤,古鎮燒柴草的歷史就從此結束了。
燒煤雖好,但煤煙對環境衛生有著嚴重的汙染。鎮上燒煤一直持續到了90年代末,國家科技已經相當發達了,就探測和開發了大量的天然氣深井,並從瀘州鋪設了大型管道,穿過古鎮鋪向成都。從此,天然氣就取代了煤炭。在2000後出生的年輕人們,對蜂窩煤這種物質,他們根本就不知道是個啥東西。我深深地記得,在上世紀的60年代,這座古鎮上的房屋,大多是青磚青瓦的磚木結構。古鎮上有個磚瓦廠,位置就在真武山腳下的小河溝邊上。因鎮上房屋建設和維修需要磚瓦,磚瓦廠就應時而生,工人們就在小河溝邊的土地上採挖黃泥,然後人工赤腳反覆澆水踩踏,直到黃泥巴的柔和程度,達到可製作泥瓦的標準。踩踏好柔和的黃泥,磚瓦匠人用鋼絲彎弓切割泥塊,大塊大塊地堆碼成高高的黃泥垜,然後上面用溼草簾子覆蓋保持溼度,再搭上個草篷子防雨。直到後來有了塑膠薄膜保溼,才淘汰了草簾子。黃泥堆碼成垜後,瓦匠師傅就可以開始做泥瓦了。他們先平整出一個壩子,運來河沙鋪在上面,瓦匠在泥垜邊的草棚子裡,架好一個圓木凳似的工具,讓它旋轉起來……瓦桶是木片製作的工具,可以撐開成圓錐形,外面圍上薄薄的紗布,放在旋轉的木櫈上,做瓦時,瓦匠用木弓從泥垜上切下一片厚薄合適的瓦泥,輕輕圍在瓦桶上,然後旋轉起圓木凳,外邊用一個有把的圓形鐵皮工具,沾水輕壓在瓦桶的泥片上,利用旋轉原理,泥瓦就光滑地完成了,用個釘子木棍按高低去掉多餘的泥片,然後輕提瓦桶放在平整的沙地上,輕輕提著紗布一鬆,就取出了瓦桶……一排排泥瓦圓筒擺滿了河沙地平壩,在陽光和風的晾曬中,待到風乾後,只要輕輕從外一拍,黃泥瓦桶就裂成了4片,收攏碼放成一道牆,蓋上草簾子防雨,等充分乾透後就可以進窯燒製成瓦了。泥磚製作的程式就簡單多了,只需製作一個四匹磚的木框架,放在平壩沙地上,用木弓切一坨磚泥,重重摔入木框,然後用木弓順木框表面一刮,去掉多餘的磚泥,開啟木框,沙地上就留下了方正的泥磚,待黃泥磚塊晾乾後,再堆碼成一道道磚坯牆,蓋上茅草簾子,待乾透後就可以運往磚窯,等燒窯匠人裝窯燒製成品磚瓦了。磚瓦廠修建的磚瓦窯,都是選在小河的山坡處,先挖出一個半圓坑,周圍用紅磚塊碼砌成桶狀圓形的磚瓦窯,周邊壘上厚厚的泥土再夯填實在,頂上搭個茅草窯蓬子遮雨。磚窯大約有兩層樓高,裡面底部做成平臺,中間預留一排燒火的窯坑砌上火磚,架上爐條,爐門呈圓拱形狀有兩米多高。
燒窯前,他們用人工挑運來乾透了磚坯和瓦坯,窯匠師傅會按順序先碼磚坯(承重好)在下,然後間隔碼好磚瓦坯,碼磚瓦坯的手藝都是很有講究的,每匹磚瓦之間必須留出空隙,能保證燒窯時的火焰穿透每匹磚瓦坯體。裝好窯後點火,每次燒窯的時間,大約需要大火猛燒整整三天三夜,當窯匠師傅看到磚瓦窯裡的火候達到通紅透亮時,就說明這窯磚瓦已經燒製成熟了。這時候,窯匠師傅看到一窯磚瓦已經燒製成熟,就會停火然後指揮封窯。若這窯磚瓦需要青磚青瓦,那窯匠師傅就要先封窯頂閉火,並立即把窯頂用泥土厚厚堆蓋並填實,泥土堆成秧田狀不能滲漏,並馬上挑水灌滿窯田,每天不斷把窯田加滿水,讓磚瓦窯裡慢慢地自然冷卻;窯門也要馬上堆土填實封閉。這時,磚瓦窯中的柴草或煤煙子就在裡面旋轉,這樣封閉好的磚瓦窯,等出爐時看到的磚瓦,就成了需要的青磚青瓦了。磚瓦窯封閉後,至少需要過了三天,才可以挖開窯頂的泥土,待飄散了窯裡的熱氣慢慢冷卻後,即可開窯取磚瓦了。磚瓦窯匠的手藝,主要還在於看火候,驗證窯匠師傅的手藝,就是取出燒好的瓦片,把瓦片拿在手上,用手指輕彈瓦片,若瓦片發出“噹噹……”脆響的鋼音,就說明這窯磚瓦非常好,無疑是最最上乘的好磚瓦了。小時候,因為我家裡姊妹多,家裡煮飯炒菜的柴禾,都是哥哥姐姐從外面山坡上撿拾回來,家裡很少抽得出錢去市場上買。後來古鎮上有了煤炭,我們就會到街上飯館的爐灶前,撿拾煤渣回家煮飯用。那時,鎮上磚瓦廠有好幾座磚瓦窯輪流燒窯,燒窯時,我為了撿拾到更多燒窯時留下的煤渣(二炭),晚上就夥同鄰居家的“左左娃”,去磚瓦廠燒窯處撿煤渣;磚瓦廠有個胖子窯匠師傅,他叫陳凱,家就住在古鎮財神廟的石梯梯邊上,離我們家不太遠。我們比較熟悉胖子陳凱,他大約有40多歲的年紀,為人厚道,街坊鄰居只要有求於他,他大多都會盡力幫忙。陳凱大叔是個手藝很好的窯匠師傅,古鎮磚瓦廠裡燒窯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出自於他的手藝。陳凱大叔一年四季都在磚瓦廠裡燒窯。每當晚上獨自燒窯時,孤獨的一個人就有點寂寞;當我和左左娃去他燒窯的地方撿煤渣時,他就非常地高興。有我們通宵地陪著他,他就在磚瓦窯的爐門前,放一把三人座的長竹椅子,讓我們坐在竹椅子上面對磚瓦窯烤火,秋冬的晚上很冷,熊熊的爐火溫度,把我們幼稚的臉頰映照得通紅……整整一個通宵的晚上,時間是太漫長了,陳凱大叔不時就要站起來,用燒窯的鋼條去通窯堂裡結成塊的煤,再用火鉤子在爐條下勾一勾爐灰(從裡面漏下的爐灰中,就有我們所需要撿拾的二炭),然後添上好幾鐵銑煤,當熊熊燃燒的爐火發出吼聲時,陳凱大叔就會一撮箕一撮箕地,把爐膛下堆滿的煤灰弄到外面壩子裡。
陳凱大叔沒啥文化,空閒下來,他就會一邊烤火,一邊同我們擺些古鎮上古往今來亂七八糟的龍門陣,他那些龍門陣自然上不了檔次,甚至於那些龍門陣,還帶有讓人臉紅的黃色,但我們需要撿拾煤渣,自然還是要裝著很高興的樣子,認真地聽他繪聲繪色地擺龍門陣。當我們熬到天快亮時,陳凱大叔就會讓我們去撿拾已經冷卻了的煤渣,然後每人背上好大一背篼煤渣,讓我們注意安全早些回家去。後來長大了,我下鄉插隊當知青,在生產隊裡,我也看到過隊上請來泥瓦匠,在村子裡製作泥坯磚瓦。做泥坯磚瓦的過程,大體上和磚瓦廠製作磚瓦的工藝程式差不多;只是生產隊上在燒窯時,都是用從炮臺山上買回來的柴草燒窯,每到點火燒窯時,窯匠師傅需要幫手,隊上就會派人幫忙,輪流把大量的柴草不斷地塞進爐膛,這樣,用柴草燒製一窯磚瓦,就會用掉上萬斤的柴草或更多……當然,那時候的磚瓦廠燒窯,和現在機制磚廠的長窯燒磚工藝有所不同。古窯是圓筒型狀態,現在的機制長窯,是將磚坯放在平板車上,從窯這頭推進去,當平板車從窯那頭拉出來時,泥磚坯已經變成了燒製好的紅磚。歲月如梭,當我們在時間的長河一晃,幾十載的光陰就悄悄地遠去了。雖然,如今我輩早已兩鬢如雪,但我對那些久遠發生的故事,卻依然記憶猶新。古鎮的磚瓦廠早已成為了古老記憶,當過窯匠師傅的陳凱大叔也早已作古。但祖輩上傳下來的古老磚瓦窯手藝,至今回憶起來,我還是覺得蠻有意思……2021.7.19.
*作者簡介: 張宏文,男,籍貫金堂,生於50年代。下過鄉,當過兵,退伍進成鋼當工人,84年參加青白江文講所學習,寫作至今。現在退休,住青白江,青白江清白詩歌沙龍成員,青白江作協會員,四川散文學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