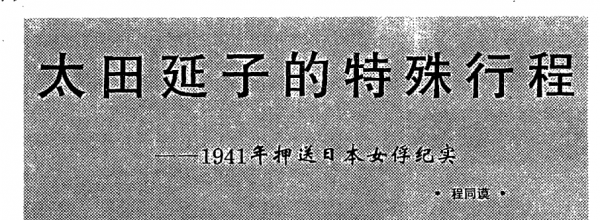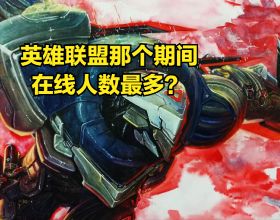1941年的3月14日,隴海鐵路碾莊車站的日軍據點被突如其來的槍聲打破了寧靜。
幾名新四軍戰士如同神兵天降一般出現在了車站內,守在站臺內的數名日軍被打了一個措手不及。
在打掃戰場時,一名戰士在月臺東邊的貨運房內發現了一對來自日本青年男女。
女子年紀十八、九歲,大眼睛,高鼻樑,留著一頭精緻的短髮,身著連衣裙,一看便不是普通人家。
面對突然出現的持槍新四軍,女子嚇得不輕,眼裡滿是驚恐,一手顫抖地打著手勢,一手又從兜內掏出了一份證件,似乎要表達些什麼……
一、意外俘虜
1941年抗戰正處於一個戰略相持的艱苦階段。
年初,新四軍第三師(黃克誠為司令員)接到任務,拔掉隴海鐵路碾莊車站的日軍據點。
任務交給了新四軍第三師的三大隊,三大在派幾名戰士化裝商販刺探敵情後,發現該據點內的日軍僅僅有七人,並且配有長短槍六支,榴彈發射器一門,他們夜間巡邏,白天睡覺,另外車站周圍有一個偽軍小分隊。
刺探明白後,三大隊已經打定了主意,派遣了十一名便衣新四軍戰士,由情報參謀徐蔭堂帶隊,混入客群中,潛入碾莊車站。
不久以後,按照情報,一輛自八義集站的列車如約駛來,七名鬼子出現在月臺上接車。
在車輛駛出站臺後,這幾名鬼子又紛紛回屋去睡覺了,睡前還將槍放置於槍架上才安穩地躺上床。
密切關注鬼子情況的幾名新四軍戰士互相打了打眼色,便腳步迅捷地衝進了鬼子屋內,槍聲過後,五名鬼子紛紛倒地。
此外,一名鬼子與門口負責警衛的新四軍戰士打作一團,隨後也被處理掉,唯一的漏網之魚是一名在廁所方便的鬼子,聽到槍聲大作,便迅速翻牆逃跑了。
此戰我軍無一人傷亡,且繳獲了日軍的一門榴彈炮及一部分價值不菲的槍支彈藥,可謂是收穫頗豐。
然而更令人意外的是,清理戰場時,新四軍戰士們在月臺東邊的貨運房內竟發現了一對日本青年男女,兩人的身份皆不一般。
原來這對日本青年是新婚不久的夫婦,出身皆不凡,男的叫做山中青一,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學生,他的父親是隴海鐵路徐海段的軍事段長。
而這個女子太田延子來歷更是不一般,她的舅父是駐徐州日軍的師團長,二人此次來華是為了探親順便完婚,他們前幾日剛在東北滿洲看望了當鐵路段長的父親後,此次又來徐州看望當日軍隊長的表哥。
沒想到剛來的頭一天,當軍隊長的表哥便在此次襲擊中戰死,夫婦二人也都成為了俘虜。
考慮到這二人的身份不一般,經過協商後,組織上決定將兩名日俘送到了邳州縣古邳鎮的五工頭村,五工頭村是抗日根據地中心,俘虜的安全有所保障。
太田延子歲數小,哪見過這麼大的陣仗,見到穿軍裝的新四軍戰士們便滿是驚恐,夫婦二人被押送到五工頭村小學後,更是水米不進,抱頭痛哭。
二、安全轉移
太田延子和山中青一嚴格來說都算得上是日本“官二代”,身份尊貴,兩人被抓,日軍自然很快做出相應行動。
駐徐州的日軍首先請來了當地的黑幫頭子陳耀東來根據地與新四軍的領導接洽,意圖將兩名俘虜贖回。
贖回俘虜自然不是不可以,日軍自然應當付出相應的條件,我方提出:三十挺輕機槍、十挺重機槍、一百萬發子彈、一百萬元軍票。
日軍很快便有了答覆:子彈與軍票都可以如數給,但是卻拒絕給付這麼多的機槍。
雙方未達成一致,因而談判也就此終止。
但是日軍一向不會輕易善罷甘休,其另一手準備便是組織掃蕩,逼迫我軍將俘虜放回。
3月21日,日軍方面直接組織了一萬多名偽軍,分六路朝著我軍根據地襲來,其在周遭鄉鎮進行挨家挨戶地搜尋,意圖將俘虜救回,這一掃蕩便是十一天的時間。
期間,我軍為安全起見,將兩名日本青年分開押藏,以減輕追捕壓力。
可不料,日本青年山中青一逃亡之心不死,為引起日軍注意,在日軍正窮追之際使用日語大喊大叫,甚至一度奪過新四軍戰士的槍支,威脅到我軍安全,無奈之下,我軍戰士只得將其擊斃,日軍無功而返。
不久後,組織上又下令將女俘虜太田延子轉移送達至師部,任務由新四軍四師九旅二十六團三營八連負責。
但是,五工頭村距離師部的駐地直線距離就有二百多公里,其間還要越過多道封鎖線,穿過數個敵戰區,行動中的艱險可想而知。
押送臨行前,組織上還一再強調日本女戰俘在押送期間要堅決執行上級指示,發揚人道主義,切實遵照優待俘虜的政策給予照顧。
由於行動艱苦,路途遙遠,加之押送期間下起大雨,行動極為不便,八連的戰士們找來了一匹小毛驢來馱著太田延子行進,而戰士們皆一律步行,他們白天潛伏,夜晚行動,潛伏加繞路,一連花了四天四夜方才到達師部。
在押送期間,太田延子對於新四軍的看法也大為改觀。
起初,太田延子在押送過程中心存疑慮,臉色慘白,雙肩不停顫抖,新四軍將士便上前,打著手勢,指著心口,表示請她放心,她這才稍稍平靜了下來。
由於押送過程晝伏夜出,安全起見,白日宿營之時,八連將太田延子安置在連部跟前,並且專門挑選戰士站崗放哨,尤為強調任何人不得擅入太田延子的房間,給足了這個日本女子安全感。
漸漸地,太田延子也感受到我軍並非野蠻之師,臉色逐漸活泛了,有時給其吃食的時候,她還能夠善意地鞠躬表示感謝。
三、轉變與分別
太田延子原本便是一個活潑、開朗、善於接受新事物且富有正義感的日本姑娘,但由於在日本國內教育的原因,此前一度未曾對這場侵略戰爭產生正確的認識。
當來到師部後方根據地以後,太田延子很快便適應了環境,並且對我軍產生了全新的認識。
她加入了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淮北支部,多次冒險跟隨著反戰同盟的前輩後藤勇到達前線據點,用日語向據點內的日軍喊話策反。
太田延子富有家鄉味道的喊話果然瓦解了日軍軍心,1942年,聽到太田延子的喊話亦或許是對這場戰爭徹底地失望,駐紮於蘇北皖北地區的幾名日本軍人選擇了放下了手中的武器,對我軍投誠。
其中有一位叫作矢口莊司的日本軍曹表示:太田延子的“箭”射中了我的心。
投誠後的矢口莊司很快便成為了與太田延子志同道合的朋友,矢口莊司是日本學生出身,投誠之後,他很快便成為了反戰同盟的骨幹,印發一系列的日文宣傳品,積極地對日本侵略作者展開了政治攻勢,取得了很不錯的效果。
矢口莊司和太田延子二人共事時日漸久,情愫暗生,很快便雙雙墜入情網。
1942年的春天,二人在第四師敵工部部長王子光與反戰同盟的候藤勇的撮合下舉行了簡樸但又熱鬧的婚禮,得到了一眾新四軍戰士的祝福。
二人婚後的小日子很是幸福,還生下了一個男孩。
1944年,由於日軍的節節敗退,抗日戰場的形勢發生了重大改變,為了促使日本天皇能夠早日投降,在延安的日共中央書記野板參三下令:所有分散在國外的反戰同盟成員返回日本,以加強日本國內的反戰力量。
野板參三還特意強調要秘密回國,不可攜帶家眷、孩子。
歸國反戰意味著勝利的接近,對於太田延子來說,這亦意味著分別。
太田延子與矢口莊司的孩子才剛剛四個月,乳名叫做“嘛嘎達”。
這天夜裡,兩個婦人來到了太田延子的住處,他們是孩子的收養者。
太田延子早已經在心中掙扎了無數次,儘管已經下定決心服從組織的安排,但是當將孩子轉至他人手中的時候,她心中的感情仍然像洪水一般止不住地翻湧著。
“噗通”一聲,太田延子已然跪地,她的眼中滿含著淚水,帶著哭腔道:“拜託,拜託,您二位了!”
在孩子被接走以後,太田延子忍受不了內心的煎熬,一個人又悄悄地步行了四十多里路,找到了領養孩子的人家,最後一次看望孩子。
太田延子最後給“嘛嘎達”餵了一次奶,並且留下了幾件衣服和兩袋子米粉,接著便狠下心,走了,這一走便不知道是何年何月。
四、養育與尋親
日本男嬰的養母叫做劉鳳英,是個勤勞樸實善良的莊稼人。
傳達領養“嘛嘎達”的訊息的人是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叫做劉一孚,同樣是做革命工作的。
“鳳英,你是女救會的幹部,是黨的人,今天黨組織讓我交給你一項特殊的任務,收養一個日本人留下的孩子,改名劉太山,這是黨的秘密,任何人都不許說。”劉一孚這樣對劉鳳英說道。
這位樸實的農村婦女聽完後,忙點點頭,接著便跟著自己的婆母火速趕到了太田延子的住處,將剛滿四個月的“嘛嘎達”抱養了回來。
儘管並無血緣關係,但劉鳳英完全將“嘛嘎達”視如己出,她為孩子餵飯、縫衣、做鞋、套被,為了給瘦弱的“嘛嘎達”補充營養,她向人討奶水,做肉糊糊,自己倒是整日吞糠咽菜。
不久後,劉鳳英自己也生了一個女孩兒,但是對於“嘛嘎達”的愛卻是一點兒也沒有少。
嘛嘎達體弱多病,劉鳳英便拖著沉重的小腳到十多里外去請郎中,為了籌錢給嘛嘎達治病,她甚至將自己的結婚戒指都賣掉了……
嘛嘎達所受到的母愛卻是一點兒也沒有少。
時間過得很快,嘛嘎達的名字改成了劉太山,他也到了能夠上學的年紀。
但是村子裡的風言風語倒是讓他受盡了白眼,同學們常常把他叫做“鬼子”,還有的學生甚至動手打他,這嚇得他隔三岔五地逃離學校。
到了小學四年級的時候,劉太山卻是再也不肯上學了,劉鳳英責怪他:
“山兒,媽為你吃苦再多都不怕,但是你也不能不聽話,你不上學,我對不起你,也對不起你爸爸。”
小太山滿臉委屈,突然流著淚哭訴道:
“媽媽,你實話跟我說,你是不是我的親媽媽?”
“是……是,怎能不是呢?”劉鳳英一把摟過了兒子,心裡湧過陣陣酸楚。
建國後不久,劉鳳英拉扯著兩個孩子,儘管生活艱苦,她始終未曾放棄過將兒女拉扯成人。
她要過飯,逃過荒,挖過野菜,始終不捨得讓兩個孩子忍飢挨凍,就這樣,硬是將一雙兒女養大成家。
1975年,劉鳳英連著幾天都昏睡不醒,她已經老了,身體一天不如一天。
劉太山夫婦日夜守護在母親的床前,照顧著昏睡的母親。
過了好一段時間,昏睡良久的劉鳳英緩緩地睜開了眼,她微微動了動嘴唇,卻發不出聲來,她的手指微微顫顫指向了灶臺,又指了指劉太山。
劉太山朝劉鳳英手指的方向上看去,兩個雞蛋整整齊齊地擺在灶臺上,那是母親最後留給他的……
劉鳳英至死都保護著劉太山並非她親生孩子的秘密。
時間來到了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中日間的關係恢復了正常。
劉太山的養父此時恢復了工作,擔任揚州軍分割槽的副政委,他把養子接到了揚州,為其介紹了工作。
1973年的春天,劉一孚決定將劉太山的身世告訴他。
田中角榮
對於自己的身世,儘管從幼時便早已有所猜測,但父親的話語仍然讓其始料未及,劉太山緊緊地抱住了劉一孚哭著說道:
“我是中國人的兒子,我不會離開中國,即使將來我能找到親生父母,我也要喊你爸爸……”
劉一孚對於劉太山心裡是極為虧欠的,他認為自己有愧於組織的託付,他後悔沒有將劉太山帶著自己的身邊,使得養子在幼時受了不少的委屈,只接受到小學的教育,他說:“將來如果能夠見到太田延子,我要向她檢討。”
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劉一孚走遍了許許多多能夠聯絡到日本方面的單位,但由於太田延子是秘密回國,因而始終無法得到一絲的訊息,他終究是沒有機會見到太田延子了。
1988年10月,劉一孚因病離世,他死前表示,希望能夠由組織出面,幫助養子劉太山尋找在日本方面的親屬。
儘管中國方面多方打聽劉太山的親生父母的下落,終究還是如同大海撈針,有曾經的反戰同盟成員林博二男來信稱,在大阪曾經見過大田延子的身影,中國方面又前往大阪尋找,卻依然一無所獲。
當年的反戰同盟成員候藤勇回到大阪後曾有信件來到中國,因而可以推斷劉太山的親生父母也一定回到了故土,但是為何了無音訊,卻是始終說不清楚。
歲月禁不住漫長的等待,時至今日,仍然未曾有關於太田延子的訊息,其是否仍然在世亦尚未可知,只願世界和平,不要再讓這樣骨肉分離的慘劇再現人世間。
參考文獻:
《太田延子的特殊行程》《烽火歲月》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