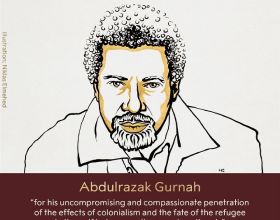1921年8月,郭沫若的詩集《女神》問世,引發了詩壇革命性的震撼。以《鳳凰涅槃》《天狗》等為代表,其中前所未有的激盪情緒,傳達出了“五四”時期除舊革新的精神。
熟悉西方詩歌的讀者,很容易在其中發現美國詩人惠特曼對郭沫若的重要影響。
但是,細心的讀者閱讀此詩集時,一定會在另外數首寧靜、平和的精美小詩中感受到另一種韻致——《新月與白雲》《鷺鷥》《春愁》《鳴蟬》《晚步》……這些詩,在詩集中排列其後。有的讀者,甚至評論家,都以為那些奔放、粗豪的詩是作者激情青春的初期嘗試,而這些寧靜、平和的小詩,想來該是詩人激情消退,技巧成熟後漸漸沖淡的所獲。這考慮雖然有相當的道理,可事實卻並非如此。
1914年9月,郭沫若以半年的刻苦攻讀,考取進入了日本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當時他與一位本科三年級的親戚同住。一天,那位學生從學校帶回幾頁油印的英文課外讀物,郭沫若接過一看,是印度詩人泰戈爾《新月集》中的幾首短詩:《嬰兒的路》《睡眠的偷兒》《雲與波》《岸上》……一讀之下,郭沫若極感驚異。因為這是他先前從未見過的:“第一是詩的容易懂;第二是詩的散文式;第三是詩的清新雋永。”“那是沒有韻腳的,而多是兩節,或三節對仗的詩,那清新和平易徑直使我吃驚,使我一躍便年輕了二十年!”
由此,郭沫若便與泰戈爾的詩結下了難解之緣,他開始四處尋找泰戈爾的詩來讀。當時,泰戈爾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不久,他的詩在日本十分熱銷,作品集在東京還頗不容易買到。郭沫若讀到《新月集》的全本,已是一年後升入岡山高等學校讀本科時的事了:“我得到他的《新月集》,看見那種淡雅的裝訂和幾頁靜默的插圖,我心中的快樂真好像小孩子得著一本畫報一樣。”
1916年的秋天,郭沫若在岡山圖書館又突然尋出了泰戈爾的《吉檀迦利》《園丁集》《愛人的贈品》等詩集。一讀之下,用他自己的話說:“我真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一樣。”閱讀時,為怕人打擾,郭沫若找到一間很幽暗的閱覽室,坐在牆角,面壁捧書默誦。在這樣特別的情境裡,郭沫若甚至因激動而流下感謝的淚水。他長時間沉浸在這樣恬靜的氛圍中,從中午兩三點鐘有時要綿延到燈光燃起之時。這樣的閱讀和感受,使郭沫若在思想和藝術上受到了泰戈爾的深徹影響。
這一段時間,郭沫若正與日本女子安娜(本名佐藤富子)戀愛。泰戈爾的影響和愛情的衝撞,使得郭沫若創作慾望被強烈激發出來。他陸續寫出了《新月與白雲》《死的誘惑》《別離》《維納斯》多首,以及《牧羊哀話》中的幾首牧羊歌,這些詩大都是為安娜而作的。譬如這首《晚步》:
松林呀!你怎麼這樣清新!
我同你住了半年,
從也不曾看見
這沙路兒這樣平平!
兩乘拉貨的馬車從我面前經過,
倦了的兩個車伕有個在唱歌。
他們那空車裡載的是些什麼?
海潮兒應聲著:平和!平和!
詩作中的泛愛思緒,精緻又清新的風格,明白地顯現出泰戈爾的深刻影響。
1917年左右,因為喜歡,郭沫若陸續翻譯了泰戈爾不少詩作。到了下半年,他與安娜的孩子即將問世。這樣,單靠郭沫若有限的留學官費,顯然不能支援家庭所需。他便從《新月集》《吉檀迦利》《園丁集》中選譯出一部分,輯成一部《泰戈爾詩選》,用漢英對照方式,加以註釋,寄往國內尋求出版,想換取一些稿酬補貼家用,可結果卻事與願違。
當時的中國大陸,知道泰戈爾的人十分有限;更重要的,“郭沫若”是誰?更少有人知。他的那些或高歌奔放,或寧靜沖淡的詩,是在幾年之後才與國人見面,從而震動詩壇,贏得廣泛聲名的。故此,他寫信給當時著名的商務印書館,求售《泰戈爾詩選》,被該館退回;再轉而投問中華書局,也同樣遭到拒絕……身處青春敏感階段,身受生活和精神雙重煎熬的郭沫若,遭受的打擊可想而知。
這結果引起了郭沫若的別樣反應。他一下子認為,他與泰戈爾不是一類人:泰戈爾是一位貴族的聖人,而自己是一個“平庸的賤子”。這兩個世界的遙遠距離,使他感到自己熱愛泰戈爾是“僭分”了。現實壓迫竟能導致人精神上如此大的變化,實在難以想象。可事實卻正是如此:“我和泰戈爾的精神的聯絡從此便遭了打擊。”
世上的事,有時可能因為一些看似偶然的因素,發生很大變化。這一點在郭沫若對泰戈爾的眼光轉移中,可以清楚見出。
那部費去郭沫若很多心血的泰戈爾詩選,最後在輾轉的途中竟然遺失了,以致後來匯聚他翻譯作品的《沫若譯詩集》中,沒有收置一首泰戈爾的詩作,太令人遺憾。不過,在郭沫若的文章裡,我們偶爾還能讀到他翻譯泰戈爾的詩句,此處不妨摘錄一節,以窺斑見豹。1920年2月,郭沫若寫有一篇《論詩三札》。該文對詩歌的內在韻律,這般論述:“內在韻律訴諸心而不訴諸耳。泰戈爾有節詩,最可藉以說明這點。
請把你心中的秘密藏著,我的朋友!
請對我說吧,只對我說吧,悄悄地。
你微笑得那麼委婉,請柔軟地私語吧,我的心能夠聽,不是我的兩耳。——《園丁集》第42首
這種韻律異常微妙,不曾達到詩的堂奧的人簡直不會懂。這便說它是‘音樂的精神’也可以,但是不能說它便是音樂。音樂是已經成了形的,而內在律則為無形的交流。”
他的一首《岸上》第三節,還直接寫到了泰戈爾:“我的阿和/和著一些孩兒們/同在沙中游戲。/我念著泰戈爾的一首詩,/我也去和著他們遊戲。/噯!我怎能成就個純潔的孩兒?”
後來,這些受泰戈爾影響的詩作,陸續在《時事新報》“學燈”欄目刊出,這極大地激發了郭沫若的熱情。然而不久後,他讀到了美國大詩人惠特曼的《草葉集》。那擺脫一切舊有形式與內容的風格,雄健而宏大的氣象,與“五四”時期青年的精神十分合拍。在惠特曼影響下,又加之“學燈”編輯宗白華的熱切催促,郭沫若的詩歌火山被引“噴發”。1919年至1920年之交的三四個月時間,郭沫若創作出了他一生最優秀的一批詩作:《立在地球邊上放號》《地球,我的母親》《匪徒頌》《晨安》《鳳凰涅槃》《心燈》《爐中煤》《巨炮的教訓》……它們也催生了詩集——中國新文學史上浪漫主義詩歌的奠基和高峰作品——《女神》。
從以上歷程可以看出,郭沫若最先是受到泰戈爾深刻影響的,而他的成名卻有賴受惠特曼影響的一批詩作。時代需求和創作之間,常常並非如人們主觀想象的那麼契合,但它卻有意無意左右了詩人的創作走向。這之後,郭沫若詩作中反映出泰戈爾影響的因素,已經十分稀薄了。不僅如此,隨著時代的發展,郭沫若對這位給了自己許多近乎“涅槃”快樂的詩人,有了許多不滿足。
藝術家創作道路的遷變
1924年,大詩人泰戈爾應邀訪華。訪華之前,國內多家報刊為此作了大量宣傳:或翻譯其詩文,或出“專號”造成聲勢……此時的郭沫若,無論文壇名聲、地位,都非先前幾年可比,思想上發生轉折,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此前的1923年10月,郭沫若寫出一篇《泰戈爾來華的我見》的文章,表達了自己對詩人訪華的看法。文章中,郭沫若對當時國內熱熱鬧鬧請文化名人杜威、羅素來華演講,表示不滿。他以為,一般國人對這些名人的思想並無精到研究,請他們不過是虛榮心的表現。在他看來,這熱熱鬧鬧的活動就像演辦一次次“神會”一般;而當時準備請泰戈爾訪華,在他看來,也不過是又一次“神會”罷了。
此時的郭沫若認為:“他(泰戈爾)的思想我覺得是一種泛神論的思想,他只是把印度的傳統精神另外穿了一件西式的衣服。”“在西洋過於趨向動態而迷失本源的時候,泰戈爾先生的森林哲學大可為他們救濟的福音。但我們久沉湎於死寂的東方民族,我們的起死回生之劑卻不在此而在彼。”
對於泰戈爾宣傳的主張,郭沫若認為在當時的中國是不必要的:“一切甚麼梵的現實,我的尊嚴,愛的福音,只可以作為有產階級的嗎啡、椰子酒;無產階級的人是隻好永流一生的血汗。無原則的非暴力的宣傳是現時代的最大的毒物。”我們可以看出,此時的郭沫若,已自覺地秉承唯物史觀,並站在底層立場來觀察、分析事物和運用各類主義思潮了,並不因為曾對泰戈爾非常鍾情而放棄自覺的立場轉移。郭沫若的這篇文章,也許還有文學同仁的影響也未可知,但他思想的轉變是明顯的,雖然時間才過去幾年工夫。
人的生存道路、藝術家的創作道路,有時常常發生遷變。這遷變,有時是自覺的,有時卻不由自主,受著時代風潮推衍而行。郭沫若先前極度迷戀泰戈爾,短短几年後便對其思想重新認知、批評可略為證明;今天我們記錄下郭沫若早期的這一歷程,也能提供一個認識人、認識詩人的個案。我們在分析、領會一個人、一位詩人的思想或詩藝演進時,有時不免簡單模式化。但實際人的發展是極為複雜的,與時代,甚至諸多偶然因素都有絲絲縷縷的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