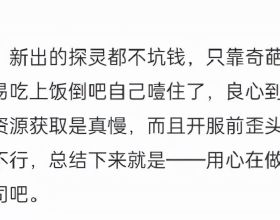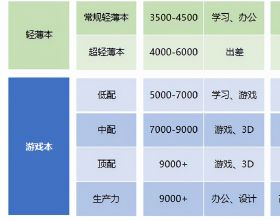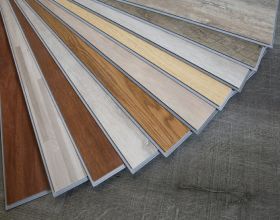我國神經病理、電生理臨床與研究事業,他是開山鋪路架橋人。在他心中,協和為重,家為輕,病人最重,名利最輕。科室長年辦公用房緊張,他默默收拾起神經病理標本,把本已狹小的家裝點得滿滿當當。耄耋之歲,依舊出診、查房、讀片,指點學子迷津。
【聽醫者講述】
建國之初入協和,名師帶教學業精,一線工作七十載,臨床病理共輝映。
節衣縮食澳洲行,滿載裝置回國來,解密“姜氏三兄弟”,初識罕見線粒體。
——訪談人戴毅
1953年下半年,我進到協和工作。先進入內科,張孝騫教授來接待我們。他說話非常客氣,說有什麼困難都可以去找他,並安排我們先在內科病房實習兩個月。
兩個月後,正趕上軍委衛生部讓協和給軍醫大學培養師資,開辦培訓班,讓各科加強對年輕醫生的培養。在這種情況下,就要重新分配科室。當時神經科叫腦科系,精神科病房和神經科病房是分開的,我覺得神經科查房挺好的,我也學了俄文,正好學了巴甫洛夫,所以就選了神經科。
我到神經科正趕上1954年的畢業班實習,當時的主任許英魁教授生病了,沒有上班,接待我們的是副主任馮應琨教授。馮教授要求很嚴格,他教我們病理標本怎麼採取,病歷要寫些什麼,還親自修改。當時24小時值班制是很嚴格的,實習大夫和住院大夫不能離開醫院。病人的三大常規、胃液分析等化驗都要大夫自己做,每個病房外面都有一個化驗室,裝置非常齊全。查房、檢查、化驗做得不合適,提出問題後都要重新再做。許英魁主任上班以後,帶著助教匡培根大夫做腦解剖標本。匡大夫給我們講屍體解剖和定位診斷,佈置我們給每個標本畫解剖圖,半年下來畫了100多張圖。
1955年春天,許英魁主任開辦第一屆神經病理學習班,進修生、實習醫生、科裡醫生都可以聽課,但不能離開工作崗位,一週2~3次,脫產的可以和他一起看片子。
神經科屍檢的腦標本都歸自己管,許教授會不定期地切腦標本,他把大家都叫來,一邊切、一邊講,然後把這些標本都留起來備用。許教授講得頭頭是道,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加深了我對病理的興趣。我和舍友經常在晚上和週末到實驗室看片子。
同年,協和進口了一臺英國腦電圖儀。1956年,馮應琨教授帶著王積詁大夫一起做腦電圖,就把腦電圖室建起來了。1957年上半年馮應琨教授就開始辦學習班,每班人數挺多,本院大夫也可以參加。但是隻講3個月,講完以後準備開下一個班。我旁聽了一部分的課,到下半年再開學習班的時候,他讓我脫產跟他學習腦電圖,目的是給他描圖。當時我和北京醫院的蔣景文教授一起脫產參加學習班,輪班描腦電圖,描完以後寫報告,馮教授批改後再發出去。
後來在馮應琨教授的推薦下,我來到澳大利亞學習神經病理。珀斯的病例很多,每個禮拜都有幾個腦標本送來,再由 Kakulas教授帶著大家一起切腦標本,切完以後做記錄,然後包埋、製片、看片並討論。那時,協和的實驗室主要是屍檢病例,沒有神經活檢和肌肉活檢,我對珀斯這麼多好材料很感興趣,就拍幻燈片。Kakulas教授說可以照幻燈片,還可以影印病歷,但是要給他留一份。因為機會難得,所以我很刻苦,週末都到實驗室整理資料,把近百例的病理都照了幻燈片帶回來。
回國前,我把病理實驗室所有使用的藥品、幻燈機、投影儀、相機和小儀器等都買來,整整裝了兩大箱帶回協和。有了這個基礎,神經活檢、肌肉活檢很快就在協和神經科開展起來了,大大地促進了實驗室的發展。
記得以前學腦電圖時,馮教授講課就經常說有“姜氏三兄弟”,這三兄弟都是癲癇發作、小中風發作、間歇性智力障礙,十幾歲發病,20歲左右在我院死亡。1970年,三兄弟中的老二去世後,譚銘勳大夫就動員做屍檢,這是三兄弟的第一個屍檢。屍檢後有很多不同意見,我當時的臨床病理診斷是家族遺傳性多灶性缺血性腦病,性質待定。我在澳洲學習時記得法國發了一篇文章,他報告的是MELAS綜合徵。我覺得那個臨床病理報告和這個病例非常相似。三年後回國,我就找到這個病歷反覆地看,越看越像,可是沒有線粒體的直接證據。
1993年,三兄弟的外甥來看病了,跟他三個舅舅一樣,都是癲癇、消瘦、反應遲鈍,我建議給他做肌肉活檢,但家屬不同意。我說我們用針給他穿刺行不行?家屬同意了。在電鏡中觀察活檢穿刺取的肌肉,我們發現了線粒體異常,證實了之前的推測,就這樣,北京協和醫院確診了國內首個線粒體腦肌病MELAS型家系。所以,我一直認為,一定要把現在的科學和臨床病理結合起來。病理雖然是古老的,但它是疾病診治的基礎,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的病理長期發展下去。
(本報記者田雅婷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