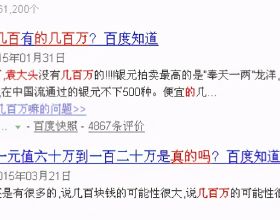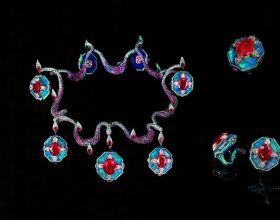文 劉旭
在傳說中尋找傳說,是為青春。
武林是一個傳說,八十年代也是一個傳說,在傳說中尋找傳說,是為青春。/《拳》封面圖
在何大草新作《拳》的後記中,他如是寫道:
“世上有兩種動物,很適宜比喻作家的勞動。一個是路上的駱駝,一個是水裡的鮭魚。駱駝不停地反芻,咀嚼著往事;鮭魚千萬裡洄游,要回到出生的水域,繁衍自己的生命。好的小說也正是這樣,在記憶裡深挖,用敘述抵抗著遺忘與死亡。”
而他最新的這部以武為母題的小說,便是從他的青春記憶中深掘出來的。四五年前,何大草就在構思這個故事。最初他的想法是寫一個短篇小說:“時間跨度只有一天,講一個正在讀書的男主人公去尋找傳說中的高人的歷程。”
因為一些事情耽擱,他遲遲沒有動筆。往後的一段日子,他關注到一些與武功相關的爭論,他覺得很是有趣,“好像那些內容也完全可以作為小說的元素” 。於是原初的故事在他的心裡不斷地生長與充實,最後在疫情深重、閉門不出的春天,何大草完成了書稿的寫作與修改。
何大草說,小說裡的“我”和他本人有一些重疊之處,他們年齡、學校與專業都是相同的。而“我”身邊的那些人物,也都是他在虛虛實實間建構出來的。於他而言,這是小說的魅力所在,既有一些實在的東西,又不乏足夠的想象力。
他把時間背景設定在了自己印象最為深刻的80年代,他每次閉上眼,那個時代中的細節都能一一浮現出來——馬路上的噪音,茉莉花茶的香味,他能立馬感知到。在他看來,那是一個很奔騰的年代:“故事所發生的1983年,相當於早春時節,馬兒已經披上了馬鞍,森林已經發了新芽,一切都呼之欲出,但還沒有綻放,總的來講,它充滿了期待,但人還是比較茫然的。”
何大草回憶,那時候的大學生,很少會主動地去尋找自己的位置,每個人都在等待分配,所以心理上的壓力和焦灼感是很強烈的。他覺得,這個時間點的特殊之處,在於它是爆發之前的寂靜。所以他想在闃寂當中,發出拳頭叩擊的響亮聲音。
而對他來說,故事的時代背景也必然是在那時。這與他的創作習慣息息相關,他的大部分小說都回避了當下的生活,他最早發表的一篇小說《荊軻刺秦》、寫王維晚年生活的《春山》,無一例外。他認為,眼下更多是表象的東西,是實在的生活,而回憶,則會讓他看見當初曾忽略的那些內容。所以對他來說,《拳》是一本緬懷之作,也是一部追憶之書。
三輪車、冰棒攤還有縫紉機和彩色電視共同構成了八十年代的社會圖景。
“成都是‘躺平’的城市,但關鍵時刻它是個‘硬骨頭’”
《拳》講述了幾次熱血澎湃的校園比武,同時也勾勒出一個尋找大師的旅程。除了豐滿的武林探險之外,不少讀者也注意到,書中提到了很多老成都的建築、吃食以及一些文化傳統。在何大草看來,復活成都的風物與舊日的市井生活,也是這部書所承載的使命之一。
杜拉斯曾說:“寫作,不是講述一個故事,而是同時講述一切。”何大草深諳此點。他很明晰的是,要將這些人物寫好,就要把他們嵌入到城市的風土民情當中,“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有了土地的味道,人也就有了質感” 。但何大草認為,《拳》這樣生動有趣的故事發生在任何地方都是可以的。但脫離了具體城市的生活,無論是節奏上還是內容上,都會變得截然不同。
他以“兄弟城市”重慶舉例。他說:“重慶是個大碼頭,兩江環抱的地方,很有江湖氣,生活在那裡的人,崇尚陽剛,可能每個人都是武林高手,如果故事放在那裡,是完全不一樣的寫法。”在何大草看來,與重慶的環境相比,成都更像一個養閒人的地方,茶館多,打麻將的也多,而頂尖的武術家就生活在人群之中,故事更有其神秘感。
近幾年,成都漸漸地變成了一個“網紅”城市。每每提及這裡,人們總是習慣性地談到美食、時尚以及安逸的生活。但在何大草心中,成都的氣質有更深層次的意涵。不久前,他的朋友向他約稿,讓他談一談心目中的成都。他第一個想到的不是茂密的植物,也不是老街巷裡的茶館,而是人民公園西北角的一塊碑。
“那塊碑很尖銳,像箭一樣朝著天空射去。”它建於1913年,是為了紀念成都保路運動犧牲的烈士們。在何大草心裡,保路運動某種程度上反映著成都的城市精神——為了捍衛權利,不惜去和力量更強大的一方發生對抗。他覺得,這是成都有“硬骨頭”的一面。他說:“人們往往對這座城市軟的部分津津樂道,但對於硬的這個面向,卻往往忽略掉了。”
何大草猶記得《一代宗師》當中的一句話:“功夫,就是一橫一豎。”他很願意用這句話去概括成都的性格:“平日裡,成都是‘躺平’的,但當需要它立起來的時候,它會變得非常堅硬。”人們所關注和欣賞的是成都“橫”的一部分,但在他看來,那塊碑是成都“豎”起來的樣子。他說:“如果說‘躺平’是成都的面子,那‘站起來’是它的裡子。”

平日裡,成都是‘躺平’的,但當需要它立起來的時候,它會變得非常堅硬。/圖·Unsplash
“拳頭裡蘊藏著不同的文化”
讓武俠迷很過癮的是,《拳》中寫到了眾多招式的拳法。但何大草坦言,作為一個小說家,他的確沒有辦法像一個武術專家一樣,透徹而詳盡地闡釋各種拳的奧秘,他只能憑藉自己的感覺來完成書寫。
而這些感覺,大多來自他年輕時的思考以及與他人的交談。他說,讀書的時候,愛議論的話題是:中國武術和西洋拳到底哪個更厲害?李小龍是否打得過拳王阿里?武術在實戰中究竟怎麼樣?
時隔多年,當他再度想起那些問題時,會深入地進行一番剖析。他覺得,形式各異的拳裡,實質上蘊藏著不同的文化。而面對這些,當時的人們態度是很複雜的:“一方面,大家對本土的武術有一種迷戀,而另一方面,人們也很不確定,這種武術在對抗中是不是會有真的效用。”

形式各異的拳裡,實質上蘊藏著不同的文化。/圖· Unsplash
那時,出於好奇,何大草和同窗的男生都訂閱了一本叫做《武林》的雜誌。他至今對其中講到的李小龍的故事有很深的印象。在他看來,李小龍是一個技術上非常懂得精進的人。在與不同功夫交手過後,他都會去取長補短,學習詠春拳、跆拳道、阿里的拳擊步法,創立雙節棍,都體現了為我所用的精神。這是何大草心中最高階的武術家的境界,李小龍所言的“以無法為有法,以無限為有限”也深深地烙在了他的心裡。
所以在小說中,他也塑造了一個不斷向對手學習的女子寶珠。寶珠在最終回合打出的拳,並不是她慣常使用的,而是從對手身上習得的。在取勝過後,寶珠的對白也在某種程度上呼應了李小龍的觀念:“俺不懂這啥拳、那啥拳,但凡過了俺的手,就是俺的拳。”何大草認為,我們今天,同樣需要有這種精神,持續地學習,才有可能讓那些苦功夫凝聚成一個特別有力量的時刻。
不過,對於那些習慣了傳統武俠敘事的讀者,《拳》似乎少了些大開大合的情節。何大草也並不否認這點。他說,如果再早一點寫的話,他很可能會寫成那些讀者想要看到的樣子。他自己早年也非常迷戀金庸,書中所展示的武功招數也曾讓他痴迷。但經過了時間的沉澱之後,他發現,那個世界中的人大多是為武而生的,“他們的理想與生活都是武術”。但《拳》不一樣,它當中的人物還有同樣精彩的生活部分,“在這裡,人生歷程會超過純粹的武林故事”。
“上升的一切必會匯合”
和很多創作者一樣,何大草在《拳》中也夾帶了一些“私貨”。比如,在宿舍的一次夜聊薩特的過程中,“我”提到了一個觀點:“用來闡釋哲學的小說,只能是二流的,跟科普文章差不多。”而這個觀念,也是他個人所秉持的。
在他看來,直接用哲學去呈現哲學,比用文學來闡釋哲學更有意義。在他的理解中,好的文學是自帶哲學價值的。西南聯大時期,金嶽霖曾在講讀《紅樓夢》時提出過類似的見解:“《紅樓夢》當中的哲學不是哲學家的哲學。”
何大草對此很是認同,他認為,人物的對話以及命運的走向,是能夠體現這一點的:“讓文學回歸到那些可感的細節當中,一碗茶、一杯酒、一次別離,都可能具有情感與思想的深度。”而他在書寫《拳》時,也將這樣的想法傾注其中。

讓文學回歸到那些可感的細節當中,一碗茶、一杯酒、一次別離,都可能具有情感與思想的深度。/圖·Unsplash
寫作期間,他曾為了探尋拳中的哲意而請教過一位資深武迷。朋友告訴他:“武即是文,是文化。”他深以為然。他覺得美國作家弗蘭納裡•奧康納的一篇文章題目可以解讀這一切——“上升的一切必將匯合”。他認為,無論是什麼學問,上升到頂點之時,匯合出來的都將是生命的哲學。
長久以來,何大草一直都想寫出“一文一武、兩部對稱而相異”的小說。在《拳》完成之後,他也算是了了一樁心願。對他來說,這最大的感觸是“好像多活了很久似的”。在寫作《拳》的幾個月裡,他每天都徜徉在舊日成都的街巷中,那些現代的熱鬧好像與他並無關聯。而在寫《春山》時,他也自我感覺像個隱身觀察者:“我看著王維和裴迪在吵嘴,就好像我也在輞川生活過了。”
寫作之餘,何大草也會涉足繪畫。他的審美偏好也經歷了一定的轉變:“我年輕時,喜歡張大千那種雄渾的潑墨,但如今,我越來越喜歡工筆畫。”在他看來,那些細緻入微的描繪,需要大量時間的累積,“雖然比較慢,但內在的推動力卻是強悍的”。他也把這種技法“嫁接”到了小說當中。他緩慢地推動著每一步,一點點地拼合出有縱深感的人物,進而讓人們洞見他們的內心世界。

中國畫的精髓在紙筆點墨中,見於自然山水間,世間萬物與畫家筆下之物的渾然一體,縹緲間,見者心安。
在《拳》的腰封上,寫著醒目的一句話,似乎囊括了這部小說的幾個關鍵詞:“武林是一個傳說,八十年代也是一個傳說,在傳說中尋找傳說,是為青春。”於何大草而言,書是對舊日的記錄和追緬。而對於未曾領略過那個時代的讀者們來說,《拳》裡盡是逝去的城市景緻與平凡人的風骨。
草而言,書是對舊日的記錄和追緬。而對於未曾領略過那個時代的讀者們來說,《拳》裡盡是逝去的城市景緻與平凡人的風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