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只恆文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顧城《一代人》,發表於1980年第3期《星星》詩刊)這個特殊的年份,這個多雨的夏日,大學生詩人透過黑色的眼睛發現了什麼?參加2021年第十四屆星星大學生詩歌夏令營的營員,在經歷了“不平凡”的人生體驗,見證了眾志成城與堅忍不拔後,以自己的生命感悟和成長記憶,寫下動情的詩行和遠方的追尋。讓我們看看來自河南理工大學的郭子暢、貴州民族大學的盧酉霞、暨南大學的張雪萌三位00後“營員”的浪漫與遐想。

郭子暢,2001年出生,河南理工大學學生,曾獲第七屆野草文學獎、首屆00後國際詩歌獎等。
空杯子
——寫給自己的20歲
河南理工大學學生 郭子暢
將一個杯子裡的水全部喝乾淨
杯子就恢復了原來的樣子。
其他的杯子也是同樣的道理。一顆空蕩的心
在注滿和掏空的過程中,逐漸
接近生命的本質。
在獲得和失去的過程中,它們
重新找到彼此的面孔。
還記得,多年前
曾經失手打破了一個空杯子
我被那些尖銳的部分刺得鮮血淋漓
時至如今,疼痛
早已經被遺忘在腦後。
而那些破碎的,尖銳的部分
卻成為一個人永恆的記憶,
卻在繼續論證著我們這被虧欠的一生。
郭子暢非常喜歡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樂府詩。“人間樂未央,忽然歸東嶽。”“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他提到這些詩句,並說道:“我相信,古今的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無不被其中熾熱的悲傷和情感擊中,但我也相信其中不僅僅是以情感動人,而是更深層次——對生命、生存困境認知的共通與體認。在這樣的過程,有種像尼采所謂的日神精神與酒神精神的統一,我們在這某一刻看清了生命的本質,但也不再為人生無意義與意義的悖論所糾纏,從而抵達更高層面——形而上或審美上的救贖。”這也是郭子暢的“詩觀”。
“遇見詩歌是一次偶然,寫詩也是一種偶然。”郭子暢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匠人般的堅持、平常的心態和追求精湛的態度’,這是我要送給自己的一句話,也將是在詩歌道路上對我自己持續的警醒和鞭策。”
在他看來,“一個詩歌初學者本身,不必要糾結於暫時的熱鬧,而是沉下心來,蹣跚學步,腳踏實地式地閱讀思考,培養自己的歷史意識和敏感度,以及對詩歌藝術本身的把握,從而形成自己獨特的詩歌創作與認知區域。”

盧酉霞,2001年出生,貴州民族大學學生,貴州省作家協會會員。
度,及渡
貴州民族大學學生 盧酉霞
把身上積釀已久的黴質抖出來,借長春的陽光晾晾
離黔北行成為我波瀾不驚日子裡孕育出的
深刻之所
我的快感源自對光的捕捉
長春的美我一一悉數給你
星的指頭們接受北方的神諭
計數關於松科樹木的性別
對綠色和老電影持有敬畏
是我泅渡在這斜面人間的作證物
肌膚上沁出的不是汗珠
而是與一座城市相擁後留下的吻痕
臨行前停止與野菊交談,虔誠地在詩碑前
交納自己曾經衰頹與破碎的部分
腦袋如漿果,吸附在右側車窗
綠化樹自矜它的頎長身材,審己度物
青扦和黑鈣土,漂流和委頓,構成相反面
相機也有純粹理想,幀幀露齒主義
儘管歡愉無限
我還是沒法停止隱隱發癢的悲憫心
悲憫短暫相聚後我們將各執一詞,逐一離席
悲憫我的線性表達沒有云朵嬗變那樣決絕
這是夏令營最後一晚,盧酉霞為“我們的長春 我們的青春”詩歌朗誦會寫作的“急就章”。說到這首詩,盧酉霞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小夥伴們紛紛感慨沒時間寫或者寫得不好,當然這其中謙虛和低調佔據的成分多。不過我由此悟出,真正的詩作應當是將感情‘冷卻’好後進入沉思狀態下創作的,每一首詩都是自己的‘孩子’,剛‘出生’時或許我們會滿意地會心一笑,但過了一段時間再拿出來看看,會愈發覺得不堪入目。其實這正是進步的表現。我們目前處於發展的過程中,尚未形成固定的價值觀念和審美判斷,隨著知識學歷的增加,每隔一段時間回頭看看,自然會覺得寫得‘醜’。”
地處半邊陲之地,盧酉霞作品中很少有故土情懷。問起這個緣故,她解釋道:“這可能是源於體裁範圍的狹隘,也可能是沒有久居故鄉,家土情懷不夠厚重。從某種角度來說,這樣是‘自私的’,作為一個創作者,不能忘了根,忘了本。”
“像呼吸一樣自然”——這是盧酉霞的“詩觀”,“或許在詩歌路上我們會聽到多種聲音,有人認可就有人質疑。以前我總是追求‘陌生化’的表達效果,拉大事物本體與喻體之間的距離,能取悅自己就足矣。適度追求並非壞事,不過凡事都要有個度,把握好度我也明白,但在寫作中往往控制不好,要麼超度要麼不及。今後的創作過程中我將注入更多經驗元素,而不只是假大空的先驗之辭。一首詩固然不是每個人都能讀通透的,但如果無人能讀懂,那也沒有其存在的價值。真正的詩歌,其中的情感是藏不住的。在此之前,我很少思考生命的向度,今後將嘗試走向返璞歸真,細緻體悟生命的本真,體驗和認知生命人格。”

張雪萌,2000年出生,暨南大學學生,出版有詩集《獵夜歌》。
車 站
暨南大學學生 張雪萌
從未將它視作目的地,儘管
每日的疲憊準時湧入:一個途經的匣子,最好
潔淨、不擁擠,細心地備有廁紙
去維繫戀情,騎士
去為下一單生意,成功者
去把腦袋靠在玻璃
發一會兒呆,不為了什麼:沿途植被
匆忙披覆上蒼綠,翠綠
南境以南,越發濃釅的塗層。
目的擺動起手腳,催促著
在準點時刻抵達的擁抱
磁鐵般吸住彼此,匣子裡
兩個靠近的發條玩偶。凌晨時分
它停下咀嚼,消化盡體內的蟻群
大理石地面,重又映出吊頂的鎂光
鐘擺。偶爾尖銳的播報。角落裡
那個疲倦如麻袋的工人。
都哪裡去了?先生。女士。
先生的女士,至於那位,我們更不曾打量過的
灰鼠一樣鑽進地鐵的父親。
在我們身後,空蕩如遺址,久佇
像世紀盡頭傳來的,一句嘲諷。只有這匣子
未竟的目的地
消隱著。揮手,外鄉的塑膠玩具
淚水,必要的寒暄與喊聲。
張雪萌的這首詩寫於上個學期。“那個階段,因為參加詩歌活動,或是去其他省市見朋友,經常需要在各地跑來跑去,車站和機場也成了我頻繁出入的場所。”
她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一次從東莞回到廣州,當時已經是晚上十點,平時熙熙攘攘、人頭攢動的廣州南站難得安靜了下來,偶爾能見到神色匆匆揹著蛇皮袋的工人、在車站座椅上打盹的上班族。那些吊頂的鎂光燈映著空曠的大理石地板,車站的發車報時顯得格外尖銳。”
那一刻,張雪萌開始思考車站與人群、與我們流動的生活之間的關係:它像一個匣子,日夜吞吐著人潮,在這人潮中,每個人為了各自的目的奔忙流竄,人人自顧不暇、神色匆匆,又總有真摯的情感——揮別、重逢、相伴——在其中生髮。這便是一處承載詩意的場所,也是現代科技催生的新場景,需要被注入新的時代表達。
來到長春參加第十四屆星星大學生詩歌夏令營,讓張雪萌有機會對同齡寫作者有了更近距離的觀察與思考。“目前00後創作群體還不夠鮮明到可以被提煉為詩歌史上的一代,但90後已經展現出自足、豐富、屬於新生力量的寫作風貌。站在00年的門檻處,一方面,我和自己前代的寫作者們有著頻繁的互動;另一方面,我也滿心期待著尚在到來途中的00後群體。雖然關於00後的代際特質還在形成中,我和幾位00後的詩人也彼此交換了各自的詩歌觀念,但,詩人的意見很少統一,每個人都需要在嘗試和失敗中找尋自己的路。這是一種寂靜的幫派戰爭。我尊重並祝福著每位同齡者在這條路真誠的探索,就像友誼的存在,正是方便了我們彼此眺望又相互砥礪,真正讓個人得以在詩歌的生態圈中成長起來。”張雪萌說。
三年前,張雪萌從北方城市來到花城廣州讀書。回憶起近年的詩歌寫作,張雪萌說道,“上了大學以後,才真正有時間、精力投入到詩歌的創作中去。在文學院三年的學習中,我開始形成對個人詩歌觀點的模糊認識。”
“詩發生於一次觀測活動,它置身於劇場,密切注視著戲臺上的人群。劇場的名稱有時是‘傳統’,有時又是‘當下’,總之,它提供著可遊戲的場所。於我而言,詩人本身的角色應當在文字中隱退。詩人畢竟作為社會中的一分子,TA的眼光如何聚焦、如何折射當下時代提出的諸多命題,又如何善意地關切著形形色色的大眾,這是首先需要給予考量的。”這是張雪萌的“詩觀”。
為期4天的詩歌夏令營生活,讓大學生詩人凝聚了友誼、交換了歡樂。自2008年開辦以來,星星大學生詩歌夏令營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與認同,為中國當代詩壇發現、培養和扶持了一批又一批的大學生詩人,為漢語詩壇源源不斷地輸送著新鮮血液。每一屆夏令營,《星星》詩刊編輯部都會把營員的詩歌作品彙整合為一本詩集,送到每一位營員手中。“天上有三顆星星:一顆是青春,一顆是愛情,一顆就是詩歌。”這是詩集封底的一行字,也代表著《星星》全體編輯對青年學生詩歌寫作者的美好祝福和殷殷期盼。
在朋友圈中曬出這氤氳夢想與熱情,清新與純粹的詩集,張雪萌感慨地說,“正如同我們寫作道路上的一處‘車站’,在短暫的相聚後,又要投入各自的奔波與忙碌。然而,總有情感在其間茂密地生長出來,像這‘未竟的目的地’,催生出‘揮手,淚水,必要的寒暄與喊聲,浪漫與遐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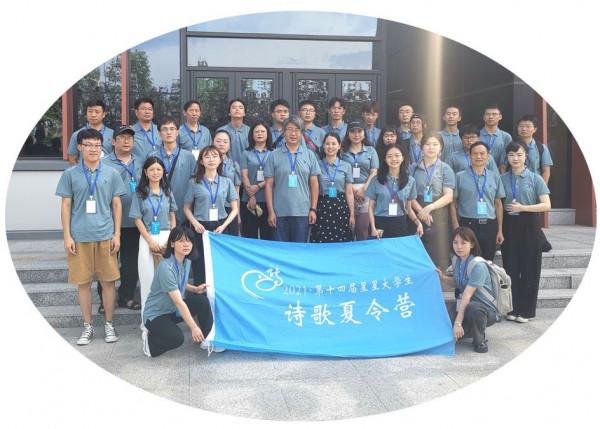
2021星星大學生詩歌夏令營全體合影。(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只恆文 攝)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