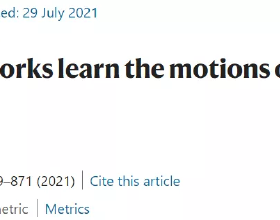情葬巴山
作者:張益庭
編者語:他和她都是知青,她是他的音樂知音,對他彈奏的手風琴曲百聽不厭。兩個情投意合的年輕人本該有一番深深的情感經歷,但蹉跎歲月卻改變了他們的人生軌跡,演繹了一出悽而不美的愛情故事……
得知曉南病逝的訊息,我怎麼也不能相信這一事實。她剛過完50歲的生日就匆匆地走了,帶著太多的遺憾和悔恨。
一
我是在1966年底回重慶時認識曉南的,那是我自1964年高中畢業下鄉以來第一次回到重慶。在農村的兩年裡,我始終用一句話激勵自己,那就是“志在農村,做一個又紅又專的革命接班人”。
我們下鄉的地方是鄰水縣石永區古路公社社辦林場,在那裡,我學會了犁田、耙田、插秧等農活,一年365天從不休息。年終結算時分到190元,這就是我一年辛苦勞動的報酬,當然這不包括安置辦公室發給每個下鄉知青的伙食費和每月2元的零花錢。
回到重慶,剛放下行李和我心愛的手風琴,1964年和我一起下鄉的鄰水風椏林場知青朋友李忠公和蘇甫其就來找我了。他們邀請我參加“重慶上山下鄉兵團宣傳隊”,這個宣傳隊駐在當時的重慶12中,即現在的復旦中學。
在那裡我遇見了曉南。她是一個活潑美麗、大方健談的姑娘,有一對會說話的大眼睛和魔女一樣的身段,1964年她初中畢業就下鄉到了萬源黃鐘區絲羅公社林場。這時候是宣傳隊裡的舞蹈演員。我們好像一見如故,很投機,常常講述各自林場的事情,談起下鄉後的感受。
一天晚上,我在寢室看書,忽然聽到一個少女用銀鈴般的聲音在輕輕地叫我。我順著聲音看去,窗前立著一個綽約的身影,我知道一定是她。曉南邀我出去走走,談談宣傳隊的工作,因為我是宣傳隊隊長。我們順著復旦中學出通遠門往七星崗方向走去。
現在看來這樣的想法未免有點可笑,可是在那時我們都真的共同感到,要做好任何工作都必須突出政治,因為當時最深入人心的一句話是“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於沒有靈魂”。因此,曉南跟我在一起時談得最多的也是政治。在那個年代裡我們對政治似懂非懂,但除了高談這些話題以外,我們就真的不知道還能說些什麼了。和自己心儀的朋友一起漫步在山城萬家燈火的大道上,雖然心中洋溢著幸福,但是口中談論的卻是嚴肅又嚴肅的問題。我們並沒有卿卿我我,也沒有我愛你、你愛我之類的甜言蜜語,那畢竟是革命的年代,像《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裡的主人公保爾·柯察金一樣,我們有意無意地迴避愛,因為談情說愛是小資產階級。
然而,有一天,我因為患大葉肺炎住進了位於南岸區玄壇廟的重慶第五人民醫院,三天沒有到宣傳隊活動。第三天,我媽告訴我有一位女同學到醫院來看我。當我努力睜開雙眼,映入我眼簾的是一位長辮子姑娘,曉南來看望我了。我們默默對視了一陣,我不知道用什麼語言來表達我的愉悅之情。我從內心感激這位才相識不久的姑娘,頓時病也好了許多。曉南滔滔不絕地告訴我那些天宣傳隊裡發生的事情:宣傳隊已移師達縣,各自回縣,因此我們的宣傳隊也隨之解散了。後來我才得知宣傳隊解散時,大家要一起合影留念,曉南藉故胃疼不願參加,這時有宣傳隊裡的其他人說,是因為益庭沒在她才不願。她從宣傳隊裡的鄰水知青處聽到我的病情,特地到醫院看望我。
1967年初,我返回林場,剛進門就有人告訴我有萬源來的信。信拿在手裡厚厚的一疊,是曉南寫的。我興奮極了,一口氣讀完了它。信裡的內容仍然和我們在重慶時的那些談話一樣,無非是有關革命理想、時事政治的討論,但我卻也跟往常一樣從信紙上那女性味十足的文字中體會出了一分溫馨和甜蜜,旅途疲勞頓時煙消雲散了。收到信許多天裡,我一直沉浸在那種溫馨和甜蜜中,我把信放在枕邊,每天都要看幾遍,彷彿永遠都讀不完。
二
林場當時已基本處於癱瘓狀態,大多數知青都回重慶了,剩下的也無事可做。閒極無聊,我也踏上了回家的路途,並把這一訊息告訴了曉南。
於是,當年9月我們在重慶又相見了。不久,我鼓足勇氣在一個知青朋友的陪伴下第一次去了曉南的家,見到了她的媽媽、姐姐等家人。我覺得他們對我非常親切。這樣一來,我跟曉南的關係就有了進一步發展,成了她家的常客。自宣傳隊相識之後,曉南就是我音樂的知音,對我彈奏的手風琴曲百聽不厭。這年秋天,曉南邀請我到她的家裡獻藝,大概是想讓她的親人瞭解我。我當然欣然應允,把手風琴帶到她家,在她的家人面前演奏,聽到她的母親和姐姐讚許我的演奏,曉楠掩飾不住滿心的得意。
曉南的家住在渝中區,我住在南岸區,中間隔著一條長江,當時長江上沒有大橋,只能靠輪渡過江,而輪渡收班時間最遲是晚上10點,因此每次見面時那說不完的話都只能因為要搭乘末班輪渡回家而匆匆結束。記得有一次曉南問我的理想是什麼,我說我不再奢望成為一名科學家或音樂家,我只想做一名能自食其力有穩定收入的工人,這樣我就很知足了。曉南點頭說她的要求也不高,同我一樣只是想做一名普普通通的勞動者。是啊,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下,我們還有什麼能力去奢侈的構築自己真正渴望的宏大理想呢?隨著交流的增多,漸漸地,我們都把自己的家庭狀況、歷史背景互相做了介紹。
我的父親出生在山東蓬萊海邊的一個漁村裡,這是一個祖祖輩輩都生活在海邊的家庭。祖父因家庭貧困離開家鄉到煙臺謀生,在一家小店當學徒,後來養育了我的父輩六姐弟。我父親最小,靠他自己的勤奮及家人的幫助畢業於復旦大學經濟學系。我父親是家族自清同治年以來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大學生。他勤奮、善良、耿直、忠厚,對新中國和社會主義懷有深厚感情。
自我懂事以來,家庭出身問題就象一個巨大的陰影一直籠罩著我。雖然我的學習成績從小學到高中一直名列前茅,並且又有音樂天賦,但是1964年高中畢業時我仍然同其它出身不好的同學一樣未能邁進大學殿堂。落榜後,我感到前途一片茫然,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我下了鄉,希望能為國家做點貢獻,實現作為一個人的價值。
曉南也出生在一個書香門第。父親雖然也有一些歷史問題,但總的來說家庭情況要比我好一些。可是1964年初中畢業以後,她也未能繼續進入高中學習。我們同病相憐,在情感和思想的交流中尋找慰藉。
這樣,我不由自主地墜入了愛河。1968年夏天,我終於不滿足我和曉南之間的模糊關係,給曉南寫了一封信,直截了當地表達了我對她的感情,並且要求她給我一個明確的答覆。信發出後,我就和鄰水的幾個知青朋友一起到了成都,住在成都衛幹校接待站。幾天後,曉南居然也來到了這個接待站。我驚奇極了:偌大一個成都,居然在這裡和她不期而遇,難道真的是“有緣千里來相會”?!曉南見到我第一句話就說,“你離開重慶時給我的信收到了,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你要同我確定戀愛關係,我的行動不是已經說明了這個問題嗎?”
那天我醉了。我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和曉南走了整整一天,漫步在成都的大街小巷,也不知道累,當然也不知道休息。在喧囂的車水馬龍之間卻彷彿只有我們兩個人在私語。曉南邀我第二天到她姐姐家去玩,當時她姐姐住在成都龍泉驛。我第二天一早乘車到達時,曉南和她姐姐都來車站接我,那份親切和熱情令我至今不忘。曉南母親也在那裡,從她的慈愛的笑容裡我再次感到了溫暖。在成都我們渡過了一段美好的時光,真正談起了戀愛。這時我才深深地體會到生活和世界真的是如此美麗!
那段花好月圓的時間,曉南也經常到我重慶南岸十一中的家裡去玩。她聰明伶俐,很討我母親喜歡,雖然我們還根本沒有條件認真討論將來的婚事,可是看得出來母親明顯地支援我們的關係,每次曉南到我家裡,母親總是千方百計地款待一番。曉南也常到我家做客。周圍的鄰居也常常誇獎她。有一次曉南迴四川江安老家還特意給我弟弟帶了幾根魚杆,因為她知道我弟弟喜歡釣魚。她的善良、聰明和得體博得我的所有親人的好感。我的幾個弟弟跟她非常親近,儼然把她當成未過門的大嫂。
其實除了愛情,我們的生活裡沒有什麼亮點。母親偶然跟我討論我和曉南的關係,總忍不住要輕輕嘆息。也許正是因為現實令人絕望,愛情才越發顯得那麼珍貴,須臾不可缺少。我和曉南不顧一切地沉浸在只屬於我們兩個人的感情天地裡,如痴如夢地期盼著生活中的奇蹟。然而等待我們的是殘酷的現實。
1968年底,毛主席發表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社辦林場正式解體,我們都要去插隊落戶了。那年春節前幾天,曉南到鄰水來了,那時我在鄰水縣宣傳隊排練演出。她在縣城住了兩天,然後我們一起回重慶過年,那年春節我是在曉南家過的。離開她家時曉南三兄妹都出門送我,她的姐姐特地跟我說,在農村好好過,以後無論有什麼困難我們一定會幫助你的,當時我聽了很感動,似乎真的有一家人的感覺。回農村前曉南提出想從萬源遷到鄰水來,這同樣也是我的心願,可我當時還沒有具體落實會到哪裡插隊落戶,因此我告訴她稍待一段時間,等我安頓好以後再說。於是曉南便先回到萬源黃鐘區絲羅公社插隊落戶。
三
1969年底,宣傳隊解散,我回到鄰水古路公社插隊落戶。我給曉南連寫了幾封信,瞭解她的近況。無奈限於當時情況,達縣地區交通很不通暢,郵件往來極不方便,我有幾個月沒有收到曉南的信。有一天,我到公社去趕場,突然間接到了曉南的信,這讓我欣喜若狂。但那封信拿在手裡薄薄的,拆開來一看,我整個人都彷彿掉進了冰窖裡──這是一封與我斷交的信!!我百思不得其解,痛苦中我苦苦思索了幾天,最後決定到萬源去找她。我無法相信她會做出這樣的決定。
匆匆地,我便和知青朋友何六喜一起啟程了。坐了一整天的車終於到了萬源,可是剛歇息下來一打聽,才知道絲羅公社離縣城還有100多里不通汽車的山路。於是第二天一早我們就出發了,翻了幾座大山,一直走到深夜才到達曉南落戶的生產隊。
那是一個人煙稀少的深山溝,周圍都是巍峨聳立的大山,只有很少的田土可供耕作。那裡的農作物主要是馬鈴薯,只能在大山裡燒荒種植,條件極為艱苦。絲羅的貧窮落後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想起她曾經告訴過我,她的林場在一個青山綠水的地方,那裡曾經是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老根據地。絲羅公社應該風景秀麗,春光明媚。但是眼前的實際情況跟她的描述實在相差太遠了。我下決心一定要想辦法把她遷到鄰水去,靠我近一點。
曉南完全沒有想到我會去找她。她不冷不熱地接待了我們,安排我們住下。說了一句“明天再談”就獨自到鄰居家借宿去了。在那裡,知青的生活作息也和當地的農民一樣,每天只吃兩頓飯。因此,第二天等到曉南下班回來天已經完全黑了。在曉南忙著做飯時,何六喜堅持要拉我出去走走,他告訴我他在曉南的書桌上翻看一本海涅詩歌集時看到一頁信紙,原來是另外一個人向她求愛了,估計她已另有男友了。
我仍然深深地愛著曉南,但是曉南的態度和第三者的插入刺傷了我的自尊,我不願意乞憐。我詛咒命運,詛咒世道,心裡暗自譴責曉南的背叛行為。我沒有質問曉南,因為我從她的眼神裡看出一絲難言的無奈。社辦場的解體對許多知青、特別是女知青是一個重大打擊。因為他們被迫接受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和更加孤獨的生活。我知道許多女知青都在絕望中尋找救命稻草,透過親友或婚姻跳出大巴山,就像燈蛾撲火一樣。而我的家中兄弟五個,全都面臨著“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命運,只有老母親一個人用她微薄的工資收入撐持著這個家。調工對於我真是遙遙無期。因此儘管當時的我們正值青春年華,情感萌動的年齡,卻不敢奢望成家立業。所有的夢想,所有的許諾,在那種無情的現實面前都顯得非常蒼白。也許正是因為這種幾乎絕望的境地,才使曉南採取“病急亂投醫”的行動。
我決定第二天就回鄰水。那天曉南沒有去出工,她殺了一隻雞,做了一頓豐盛的早飯,我心煩意亂中嚥了兩口就匆匆上路。曉南送我們一直走到公社。這段路大概只有兩三里地,就在這兩三里地的無言中我和曉南的一切從此就都結束了。我的美好的初戀就這樣在一剎那間夭折了。我嚥下了酸楚的眼淚,在心裡默默地跟曉南道別!頭也不回離開了絲羅,也離開了所愛。
1970年,我去了正在修建襄渝鐵路的達縣民兵師鄰水民兵團宣傳隊。民兵團的團指揮部設在萬源縣的平溪鄉,離縣城只有六公里。有一次我們宣傳隊到萬源縣城演出,意外地碰到了曉南。當時她已經在縣城一個小學教書,豁然間我似乎解開了當年曉南寄給我的那一封薄薄的絕交信的謎底,她已經選擇了一位在萬源縣機關工作、有穩定收入的先生。在那位先生的幫助下她離開了十分艱苦的農村,到縣裡一所小學任教,這對於當時的她無疑於一步就從地獄走到了天堂。畢竟她還只是一個年僅22歲、不諳世事的女孩啊,她對人生、前途的認識還相當幼稚,不能把握自己的情感,更無力主宰自己的命運。
幾個月後,我離開民兵團宣傳隊調往重慶工作,臨行那天,曉南從縣城專程趕來送我,什麼也沒說。汽車開動的時候,我們揮手告別。不知為什麼,我感到在曉南淺淺的微笑背後有幾分悽楚。看著她遠去的身影,我回憶起跟她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心裡有一種不可名狀的失落。
四
1976年夏天,曉南出人意料地來到我的家,我感到很驚詫。她還是那樣光彩照人、風韻綽約,還是那樣的開朗。我當時真不知道該和她談些什麼。我已於1974年結婚,生活得很平靜。寒暄之後,我們互相介紹了一下自萬源一別後的情況。她臨走時約我第二天再見面,說想再跟我談談,並告訴我她常常從朋友那裡打聽我的情況。
第二天我如約到了朝天門客運大廈的大門前,這是我們以前經常幽會的地方。曉南已經早早地在那裡等我了,我們的約會從來都是準時的。她穿著一件淡雅的印有小花的襯衫和一條裁剪得體的淺色裙子。沒有什麼約定,我們便默契地沿著十年前我們經常喜歡走的路線從朝天門到道門口再向菜園壩方向走去。走到望龍門纜車處我們停下來,坐在長江的貨運碼頭邊,面對鬱鬱蔥蔥的南山和滔滔的長江我們觸景生情無限感慨,日夜奔騰不息的長江水啊,帶走了我們多少難忘的日子!
沉默良久,曉南打破沉寂,用一種異常平靜的口氣告訴我,這些年來她過得並不幸福。她說她的丈夫開始很愛她,很寵她,但是新婚不久她發現自己跟出身工人家庭的丈夫在性格、情趣以及對生活的理解上大相徑庭,肉體的歡愉並沒有給她心靈的幸福,夫妻之間的爭吵發生了,而且頻率越來越高,以致發展到一種無法收拾的境地,除了離婚沒有其他解脫痛苦的途徑。她周圍的同事和朋友都不理解她的想法,因為那先生是一個國家幹部,而且在小小縣城人緣也不錯,一些人甚至指責曉南“忘恩負義”。但從她的談話中我感到她去意已決。在當時中國的清教社會里離婚是極不光彩的事,更何況曉南是一個女人,她要主動提出離婚這需要多大的勇氣啊!
當曉南征求我的意見時,我傻愣愣地無言以對。而那時我妻子已經懷孕,兒子就要出生了,我完全沉浸在即將當父親的喜悅裡。“飽漢”不知“餓婦”之飢,我沒有認真體會曉南的話,也的確不瞭解她婚後的生活以及她的丈夫的為人。但有一點我很清楚:那就是我不能勸她不離婚,因為我知道她確實生活在痛苦中;我也不能勸她離婚,因為如果離婚,像她這樣一個遠離家鄉舉目無親並且還帶著一個兩歲左右兒子的女人,在那個偏遠的小縣城會是多麼的無助。但除了勸她“慎重考慮”之外,我又能做什麼呢?
許多年以後我才從我的一個曾經在萬源青花鐵廠工作過的好朋友那裡得知,曉南大概是在1974年結的婚。這位朋友因工作原因經常要到萬源縣城去,每次去都要到曉南那兒坐坐。但後來經常碰見他們夫妻爭吵不休,家庭氣氛不很和諧,就再也不好去看她了。有一次這個朋友又到萬源縣城開會,在路上遇見了曉南,曉南一定要他去家裡坐坐。我的朋友告訴了她自己的顧慮之後曉南才道出了箇中緣由。她說她跟丈夫的關係確實不好,因為她的丈夫跟另外一個年輕女子經常攪到一塊兒。發現自己丈夫的外遇之後,她把遲歸的丈夫關在門外,迫使她丈夫到其他同事家借宿。奇怪的是,這也竟成為曉南的過錯,連萬源縣的一些知青也指責她無情,但她卻不能向任何人傾訴。曉南的第一次婚姻就這樣結束了。
五
1978年,我兒子一歲多了,每天下班回家和兒子在一起嬉戲、玩耍是我最愉快的時候,他會不停地叫我爸爸,纏著我講故事、搭積木、開小汽車,直到他玩累了、睡覺了我才開始開啟書,坐到書桌邊伏案工作。我的日子就這樣流過。
一天,我一個人在家,曉南又來了。和她一起來的還有一個和她在萬源縣工作的女知青。她這個朋友是一個熱情、爽朗的人,坐下後沒說兩句客套話便直截了當地說:“你們兩個有什麼該說而沒有說完的話要繼續說完,有什麼該做而沒有做完的事也應該繼續做完。”說完後便獨自起身離去,剩下我和曉南相對而坐。
一陣沉默之後曉南又開始向我述說她的不愉快,並告訴我她曾經在新婚之夜痛哭了一場。我清楚她的來意,也非常同情她的處境。有了婚姻的經歷,我對男女之間的所有隱秘已經瞭如指掌;而曉南雖然三十歲了,卻仍然顯得年輕,比起十年前的那個少女,更多了幾分女人的豐滿和魅力。我尤其沒有想到,十年前我跟曉南之間那段柏拉圖式的戀愛對她竟是那樣的刻骨銘心!一時間,我產生一種想擁抱她、愛撫她、給她人間溫暖、撫平她心靈創傷的男性的衝動。但是閃念之後,我壓抑了自己的感情,沒有去償還青春的宿債。我言不由衷地勸她,走好自己的路。其實我也知道,這種勸慰是何等的無力,但除此之外我沒有任何辦法。
列夫·托爾斯泰說過:人有兩面性,當理性的一面佔上風時他就是一個理性的人,而當動物性的一面佔上風時他就是一個動物性的人。我們當時所受的教育使我們傾向前者,特別像我們這些當時被稱為是“黑五類子女”的人,做人行事更是謹小慎微,很多正常的事我們都不敢去做,常常處於一種自卑而無奈的境地,何況那時我們都已經分別為人母、為人父了。因此,我在雷池邊上駐足不前。我希望保持我們之間純潔無暇的初戀的美好回憶。於是曉南帶著失望,默默地離開了我家。
80年代初,我在大學上學,圓我的讀書夢,曉南又來了。她已經又結婚了。我非常高興,衷心地祝福她,我希望她過得幸福。當我送她走時,我感到她用一雙迷濛而又失望的眼睛望著我,直到汽車遠去。又過了幾個月,我收到她一封信。寥寥幾行字道出了她埋藏心底多年的秘密:“益庭,我一生中犯過不少錯誤,我都沒有任何後悔。但是我犯了一個最大的、無法挽回的錯誤,我背棄了你,為此我抱恨終身。”
沒過多久,我突然意外地接到曉南姐姐的來信,這是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給我寫信。於是我匆忙趕到了她家,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心中忐忑不安。一進門我看到了大姐一臉的凝重,她開口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曉南不想活了。我從大姐處得知,她與她的第二個丈夫關係非常糟糕。
原來曉南第一次離婚成了萬源縣城裡街頭巷尾很多人議論的話題,使她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擊,還有人謠傳她已經在重慶找到了如意郎君,因此拋棄了A先生。為了證實自己的清白,曉南倉促地又在當地與B先生結了婚。據說B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學教師,妻子剛剛去世,帶有一個養子。當地報紙還曾專門報道過他如何體貼關愛患病妻子的事蹟。曉南因此傾慕敬仰他,希望從這個男人那裡得到愛撫,希望她的兒子能得到更好的教育。哪知事與願違,他們生活在一起後她才覺得無論在生活上、性格上、在對待她最心愛的兒子上丈夫都不能使她滿意。俗話說期望越大失望就越大,他們結婚才短短的一年,就已經到了互不相容的狀態,甚而發生打架摔東西的情況,家裡值錢的東西幾乎都砸壞了。她的滿腔熱情和希望又一次遭受了無情的打擊,她一定絕望到喪失理智的地步。
大姐的一番話令我窒息,我怎麼也想不到一個當年天真爛漫對生活充滿嚮往和追求的女子在短短的十多年以後竟想結束自己的生命,這不禁讓我想起當年熱戀中的我曾寫下的幾句小詩:“一個長辮子姑娘,把一個青年愛上,她那含情脈脈的雙眼象玉石一樣晶亮。青年拉得一手好琴,美妙的琴聲令人神往。姑娘長於舞蹈,當她翩翩起舞的時候就像孔雀展開了翅膀。他拉他心中的歌,她跳她情中的舞,兩顆燃燒的心啊,應著歌聲飛揚,隨著舞蹈盪漾。啊,生活多麼美好!”大姐希望我能勸慰她,但是我知道無論我說什麼對她來說都是蒼白無力的,眼看曉南在命運的泥沼裡不能自拔,我完全無計可施。
後來,我也從萬源青花鐵廠的朋友那裡得知,曉南經常與B先生髮生毆打後帶著傷痕到他那裡小住。原來她的生活是如此艱難。曉南母親是重慶鐵路分局的老職工,知道女兒的處境之後,千方百計把她從萬源調到了達縣鐵路子弟校。又過了一年,她跟第二個丈夫離婚了。那時她才三十四歲。以後就再也沒有結婚。
1993年,我生病住院,我的那位萬源朋友來看我,那時我也離婚近兩年了。他說曉南已得知我離婚的訊息,託他帶來口信明確地提出希望我能跟她結婚。據我朋友說,他回重慶前一天,在達川市跟曉南長談了一夜。曉南囑託他一定要把她的話捎帶給我,並且讓這位朋友轉告我,那些年她已經攢下了一大筆錢,希望用自己的辛勤勞動所得來彌補年輕時的過失。那時她才四十四歲。但是那時我已經跟現在的妻子確定了關係。我拒絕了曉南的表示,她又一次失望了。
六
在人生的漫漫長路上,我們這一代人就這樣跌跌絆絆一路走來。曉南的命運尤其坎坷,恰好印證了“紅顏薄命”這句老話。她曾親手埋葬了自己的初戀,爾後又在不斷地追求夢想中遭遇一次又一次的打擊。儘管她努力,她抗爭,她想得到幸福,但她始終不能擺脫那張用世俗與偏見編織成的大網。最後讓病魔為她悲劇式的人生劃上了句號。
我曾經怨恨過曉南。但是經過了人世的種種艱辛,特別是知道她那兩場不幸的婚姻之後,我不僅原諒了她當年的作為,而且為她感到深深的惋惜。她那陰差陽錯的一生不正是那個陰差陽錯的時代的產物嗎?我知道,由於她的勇敢和無助,她在許多正經和心滿意足的人的眼裡是個“不道德”的女人。但我不以為然。一隻鞋究竟是不是夾腳只有穿鞋的人自己才清楚。有些人特別喜歡討論別人的隱私,熱衷於道德判斷。我知道自己不配指責曉南。我還知道,當列夫·托爾斯泰寫完《安娜•卡列尼娜》後,從書房裡衝出來,老淚縱橫,邊哭邊喊“她死了!她死了!”三十年前我怎麼也不懂老托爾斯泰對安娜的痛惜之情,今天我算是完全明白了。
願上天那無邊的慈愛跟曉南的靈魂同在!
作者:張益庭,男;1964年高中畢業後下鄉到四川省鄰水縣當知青。1972回到重慶。此後長期在中學執教。曾擔任重慶南岸區第四屆政協常委、第五屆政協委員和南岸區人民法院執法廉政監督員。已退休。
來源:老知青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