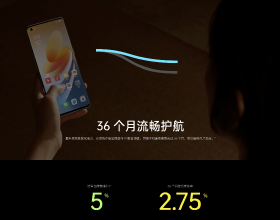英麻/文
無論在未來你以何種方式談起《進擊的巨人》,這部動漫都難逃在“神作”與“爛尾”這兩個極端評價之間搖擺的命運。這部漫畫的創作者是日本漫畫家諫山創,自2009年漫畫開始連載到2021年4月份動畫完結,曾經帶給人無數的驚奇、悲憤與感動,也許之前人們對巨人的故事有多熱愛,就對之後潦草收尾的結局就有多憤怒。當漫畫進入“王政篇”與“馬萊篇”,主題不再是熱血少年漫慷慨激越的風格,而是轉入到更為現實與殘酷的政治與家仇國恨的主題中,最終由陪伴著讀者一起成長的男主角艾倫·耶格爾“黑化”發動地鳴滅世達到高潮。漫畫家諫山創所謂的早就成熟在胸的結尾,則引起了巨大的爭議——艾倫為了拯救自己所屬的族群艾爾迪亞人發動的“地鳴”,不惜殺害牆外80%的無辜人類,“地鳴”是否是唯一的選擇?而被記憶與歷史所困擾的艾倫,最終無可奈何地選擇了命運唯一的歸宿,甚至不惜扭曲過去與未來,獻祭自己的母親以達成目標,為了民族的生存成為不擇手段的惡魔,將整個世界變為了地獄。這種人物塑造是否與之前諫山創所追求的主題“自由”相違背?曾經以追求自由為己任的艾倫,又為何變得陷入到命運的深淵之中變得“不自由”,他的負擔與抉擇的困難又來自哪裡?
歷史與記憶的囚徒
在漫畫創作早已成為工業產品流水線的一環的日本,《進擊的巨人》被譽為天才之作。初出茅廬的漫畫家諫山創憑藉的不是精緻的畫工和細膩的分鏡,而是對於人物性格的刻畫以及不斷反轉、鋪陳的情節轉折。我們看得見每一位人物的抉擇,以及隨之而來的痛苦。然而,所有情節推動的方向,則是諫山創不斷提及的“自由”。艾倫與調查兵團要衝破高牆的拘禁,消滅巨人享有真正的自由,不再貪圖家畜般被圈養的安逸,在牆內要打破權力對思想的壟斷,戳破被美化的現實政治,將被篡改的歷史真正展示給公眾。如果說第一卷至第二十二卷是熱血激昂的少年漫畫,那麼當故事推進到“馬萊篇”時,主題就變得現實乃至沉重了許多。調查兵團發現的真相——族群之間無休止的戰爭與迫害,帝國與弱小民族之間不斷燃燒的敵意,加害者和受害者的身份的雙重轉換,如同人類歷史階段的翻版。“馬萊篇”中的艾倫以巨人之姿,向普通人大開殺戒時,與漫畫開篇時鎧之巨人和超大型巨人攻破瑪利亞之牆形成了鮮明對比(諫山創也因此被許多粉絲稱之為“對稱狂魔”)。讀者不得不接受這樣的事實,自己親眼見證了其成長與磨礪的男主人公,在作為敵方馬萊帝國平民眼中和第一季中壓迫感十足的巨人一樣的代表著暴力統治的惡魔。因此,我們無法把巨人的故事概括為人類對抗超自然力量的巨人,作為交戰雙方的馬萊和帕拉迪島同樣在暴力和仇恨的漩渦裡沉淪。艾倫與敵人萊納,並不是簡單的善惡之分。他們同樣揹負著難以和解的來自歷史的疲憊和對無休止的戰爭的質疑。但他們二者卻難以握手言和。《進擊的巨人》的底色是悲觀的,因為我們無法相信調查兵團是以熱血沸騰的戰鬥與犧牲為結局的,他們最終陷入了和現實一樣的修羅場。
在“馬萊篇”中,馬萊帝國的平民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得淳樸、善良,卻在軍國主義的煽動與動員下對於艾爾迪亞人極度仇視,並視之為“島上的惡魔”。巨人在漫畫中是一個重要的隱喻,注入始祖巨人脊髓液的艾爾迪亞人會無意識地變成沒有記憶和人性,只知道吃人和破壞的無垢巨人。他們是被人類刻意製造、批次生產而且自相殘殺的戰爭機器。在二十世紀開頭的歷史中,我們不難發現平時溫和、馴順富有教養的公民,可以在足夠的動員下瞬間成為國家意志的化身,並在身邊的敏感族群區別出國家體制中的異己,並變成拋棄人性的惡魔。漫畫中的馬萊帝國甚至刻意篩選出具備戰鬥天賦的艾爾迪亞人進行培養,並使其得以繼承巨人之力可以永遠地成為順服國家體制的機器。他們晉升的方式只有不斷戰鬥,展示出自己對敵人的仇恨,才可以成為“榮譽馬萊人”。帝國與人民經常彼此塑造,馬萊帝國選擇軍國主義與仇視艾爾迪亞人的政策時,人民無意識地成為了幫兇。如同馬萊帝國的實際掌權者威利·戴巴所言,是馬萊人自願使得國家成為了軍國主義。這已經不止是對日本近代史的“隱喻”了。德國曆史學家梅尼克稱這種集體情緒為“群眾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在大眾社會建構不完善,以及民粹主義難以馴化的國家中,這種情緒經常由把持國家權力的一小撮人傳染到整個社會。
作為讀者我們不自覺代入主人公的視角,把故事開始時主人公與調查兵團的一系列戰鬥與探索看作是對於人類既定的命運的抗爭,可創作者精心設計的陷阱則讓讀者幻滅。在巨人的霍布斯世界下,馬萊帝國和帕拉迪島都被歷史和憎恨所撕裂,康德式永久和平的理想被無情地嘲諷,躍入民族主義階段的帕拉迪島不得不為了適應弱肉強食的政治秩序走上軍國主義的道路。這也是巨人的結局因何譭譽參半的原因,背後的邏輯之現實像極了現實生活種的法則。馬萊帝國對於作為異己存在的艾爾迪亞人所進行的人體試驗,以及帕拉提島內耶格爾派對於群眾運動的煽動和對外戰爭的叫囂,都讓人聯想到民粹主義在二十世紀肆虐的歷史。正如一戰前的德國哲學家保爾遜對於德國戰前的政治狂熱氛圍的精確診斷:一種過分激情的民族主義已經成為了對歐洲一切民族的十分嚴重的危險;他們正因此面臨著喪失人類價值感的危險。民族主義被推到頂峰,就像宗派主義一樣也會消滅道德的、甚至於邏輯的意識。
在一個架空的世界中,諫山創並未給我們一個超越現實的美好結局,如同真實的世界一樣,高牆破碎後的帕拉迪島和牆外世界陷入了無休止的征戰,艾倫·耶格爾不惜滅世成為罪人想要拯救帕島並使得巨人之力消失,他的犧牲與獻身也成為了徒勞的奮鬥。也許整部作品真正的毀滅性力量並非是巨人之力,而是受困於歷史與記憶中的人們對於他者的非人化。曾經的受害者尋求真相與記憶並非為了和解與救贖,只為了理直氣壯地成為加害者。與其說這是諫山創想要“傷害讀者”的滿滿惡意,不如承認這種結尾來自於他洞察了世界史上的無數悲劇,以及難掩地對於現實的失望。《進擊的巨人》滲透了諫山創對於政治與公共生活的悲觀的理解——“王政篇”揭露了國家內部統治的藝術,掌握了刪改記憶的權力就擁有真正意義上的最高的權力。“馬萊篇”和“地鳴篇”則更為直接地表達了作者對於今日世界政治結構性暴力的無奈,這裡沒有善惡與是非之分,弱小民族永遠擺脫不了被支配與被仇恨的命運,只能在毀滅的陰影下重複之前的命運。我們無法要求作為一個漫畫家的諫山創可以如同政治學者般為今天的國際體系尋找出路,或者更新政治倫理展望未來,更無法奢望他在充滿著怨恨和暴力的政治遺產的世界中,對無法預期的未來感到樂觀。然而不管我們如何評價《進擊的巨人》的結尾,都難以逃脫諫山創在其中設定的種種道德難題:今天的我們是否應該揹負歷史上屬於先輩的國家罪責?在民族神話的編織越來越巧妙同時也更加潛移默化的今天,我們能否逃離其中,並找到自己的位置?又或者在歷史和記憶中糾纏著的我們,能否為這個被民族主義所撕裂的世界賦予新的意義?諫山創的回答也許是悲觀的。作為讀者的我們也許要給出更為樂觀的回應,正是因為世界的敗壞,行動者才更有價值。就像調查兵團的同袍不希望埃爾文兵長和韓吉等人壯烈的犧牲被虛擲浪費一樣。
自由和命運的終點
《進擊的巨人》前半部分的關鍵詞是“自由”,所有的情節都沿著自由的方向推進。主人公艾倫對於自由的理解是將巨人趕出世界,讓人類不再受到高牆的約束,艾倫在與巨人的戰鬥中也成為了人類最後的希望。此時他的自由便意味著讓自己的選擇決定歷史的走向。他的同伴阿爾敏對於自由的理解是突破高牆的束縛,看到大海並走到對岸,理解世界的真實面貌。調查兵團團長阿爾文的自由則是滿足自兒時以來的夢想,讓被王政府隱瞞、篡改的歷史得以重新浮現,真正瞭解自身族群的命運和未來。此時,《進擊的巨人》裡的“自由”的概念,符合的是黑格爾的定義:真正的心靈自由因而不僅僅在於做或者選擇一個人所希望的東西,而是在於成為一個“意願著自由意志的自由意志”。對於他們三者以及他們所代表的調查軍團而言,自由的含義早已成為一種信仰,戰鬥和探索的目的在於擺脫人類被高牆圈養,追尋被權力隱瞞的人類真實的歷史。然而隨著劇情的深入,自由的象徵也逐漸成為一種重負,當我們陪伴著主人公一起戰鬥,一起經歷戰友的生離死別,一起發現世界殘酷的真相,自由不僅是承擔起真實的重量,也在於與寄託了共同記憶與信念的逝者一起生存下去。
哲學學者包偉民曾經把自希臘以來的政治學分為強者政治學和弱者政治學,他認為這種差異正是區分古今政治哲學觀念之爭的分野。在他看來,強者之強在於是否具有堅定的血性,能否透過暴力來實踐道德理想,發動戰爭或準戰爭保護家人。而弱者期待於強者的,在於“主權者運用強大力量為他們伸張正義,抵禦傷害,提供安全保障。”在這種視角下,我們不難理解艾倫對於自由的理解是如何形成的,在經歷母親被巨人吃掉的慘痛悲劇後,他決定加入調查兵團,保護親人與朋友,為父母報仇。弱者與強者之分就在於弱者必須在強者的羽翼之下,達到自足的存在。我們可以把艾倫加入調查兵團看作他從弱者向強者的邁進,他用合法暴力的方式介入到權力和公共生活中,渴望擺脫自己的弱者性(相對於“人類最強戰力”的利威爾兵長和艾爾文團長,艾倫依舊屬於弱者,需要保護。在複雜的政治權力鬥爭中,調查兵團同樣是弱者)。而在“王政篇”之後,獲得了始祖巨人之力的艾倫,毫無疑問成為了牆內反抗牆外勢力的希望。此時,艾倫對自由的理解已經變成充當命運的主人,將自己的意志貫徹到歷史的程序之中,從而帶領族人擺脫被宿命(尤彌爾之力)詛咒的命運。同樣,這種強者的自由帶來的是對於他者生命的踐踏以及對於秩序的破壞。也因此,當艾倫伸張自己的自由意志時,勢必對他人的自由造成危害。這也使他對自由的理解迥異於渴望與世界交流達成和解的韓吉和阿爾敏等人。
如果說具有洞悉歷史以及毀滅世界的巨人之力的艾倫是政治強者,那麼站在人道和希望與牆外彼此理解的韓吉和阿爾敏則是德性上的強者。阿爾敏與韓吉對於自由的理想是世界主義的,艾爾迪亞人只有在世界中成為一個被接納和自由交流的自由人,帕拉迪島作為現代國家的崛起才是有意義的。當艾倫滅世陷入癲狂時,韓吉為了阻止地鳴為夥伴爭取時間獻出了生命,阿爾敏與超出自己力量數倍的艾倫展開了死鬥。他們理解世界的殘酷卻不讓自己與之一起沉淪,相信傾聽與和解可以塑造新的世界。他們的德性源自於人類價值面臨危機與挑戰時挺身而出的勇氣。
希臘悲劇中經久不衰的主題就是這兩種強者之間的對立和衝突。終章的“帕拉迪島分裂篇”和“地鳴篇”中的作為生死之交的阿爾敏和艾倫大打出手展示了這種衝突。強者之間的鬥爭在於爭奪對於“正義”的理解,艾倫的正義在於改變民族被囚禁和獵殺的命運,將既定的命運真實的伸張,阿爾敏的正義則認為無差別的屠殺無法解決世界間的仇恨,只會帶來新的地獄,人類的未來在於和解和寬恕。納斯鮑姆在《善的脆弱性》中認為強者如果不想成為弱者和庸眾的一部分,就只能付出暴死的代價。於是,艾倫與調查兵團的戰友的矛盾是無法調和的。弱者在意的是現實生活和其中具體的感受,正如在漫畫137話中,阿爾敏與艾倫的同父異母的兄弟吉克·耶格爾的一番對話中一樣,阿爾敏不接受地鳴,他要守護所珍視的童年在黃昏中和夥伴們一起奔跑、在下雨天自在讀書的午後、喂松鼠吃松果的瞬間。不甘淪為戰爭機器的吉克則回憶起來兒時與長輩拋接棒球的時刻是他人生中為數不多的幸福時刻。
也正是這種瞬間,最終使吉剋意識到生而為人的目的不再是繼續揹負歷史的重負與民族的存續,人類透過交流而產生的溫情和連線,也足以激發沉淪與墮落的人性再次閃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發現人類歷史在步入現代之後,代表著強者逐漸隱匿,弱者不斷湧現登上舞臺。因為艾倫式的強者伸展意志,展現作為英雄的自由和驕傲,帶來的往往是專制和對於他人自由威脅。
當劇情轉入“馬萊篇”之後,獲得始祖巨人之力得以預見未來並洞悉過去的艾倫開始了“黑化”的過程。他開始對馬萊的平民大開殺戒,支援他的年輕軍官形成了耶格爾派並迅速完成了國家的總體戰式的戰爭準備,最後他不惜開啟“地鳴”殺死島外80%的人口成為世界的惡魔,迫使自己之前調查兵團的同伴殺死自己,使他們成為拯救世界的英雄,以此達成帕拉迪島和世界的短暫和平。更為殘酷的是,艾倫已然得知自己與國家的宿命已經被鎖定,甚至不惜以始祖巨人之力穿越過去,以現在的自己驅使巨人吃掉自己的母親,甚至迫使自己的父親為了繼承巨人之力殺害無辜的兒童。艾倫並未使這個世界發生改變,甚至獻祭自己的生命與人格使之成為了一場虛無幻滅的戲劇。這也使得艾倫的抉擇成為了一種存在主義式的悲劇——自由遮蔽了命運的不可逃遁性,人的之為存在和自在存在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
羅素認為希臘悲劇的核心在於“在荷馬詩歌中所能發現與真正宗教情感有關的,並不是奧林匹克的神祗們,而是連宙斯也要服從的‘運命’、‘必然’與‘定數’這些冥冥的存在。”如果說希臘悲劇的起源來自於冥冥之中的宿命選擇了克洛諾斯、宙斯、俄狄浦斯,使他們和所代表的自由意志會在不可逆的命運面前一敗塗地。《進擊的巨人》則表現出與希臘悲劇相同的質地,故事中的每一位主人公同樣也是被命運所選擇,他們奮力戰鬥,自以為代表的是正義與希望,卻難以超脫命運的詛咒,成為他者眼中的惡魔。透過“工具人”艾倫人生悲劇地徐徐展開我們看到了一個殘酷與悲觀的世界,然而這個被暴力和仇恨吞噬的故事裡,諫山創依舊為我們帶來了無數動人閃光的瞬間——主人公們在命運面前敞開自己的勇氣與德性,揹負亡者的期待和生者的希望,一次又一次地向虛無的歷史和未來進行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