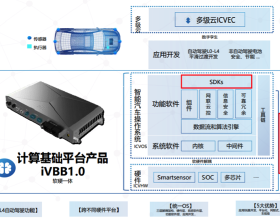明朝正德年間,河南新野縣一個婦人清晨叩響了里長家的大門。里長睡眼惺忪地開啟門,婦人哭喪著臉對他道:“我家丈夫兩天未回,他是不是失蹤了?我很擔心。”里長一臉的不耐煩:“兩天而已,他不是去別的地方了?你著什麼急?說不定過兩天,他就自己回來了。”說完,啪地一聲將門關上了。
過了五日,婦人再次找到里長:“我家丈夫已經七天沒回來了,你能不能帶人找找去?”七天沒有回家,又沒有去外地,里長心裡不由地咯噔了一下,喊來十幾個縣民,去到縣城及城外四處搜查。
縣城裡所有客棧都不見婦人丈夫的身影。在城外荒山上,一棵陰密不透光的大樹下,有人發現了一處地方有些奇怪,四周不見落葉,只有這一處地方堆滿了枯葉,他輕輕地按了按,還十分地鬆軟。那人刨開樹葉,一個土坑赫然呈現,他連忙發出訊號。眾人從四周趕了過來,舉起火把,往坑裡一照,裡面竟躺著一具男屍!
里長一見屍體,腦袋都大了,吩咐幾個人守著屍體,自己則帶了幾個人前往縣衙報案。
新野知縣蘇運維個頭不高,全身圓滾,一雙小眼,兩頰通紅,就像剛喝過酒一樣,從面相上看不像是一個精明之人。
聽到里長的報告,他嚇得從椅子上跌落了下來,帶著衙役和仵作就去了事發現場。
衙役們用繩子將屍體從坑裡拖上來,婦人一見,撲上去嚎啕大哭。衙役將她拉開,仵作上前檢驗屍體。
蘇知縣搖頭晃腦地看著婦人,讓她將丈夫失蹤的經過詳細講述一遍。
婦人姓苗,死去的人正是她的丈夫鄭炎青。兩人成親後,鄭炎青外出經商,盈利頗豐,雖稱不上富貴,但也算當地的小康人家。
七八天前,鄭炎青的好友李冬括找上門來,請他出去喝酒。
李冬括與鄭炎青相識十餘年,兩人來往密切,猶如親兄弟。見李冬括邀請,苗氏也就放心地讓丈夫出去了。
奇怪的是,從那天晚上出門後,鄭炎青就一直沒有回過家,音信全無。
苗氏也曾讓人去李家尋人,可李冬括卻說當天晚上喝完了酒,兩人便各自回家了,自己也不知鄭炎青去了哪裡。
苗氏一等再等,等了兩天,不見人,去往裡長家報信,可里長讓她再等,她又等了五天,還是不見人影,遂又去了里長家。里長感覺事態嚴重,帶人四處尋找,沒想到在城外的這座荒山找到了丈夫,卻已經是一具屍體了。
馬氏顫顫巍巍地說完,又開始哭起來,整個人哀慼得不行了。
蘇知縣問道她:“你說你丈夫的朋友叫李冬括,他是做什麼的?”
馬氏搖了搖頭:“他沒有什麼正當的營生,偶爾給人打打零工。他這人力氣很大,僱主都很喜歡他。但他賭性太大,兜裡有幾個錢就想著去賭,所以每份工都幹不長。”
蘇知縣又問:“那他和你丈夫經常談些什麼呢?”
“天南地北地閒扯,有時還借錢。”
這時,仵作已經驗完屍,走過來向蘇知縣回稟道:“死者脖子上還繫著麻繩,也有明顯的勒痕,顯然是被人勒死後拋屍在此的。”
蘇知縣查看了屍格,又親自走到屍體旁,剛蹲下來他便大聲喊道:“唉呀”,用手閃了閃四周的空氣,然後緊緊捂住自己的鼻子。
麻繩約有大拇指粗,死者脖子被麻繩結成的圈套套住,脖子後方有一個結,結下面的繩子自然垂下。
蘇知縣撿起左右兩邊的繩索,左看看,右看看,只聽見他嘴裡輕輕地說了聲“哦”。
現場勘驗完畢,一行人打道回府,蘇知縣令人帶將李冬括帶到縣衙。
不多時,李冬括被帶到,此人1米7左右,長得五大三粗,特別是雙臂,粗壯有力。
蘇知縣清了清嗓子,問道:“堂下何人?”
李冬括上前一步回道:“小人李冬括。”
“哦,你認識鄭炎青嗎?”
“小人認識,那是我的好朋友,我們幾乎是從小一起長大的,親如兄弟。”
“那鄭炎青死了,你知道嗎?”
“啊?”李冬括一臉不可置信的樣子:“他,他是怎麼死的?”
蘇知縣哼了一聲:“據馬氏說,七八天前的晚上,是你請他出去喝酒的,你將你二人喝酒時發生的事如實道來!”
李冬括顯然被鄭炎青的死弄得愣了神,半天后緩過勁來才開口說道:“那天晚上,我請他去福如酒樓喝酒。我們以前也經常去,就是朋友間敘敘情,這天也不例外。大約亥時左右,我們從酒樓出來,各自回家了。當時他喝得有點醉,我本想送他回家,但他說僅幾步路遠,堅持不要我送。我看著他走遠了,才掉頭回了自己家。”
李冬括一邊說,一邊自然地用左手比揮著。
蘇知縣看著他的一舉一動,突然問道:“你是左撇子嗎?”
李冬括一聽這話,趕緊將左手縮了回來,連聲否認道:“不是不是,小人右手傷了筋骨,所以用了左手。”
蘇知縣又哦了一聲,繼續問道:“聽說你經常找鄭炎青借錢?”
李冬括雙手並在雙腿側,回道:“偶爾有過幾次,但我借的錢不多,每次就幾兩。”
“那總共借了多少兩銀子?借的錢你還過沒有?”
聽到這個問題,李冬括有點不好意思了:“加起來就六七十兩吧。每次我說要還,可我兄弟說不急,讓我先用著。”
蘇知縣點了點頭,表示知道了,然後又說道:“這樣吧,我們還要去核實相關情況,你先將今天的口供籤個字,畫個押。”
說完,公差將寫好的供詞遞到面前,李冬括本能地伸出左手,一想不對,又伸出右手,歪歪扭扭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退堂後,蘇知縣派公差去福如酒樓找夥計打聽當晚的情形。誠如李冬括所說,二人申時到的酒樓,亥時離開,期間,兩人相談甚歡,並沒有什麼不合。
又找李冬括所在裡的里長打聽,得知李冬括父母雙亡,只給他留下一間破草房。貧困如此,可他卻生性愛好賭博,無一日不賭。十賭九輸,為此輸盡了家產,還借了不少外債。曾有幾次,被債主逼債上門了。
五天過後,蘇知縣重新開堂審案,李冬括再次被帶上了堂。
李冬括剛一站定,蘇知縣猛地一拍驚堂木,喝道:“李冬括,本官已經查明鄭炎青死亡真相,眼下給你一個贖罪的機會,將你犯案的經過如實說來。如若不招,定當重刑伺候!”
李冬括當即傻眼了,一下跪倒在堂下,大聲喊冤:“大人,小人真的沒有殺過人啊,請大人明鑑!”
“還敢狡辯,來人,重責二十杖!”
左右齊齊上來,按住李冬括,掄起棍棒就打。幸得李冬括身體健壯,二十大杖雖有些疼痛,但還能堅持住,搖搖晃晃地爬起來。
二十杖打完,蘇知縣又問:“你招是不招?”
李冬括哭喪著臉:“大人,你再打,小人也沒有說謊啊!”
“那就再打!”蘇知縣說著,從籤筒裡抽出一支令籤,正要往下扔時,門外突然傳來一陣喧譁聲,一隻牛從門外闖了進來,朝著蘇知縣猛衝過來。
牛主人拿著繩子在後面緊追不捨,卻始終追不上發狂的公牛。
蘇知縣嚇得一身冷汗:“誰,誰能拿下這頭牛,本官重重有賞!”兩旁的衙役一個說我腳前日崴傷了,一個說我手疼,拿不了重物,個個爭先恐後地往柱子後面躲,誰也不肯站出來。
已經鑽到公案底下的蘇知縣朝著李冬括喊道:“你如果能拿下這頭牛,本官馬上放了你!”
李冬括聽見這話,當即站了出來。他朝牛衝過去,一手抓住一隻牛角,死死地往後抵。牛奮力向前拱,為了使盡全力,李冬括也調換了一個慣用的姿勢,左腳在前發力,右腳在後支撐,用力和牛對抗著。
一人一牛相峙了數分鐘,那牛被抵得連連後退,眼看久攻不下,也就洩了力氣。牛主人趕緊上前,將繩子牢牢系在它的脖頸上,拖了出去。
李冬括拍了拍衣服,重新面對著蘇知縣。蘇知縣也從公案底下爬出來,抖了抖官服,端坐在椅子上。
李冬括笑著對蘇知縣說道:“大人,小的已將牛制服,大人剛才說的話,可算數?”
沒想到此時的蘇知縣一改剛才的膽怯,喝令左右道:“左右來人,將殺人兇手與我拿下!”
李冬括一臉不解地望著蘇知縣。蘇知縣冷笑道:“鄭炎青是被左撇子殺死的,你正是殺死他的左撇子!”
原來蘇知縣看到鄭炎青脖子上的繩索,磨損得十分厲害,推測兇手是力大之人。一般人慣用右手,通常右側力氣更大,而左邊那根繩索磨損得更嚴重,表明兇手是慣用左手之人。
第一次審案時,李冬括習慣性地用左手配合言語,蘇知縣心中有了幾分懷疑。在他提出自己的疑問後,李冬括突然改用右手,動作顯然沒有左手來得自然,簽字也不甚流暢。
二次審案前,蘇知縣讓公差找來一位家中有牛的農夫,讓他在審案時,將牛帶到公堂外,激怒它,並讓他衝進來。
左右官差藉口躲避,順理成章地給了李冬括展現的機會。
為了控制住牛,李冬括習慣性地用回了左手、左腳發力。在突發之下的反應,正是人最自然不過的反應,蘇知縣確認了自己的懷疑。
聽完蘇知縣的一番解釋,李冬括無力狡辯,一五一十地交代了自己殺人的經過。
李冬括與鄭炎青確實是好朋友,藉著朋友這層關係,他經常找鄭炎青借錢。這天晚上請鄭炎青出去喝酒,也是為了再次找他借錢。
酒樓里人多,李冬括不便開口,遂趁著出來後,提出了借錢的請求。
可沒想到,鄭炎青卻是一反常態,不僅不借給他,還限他在三天之內,將以前所欠的六十兩銀子還來。鄭炎青知道他愛好賭博,自己一再借錢給他,只是放縱了他,不願再借,也只是希望這個視如兄弟的朋友能金盆洗手,潔身自好。
可李冬括不明白啊。他苦苦哀求,鄭炎青就是不同意,非逼著他還錢不可,還威脅他如果再不還錢,以後朋友沒得做,還要報官。
在明朝時,賭博可是重罪,一旦被人告到官府,輕則砍去雙手,重則關押起來活活餓死。
李冬括擔心鄭炎青真的去告發自己,再加上最近債主接二連三地上門逼債,還恐嚇他不還債就殺人。幾重壓力之下,李冬括崩潰了。
二人一前一後經過一家肉店時,門口正好有一根丟棄的麻繩。李冬括惡向膽邊生,撿起麻繩,打了一個結,從後面套住了鄭炎青的脖子,然後用力,將其勒死。
李冬括將死去的鄭炎青揹回自己家中,將他身上的銀子搜刮得一乾二淨,然後捱到五更時,城門開啟,又將其背到城外的荒山上,挖了一個洞,丟了進去。為掩人耳目,他把四周的落葉圍攏來,覆蓋在上面。隨後偷偷潛回家中,裝作毫不知情的樣子。
等到天亮時,將搜刮來的銀子拿去還了債。
看似粗笨的蘇知縣,卻大智若愚,從繩索的磨損推斷出兇手的顯著特徵,再用言語和突發事件一一加以證實,最終將兇手繩之以法。
李冬括賭博,殺人,數罪併罰,被判以斬立決。
左撇子是慣用左手的人,身體左側的機能開發遠遠強於慣用右手的人,連帶著左手,左腿和左眼都更加靈活發達。投射在某些運動專案上,這類人的表現通常優於別人。
不論是習慣用右手還是左手,都是基因決定的,都不應該遭受到歧視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