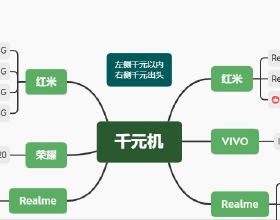<今日頭條>歷史灰塵注:前面我更新完了曾昭掄博士的《滇康旅行記》,下面我們一起去看看大涼山的人文與風光。1941年7月1日,跟隨民國曾昭掄博士和他的“川康科學考察團”出發,看民國時的大涼山人文與風光。本文摘自曾昭掄博士《大涼山夷區考察記》。
如果你喜歡有趣的、不常見的歷史資料,請關注我,我會每天堅持發掘出那些快要淹沒在時間煙塵中的歷史文章。如果你喜歡本文,請點贊、評論、轉發。
純粹地再現一下民國時的學者對於夷人的研究與看法,很客觀地呈現一下過去的資料而已。我覺得民族政策的最終是各民族都走向現代化,不存在優待,也不存在歧視。
美姑
美姑是阿祿家黑夷居住的一座夷村,距烏坡實約三十三華里,為半站路。美姑一名,由於其逼近美姑河而來。其夷音實為“磨古”(Mogu).漢文“美姑”二字,乃系夷名訛音,並無任何其他含義在內。自河濱上望此村,彷彿就在山頂。走到此處,方知至多不過半山。後來繼續前進,乃知它實位近大涼山的山腳。自美姑河濱上爬,經美姑、磨石家,到黃茅埂,兩天半的路程,大體全部是上山路,一直爬上大涼山正脈的緩和西坡,直到山頂黃茅埂為止。
阿祿几几,是本村的領袖黑夷。他的房子,為村中位置最高的一幢。烏坡久博和他家是親戚,到此當然引我們到他家投宿。吳齊倮狗子和他的同伴(就是那位背背一籃梨子的夥計,一位幫他趕豬的吳齊家娃子),也到此處宿下。原來他和主人,也是親戚。
來到此間,時間還早(不過四點多鐘),未到夷人進屋休息的時候。那時主人阿祿几几,在屋前小坪上,背靠著一棵大樹,面對著我們。經過久博與倮狗子介紹以後,他還老半天不和我們說話。睜著一對眼睛,以一種懷疑的態度,注視我們。這時候伴我們來的兩位黑夷,和他嘰裡咕嚕,攀談起來。瞪了一大陣,這位夷酉,方才對我們說了一聲Goonila(夷語“請坐”的意思)。於是我們便在他的對面,席地坐下。同時他也背靠著樹,面對我們坐下。久博和倮狗子,坐在他的兩旁。主人一共有三位少爺,三位小姐。三姑娘在外看羊,那時尚未返家。只有二姑娘在場,幫著招待客人。她將酸湯拿過來。這是主人下午所吃的點心。因為我們來到,特為送些給客人吃的。主人身上帶有幾個梨子,也分些送給我們。另外凡是吸菸的客人,這位小姐跑過去,到每位面前,抓一撮草煙送給他吸。倮夷和別的民族一般,最大的嗜好,是煙與酒。每個黑夷男子以及許多娃子,身上都帶有一隻菸斗。黑夷女子當中,亦往往以吸菸為時髦。女子所用菸斗,有點像以前漢人所用較短的一種旱菸袋。男子所用的,形狀大體類似西洋人所用菸斗。材料則管子部分,系用細竹製成;下面的鬥,或用石頭,或用竹子。石頭菸斗,乃是涼山夷區一種特產,有些相當好看(例如用烏坡銅礦的礦石製成)。
這位二小姐,大約是此處的交際明星。兩耳上垂有很長一串銀首飾,衣領上戴有一隻三排形式的大號銀別針。這些銀首飾,據說全是夷人裡面的銀匠打的。她為人活潑,很會說話。招待客人,尤屬殷勤。我們雖則彼此不通言語,她那種交際花的派頭,一看就很明白。
阿祿几几本人,年紀約有五十歲,他的夫人,仍然健在。這一家人,差不多完全不會說漢話,老主人亦非例外。有人說,這一帶的夷人,往往會說漢話,卻故意不說,藉以自示高傲。但是果你用漢話罵他,他是明白的,而且會想方法來報復。無論如何,這位老酋長不說漢話,使我們不得不倚仗呂贊臣和木家烏七來傳話。呂贊臣愈來愈討厭,老是陰陽怪氣的。人家說了一大篇的話,他只翻一兩句。還是木家比較忠實些。阿祿几几和烏坡烏達一般,頭上也留有“天菩薩”,結成一條小辮。身上披上雙重擦耳窩,外面掛有一枚屯委會頒給的圓形搪瓷獎章,乃是上次張秘書路過此處時所給。坐定以後,他慢慢開始和我們攀談。第一句問的,就是我們認不認識鄧旅長(指鄧秀廷),和他有什麼關係。鄧氏威名震涼山,到處黑夷總喜歡問這句話。我們的回答,總是鄧氏在西昌見過,但是和他並無關係。如果替鄧秀廷說好話,或者承認和他有關係,那麼不測之禍,馬上就可臨頭。阿祿几几還問我們,是不是從馬烏達家來,他的病勢如何。夷人最怕傳染病,所以特別要問此事。後來又問,我們身上,是不是帶有銀子,不然何以買吃的東西。生夷究竟不同,這些事喜歡問三問四的。
在屋前小坪一直坐到天快要黑,主人方始照例將我們請到屋子裡去坐。這家黑夷,房子特別寬敞。鍋莊用三塊很規則的大石頭,上端向裡彎曲。石頭表面,刻有相當考究的圖案花紋。當晚八點鐘,就吃了晚餐。主人“打豬”相款。“打豬”儀節,與烏坡所見“打羊”相同,將小豬在篾籮內當眾殺死後,全豬放在鍋莊火中燒幾次,然後用刀將燒焦的毛,大部刨去。此時乃將豬剖開,肚腸取出,略予洗滌。豬肉連燒黑的皮,與剩下未刨乾淨的毛,切成若干大塊,投入鍋中煮熟,最後還是加上一桶生水。豬腸一部分直接加入鍋中,與豬肉一同煮熟。另外一部分,則置圓底鐵瓢中,直接在火中煎之,將油煎出,然後倒入鍋內。豬頭及豬蹄,不入鍋煮。將豬身破開以前,先將頭及四蹄割下,放在鍋莊火中煨燒。燒好的蹄子,後來賞給娃子吃。豬肉煮熟以後,向我們要去一些鹽,與辣椒末一同加入鍋中,再煮一會兒,然後拿出來吃。
進餐的時候,主人照例將大批娃子招來,一同聚餐。吃時三四個人成一席。對於我們這些貴賓,主人一上來先獻豬肝。這算是敬意,因為肝在夷人中被視為牲畜最貴重的部分。據說豬頭平常也常拿來款客。尤其是豬嘴的兩塊,獻上算是無上的敬意,客人不得拒絕。常隆慶先生在涼山旅行,就常以此受窘。這次還好,主人沒有將豬頭拿來窘我們。烏坡久博人不錯。對於我們順利前進,透過涼山,頗為關切。自烏坡動身以前,曾以雞骨作卜,結果說此行必然有成。到了阿祿家,“打豬”時候,豬頭斬下以後,看見豬唇上翹,連忙告訴我們,這次前進,運氣一定很好。
晚飯以後就寢,鋪蓋剛一開啟,夷人看見了,從未見過的被褥,照例又是那一套驚奇和紛擾。食宿的報酬,我們送了四件藍布、兩方紅布、三個針抵、十八根針和若干棉線、絲線、絨線。主人對此,深表滿足,連聲道謝。三個女兒,連忙跑過來,搶著分東西。
阿祿几几和烏坡烏達兩個家庭,不期而然地有巧同的地方。兩家主人,各有三個兒子,就中以幼子為最好玩,最得寵愛。更屬巧合的一件事,是兩家小少爺,年齡都是十三歲。誰說十三是一個不吉利的數目?阿祿几几的小少爺,也和我們一見如故,玩做一堆。他父親那種奸詐和高傲,他一點也沒有。一到屋裡,就不斷地教我們夷話,同時我們也交換著教他漢文名稱。我們指著房子裡陳設的許多東西,以及身上各部分與衣服等,他一件件地告訴我們這些東西的夷名,這樣使我們一晚上學了不少夷話。吳齊倮狗子住的地方,位在黃芳埂附近(在涼山西坡近頂處),名叫“隴作”,夷語讀如Roontso.用法文的r字音,不很容易讀。我們裡面,每逢有人讀此字讀不真,這位小少爺,便笑個不止。
蕭木雞
阿祿几几家中的當家娃子兼鍋莊娃子,是一位姓蕭的漢人。據他自己說,原籍為貴州威寧縣人。原名蕭少卿,乃販賣布匹的商人。二十多年以前,入涼山做布生意,為保頭所賣,遂致流落夷區,輾轉賣到此處。“蕭木雞”乃是夷人替他改的名字。家中老母已故。遺下妻子,還在故鄉,音信久已不通。我們笑問他,在夷區何不再娶。他說在此聘一位女子,需要一百多兩銀子,無法可以擔負。當家娃子,為夷區娃子階級中的第一流。蕭君爬到這種地位,很覺得滿足,並不想回老家去。此君仍作漢裝。上身打著赤膊,肌肉甚為發達。底下一雙赤腳。只有下身一條藍布褲,仍然是漢式的窄褲腳。大約他的衣服問題,亦為經濟所限。夷區所見,到處是赤貧。當家娃子尚且如此,別的人可想而知了。
蕭木雞雖則本身甘為夷人奴隸,對於我們這班透過涼山的漢人,卻十分照應,而且相當具有感情。比起一般漢人區域的邊地漢人來,要強一百倍。一早起來,推著石磨呦呦地叫,為我們製備甜蕎餅當早餐的時候,一面他便和我們聊上了,告訴我們許多關於本地的事情。據他說,由雷波挑鹽到此處,趕程不過四天路,比由西昌運鹽來還要快些。因此本地夷人,均吃川鹽。土鹽(即鹽源縣所產鹽巴)在此無市。本地氣候溫暖,羊毛甚貴。棉布因容易自雷波來,價格不高,不過合一兩銀子一件。銀子一兩,當時在此處,約合國幣十三四元,在雷波則可合十六元。在此一兩銀子,可換二錢至四錢大煙,川鹽則大約一斤可換一錢煙(土鹽需一斤半)。

戰爭時俘虜的白夷群,白夷被俘後常被征服者瓜分作更低下之奴隸或被分賣於他支為鍋裝娃子,1941年莊學本攝
美姑出產鴉片甚多。以前多系商人販賣。近來則官方敗類,成為大宗主顧。一位代某公專收煙土的徐八師爺,在此大收,結果在今年一年以內,即收去將近千兩。他們收煙的辦法,規模很大。預先將大批鹽布運來,存在夷人家中作抵,有多少要多少。這位徐八師爺,大煙生意雖然得法,結果卻受用不了。不久以前,一命嗚呼。現在他存在此處的東西,還有一百件布,幾十斤鹽。蕭君又說,美姑地勢頗低(據常隆慶先生記載,此地海拔一千四百米),天暖不長燕麥。米(系紅米)只長在河邊,為量不多,現在已吃完。一般夷人,普通多吃包穀。此外亦有蕎麥及小麥。一兩銀子,在此可換三升半穀子,或一升半蕎麥。柴在此處,最為艱貴。普通燒的燃料,多用草及包穀心。蕭木雞的漢話,絲毫未曾忘記。同時夷話說得異常流利,和夷人簡直一模一樣。他也說,夷家只管吃不管穿。自己種莊稼,並沒有多大利錢。所以娃子們總是窮的。
不祥之鳥
路上碰到吳齊倮狗子,乃是我們旅途中莫大的災禍。在阿祿几几家住下,吃過晚飯以後,屋裡有一位夷人,躺下抽鴉片。保狗子和呂贊臣,馬上就加入大抽。一面躺在地上抽大煙,面保狗子就對我們說了許多很甜的話。非常殷勤地,他用這些花言巧語,來哄騙我們。他說由美姑到雷波,他可不要任何代價,一直護送我們前去。有了他,一切便沒有問題,用不著另找保頭。過黃茅埂以前,繞道去“隴作”到他家裡住一宵,他一定“打牛”相款。對此阿祿几几也說,由倮狗子作保,最為妥當,他乃是去雷波路上最重要的保頭。保狗子前後彷彿兩個人,表面上態度竟作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令我們又驚喜,又懷疑。卻不料這個騙子,一方面就在畫我們的符。一面對我們說得那麼甜,同時他卻和阿祿几几兩人,嘰裡咕嚕地長談。欺負我們不懂夷話,當晚當著我們的面,他們就商量妥當,如何有計劃地阻撓我們的行程,不讓我們透過涼山。這些話呂贊臣都聽得懂。可是他也很壞,當時一點不給我們暗示,讓我們睡在鼓裡,妄想此行已無問題。等到後來到磨石家,幾乎走不通,方才把這些事和盤托出,而且怪我們由美姑到磨石家的一天旅程根本就是多餘,自美姑早就該折回。這種鴉片鬼,真是太可惡了。
吳齊倮狗子,奸詐、狡猾、兇狠,兼有漢人與夷人的壞處。可是人很聰明,漢話說得非常好。還會寫倮文。請他留幾個字在筆記本上作紀念,不料競寫了一句罵人的粗話。
續上涼山
早上八點半鐘,從阿祿几几家啟程,上後山去。阿祿几几本人,只送了一段。臨別的時候,他和我們說,萬一到了磨石家走不通,就請折回來,再到他家裡住,他再派人將我們送回烏坡。原來初到此處,問他去雷波有沒有問題,他的回答,是沒有問題。不意昨夜與倮狗子談後,論調忽然變了。今晨再問:他說由此到磨石家,他可擔保。磨石家以後的情形,不很清楚,最好到該處再問。原來他們計劃阻撓我們,業已有了定局。
派去代表護送我們的人,是主人的一位侄子,名叫“阿祿迭諾”。另外替我們背東西的四個娃子當中,主人叮囑了一位,特別招呼我們。蕭木雞也自動地送了我們幾里路。
離開阿祿家。路初左繞山緩上,右沿田走,向東北行。裡餘改向正東,上趨較陡。旋又緩上向東南前進,嗣復改朝東北走,順山脊走頁岩石板上,陡趨上坡。裡餘改右繞山上趨,一段陡一段平。如此一里左右,涉過一道小溪,路平坦向東行,右溯溪而上。略前復改向東北,路左繞山緩上,右仍溯溪而上。不遠上又較陡。裡餘涉溪,改由右繞山行,左溯溪而上。旋復涉溪,溪又到左。約半里,停下瀏覽風景。由阿祿几几家到此,共約六華里。自此前望,正東望見龍頭山斷崖,已不甚遠。崖下即滇境沙馬土司地。此座山峰的北面,延接上去,一條狀似刀背的山嶺,即是我們所要越過的黃茅埂,美姑河河谷在下,兩岸大都頗為陡峻。山上向西一條路,引到牛牛壩,循之空手趕路,一天可達。
續向前進,路改北行,沿雷建通道在山頂地帶走。約一里餘,改由路左繞山緩下。由美姑河一直上到此處,涼山系由暗紅色砂岩及泥頁岩所構成。至此再向上去,乃改為灰色石灰岩。緩下約一里不足,停下休息。阿祿几几與蕭木雞,在此告別回去。此處即系去牛牛壩的岔路口。更向前進,路左續繞山下趨,半里餘,路旁所見岩石,又由石灰岩改為暗紅色砂岩及頁岩,土色亦由黃改紅,路仍繼續下趨。又半里不足,涉過一道溪水。前去路右繞山走。有上有下,勢向上趨,方向仍蜿蜒向東北去兩裡半,又過一道小溪,路改陡上。半里餘,再過一道小溪,仍續陡向上趨,旋循山脊陡上紫頁岩山,中有一部分為淺色及黑色頁岩,此外並見有砂岩。這一段上山路,極為陡峻難爬。陡上共約三里,達到一片山岡頂上,停下休息。此時已近正午。忙將由美姑帶來的蕎巴,拿出打尖。此處崗頂,距美姑約十四華里。崗上菊科植物不少,此刻花正盛開。小朵的黃花、紫花與白花,編成一幅天然的美麗織錦。上山途中,自下向上望,彷彿此處即是山頂。到此才知錯誤。前面黃茅埂高高在上,還有相當的高。站在崗頂,回頭西望,烏坡、八咀等山。亦系高嶺插天,但是顯然並不見得比我們所站的地點高出多少。
下午十二點十分,復向前進,穿崗頂朝東北方向緩上。兩裡不足,上趨較陡,仍在山頂地帶向東北走。中間穿過蕎麥田不少。自美姑附近,所經皆系荒巾地帶,至此乃復見田。田中工作的夷人,看見我們走過,紛紛站起,問我們是不是販鴉片的。頻頻答不是,答多了覺得非常厭煩。這些無知的夷人,誠然可恨。可是漢人也不爭氣。過去別種人很少來此,來的全是些販賣鴉片的,無怪他們以為每個走涼山的漢人都是以此為職業。陡上一里,路改緩下。又一里,復改緩上。再一里,因候伴在路旁停下休息。
老婦的申訴
停下休息的地方,路兩旁都是蕎麥田,地面相當平坦,田裡有婦女們正在工作。該處距離美姑,約有十八華里。這時候王主任等,陪著倮狗子他們,慢慢在後面走,落伍很遠,我一個人走在前面。正在休息的時候,左邊田裡一位下田的老婦,突然跑過來,找說話。一看她是一位漢人。底下一雙赤腳,乃是小腳。這種樣子在田裡工作,真太可憐。這位老太太,大約已有五十歲的光景。跑過來便對我說,她家原來住在自流井,在該處算是相當有錢的人家。夫家姓傅。一個兒子,名叫傅章淑,原在貢井範團長部下,刻已奉令赴前方作戰。本人因避敵機轟炸,來到雷波,隨夫弟一同在縣城居住。不料後來夫弟被縣長征去做民工,剩她一人在家,無所依靠。這時候雷波城裡一位開糖坊的漢人,名叫秦懷卿的,欺負她無人照顧,將她綁走,賣給夷人。後來以十三兩銀子的身價,輾轉賣到此處當娃子。來此不過一年。成天光著一對小腳,在田裡做工,痛苦不堪。說到這裡,這位老太太,噓唏不已,連說:“請老爺做好事,給我通個信。賣我的就是雷波縣開糖坊的秦懷卿,這個傢伙最不是人,務必請官廳辦他。”這段傷心故事,真可叫人下淚。想不到一位抗戰軍人的老母親,一世享慣福的老太太,竟會賣到此處,做阿祿家的娃子,替野蠻的黑夷種田,於痛苦中消磨她的殘年。不過我們這種過路旅客,根本自己來涼山,就是冒著性命的危險,因此對於此類事,一時完全無法可以幫忙。只能允許她,到了雷波以後,一定替她遞一個信。後來走到雷波,公佈此事。不料縣城的人,業已忘記了秦懷卿這麼一個人。至於這位傅老太太和他的兒子傅章淑,更沒有人知道。可憐的老太太,她是被世界遺棄了,忘記了。
此片地方,皆是阿祿家地。夷區裡面,阿祿家原是相當強悍的一支。蕎麥田中工作的娃子,以婦女佔去大多數。夷籍女娃子、身體壯健,對於此種工作,感覺滿足。她們對於這位漢婦過去的歷史,內心的悲痛,完全不能瞭解。看見她久不回田,工作耽擱,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用一種快樂的聲調,向她尖聲叫喚,催她趕忙回去工作。哪知道這位老太太,已經是痛不可抑。
傅老太太來到夷區,雖不算久,但是一部分習慣卻已夷化。她的服裝,除底下一雙赤腳外,誠然仍是漢裝,並未改變。可是心理上面,已有變遷,向我訴說苦境以後,忽然也和夷婦一般,討起針線來。也許她確實迫切需要此物,所以不得不放厚臉皮。當然至少在這點上,我很願意幫她的忙,可惜針線等物,大部包在行李裡面。剩下少數,也全在同伴們身上。在此種情形下,只好用兩手遍摸身上口袋,做過試找針線的樣子。最後什麼也找不著,乃告她實在沒有,請她原諒。正在這個當頭,王主任和倮狗子他們來了。這位傅老太太,毫不知趣,不知道倮狗子就是慣賣漢人的壞東西,反而向他又申訴一番。將剛才和我講的那許多話,一五一十地又告訴他一遍。這事不異“與虎謀皮”,倮狗子當然是付之一笑。
奸計揭穿
原來我在旅途當中,常喜一個人走在前面,目的不過是想保持一種固定的行進速度,好從時間紀錄,計算路程遠近。此外並無任何其他企圖。至於碰上傅老太太這件事,完全是出之偶然。當時自己也就覺得,在這種地方,和漢人久談,不免要使夷人多心,很想快點擺脫。果真如此,倮狗子從後面望見,大為不快,便對王主任說,我一人走得這樣快,不和他們一起走,令他感覺不安逸。又說我身上有東西,不給他,只給漢人,不夠朋友。齊伴以後,王主任將這些話告訴我,勸我以後不要一人往前走,免得夷人多心。聽從此種勸告,只好大家一起前進。倮狗子彷彿故意為難。在一種平坦好走的緩坡大路上,他偏要慢慢地拖,弄得行進速度一點鐘不過四華里,可惡已極。
如此約行一里左右(自遇傅氏處算起),路上碰見黑夷數人,皆與倮狗子相識。因此大家又停下來。一群黑夷,大家坐下,吸菸久談。過了一陣,倮狗子忽然問我們要絲線。裘君從身上拿來一絞藍絲線給他。他嫌不好。給他綠的,又不要。身上實在沒有別種樣品,只好老老實實告訴他,其餘一起打在鋪蓋裡面。當晚到了宿站,便開啟讓他自己挑。聽到這話,他一聲不響,便把絲線拿了一些,還要去幾根針。倮狗子原來答應將我們一直送到雷波,而且自願不收一分的報酬。現在要東西要得這樣急,看來就有點兒蹊蹺。後來才知道,當他和那些黑夷高談的時候,曾經指著我們說:“像他們這些人,就是送五百兩銀子請我保,我也不保。”可惜我們夷話懂得太少,這種情形,當時一點不知道。
下午一點五十分,方又再度啟程前進。緩上約一里後,改陡上趨,向西北行。陡上約一里,到一岔路口。此處地名“易子角”,距美姑約二十一華里。前去磨石家。尚有七華里(俗稱五里)。去磨石家的路,在此與雷建通道分路。雷建通道,為右邊岔路,路面頗寬,爬緩坡徑上山去。向左岔出的小道,則是去磨石家的路。吳齊倮狗子,原來已約定我們,當晚一同宿在磨石鐵哈家,明日保我等前進。不料走到此處,忽然告訴我們,因有事要順雷建通道上山,到坡上一家親戚(也是阿祿家人)家裡歇,不去磨石家,請我們自己好走。明天他徑直回家,不過磨石家。我們過涼山的事,請找磨石家做保。這樣一來,使我們非常詫異。原來說得好好的,大家彼此也很客氣,何以忽然完全變卦,令人莫解。我們要他找完親戚,仍到磨石家宿,他不肯。要求和他們一起走,歇在他那親戚家,又不肯,反說到此應宿磨石家。最後雖然勉強約定,明天一早八點鐘,來磨石家找我們,一同前去,但是他對這話,全無誠意,顯然可以看出來。從此以後,我們就沒有和保狗子見過面。
最奇怪的,是負責送我們到磨石家去的阿祿迭諾,此時也推說有事,要和倮狗子一齊去親戚家,把我們交給娃子們代送。這事愈加離奇。起初大為不解。仔細一想,恍然大悟。原來倮狗子和阿祿几几,早就安排好了,預備破壞我們的壯舉,一切都是預定計劃,毫不足奇。我們發現這種詭計,還不算遲。要不然,倮狗子跟我們一起都到磨石家,只有故意向磨石家鐵哈,多說一些壞話,讓我們走不成。或者甚至假裝保送我們,半途卻把我們賣了,結果更不堪設想。
這時候呂贊臣方始將倮狗子剛才對那群黑夷所講的話,說給我們聽。他的結論是,倮狗子絕對不會再來找我們;如果不信,可問替我們背行李的那些阿祿家娃子。我們試問一位娃子,倮狗子好不好。回答果然是:“不好,倮狗子很會啃人。”問到阿祿几几和磨石鐵哈,他們卻都說好。至此完全證實以前的疑慮。我們果真上了倮狗子的大當了。
向磨石家走
倮狗子他們走了以後,我們循左邊岔路,向磨石家前進。現在護送的人,一個黑夷也沒有,一切要憑自己的運氣。初行路右繞山緩下。隨即改由路左繞山行,陡向上趨。此時路旁露出岩石,又系暗紅色砂岩及泥頁岩。半里後,路在山頂地帶走,微有上下,勢緩上趨。略前途中又碰見一位在此充當娃子的老年漢婦,向我們訴說身世。這位婦人,名叫李劉氏。自稱雷波縣李家灣人(該處距雷波城不遠),李家祿的母親。兩年前,母子兩人,在家同時被劫。其鄰居婦人,亦為夷人所擄。現在吳齊家當娃子,託我們設法救一救。對於這類事,我們所能做的,止於答應出去以後,替他們報過信。後來由雷波東行,到達箐口。因為李某正是那地方附近的人士,特別將這件故事,述給街上人聽。不料那些人對於此事,漠不關心。他們說,這類事情,在雷波一帶實在太多了,早司空見慣,不足為奇。而且李家祿一名,根本就已沒有人知道。擄進涼山的漢人真慘。自己受盡精神與物質上的痛苦,自不待說。最慘的,是外面的同胞們,早就把他們忘記得乾乾淨淨了。由美姑到磨石家,這一天途中,特別有感。上述兩件例子以外,路上碰見好幾位漢人,都是被擄進來當娃子。其中至少有兩個,原系商人,為吳齊家“裝桶子”裝來。由此看來,整頓涼山夷區,非殺吳齊倮狗子不可。
緩上一里,路改平坦,旋復陡上。如此半里,復改平坦,在山頂地帶走,向東北去。一里路左走過一座水塘。前行不遠,附近所見岩石,大體又系石灰岩。由此看來,大涼山正脈的地質構造,大約下面一節,系由暗紅色砂岩及泥頁岩所構成;上面一段,則系石灰岩,但其中亦互有穿插,裡餘改向北行,陡下石灰石做成的石路。隨即左繞山行,仍循石路陡下。此時所見石頭,又系砂岩。百米左右,下到一條小河。涉河陡行上山,初向正北走,嗣改東北行,右循山邊,左溯河而下。半里又見石灰岩。自易子角至此,計程約五華里。前行路續陡上,旋改平坦,曲折向東北去,右繞山行,左沿田走。田中所種的農作物,計有蕎麥及燕麥。更前右山亦有一部闢田。裡餘陡向下趨,走過已千的溝一道。過溝略上,乃又平坦,旋即於下午五點,到達磨石鐵哈家停宿。午後十里路,因沿途耽擱,走得又慢,幾乎費去四點鐘。然而究竟這天路短,到磨石家還嫌太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