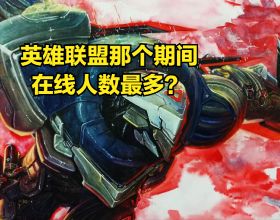2018 年11月7日,瑞典馬爾默。噁心食物博物館正在展出來自秘魯的美食烤豚鼠。(圖/ 視覺中國)
爬滿活蛆的乳酪、有壯陽效果的青蛙汁、浸泡在番茄汁中的醃製羊眼球、腐爛幾個月後曬乾的鯊魚肉、炸制的人類手掌那麼大的狼蛛、蝙蝠湯……這些腦補一下就能讓人作嘔的食物,就是位於瑞典第三大城市馬爾默的噁心食物博物館(Disgusting Food Museum)的熱門展品。
除此之外,我們熟知的臭豆腐、皮蛋、毛蛋等中國食品也在其列。此外,這家展覽館還展出了一些無從考究的來自中國的食物——比如,中國古代猴腦、來自廣州的鼠寶寶酒以及浙江東陽的童子蛋等。
該博物館網站首頁上寫道:“這個展覽有 80 種世界上最噁心的食物。如果你是喜歡冒險的遊客,你會很高興能有機會聞到和品嚐到這些臭名昭著的食物。你敢聞世界上最臭的乳酪,或者嚐嚐用金屬清潔劑製成的糖果嗎?”
博物館的小黑板記錄下了每個參觀者的嘔吐次數,噴射臭味氣體的空間中也配備攝影機抓拍每個參觀者的表情,有趣的是,可能是擔心弄髒地面,該博物館的門票就刻印在嘔吐袋上。
什麼是食用和不可食用的邊界?
這家噁心食物博物館於2018年10月首次開館,每年約接待2萬名遊客,由著名心理學家塞繆爾·韋斯特(Samuel West)發起。2018年,韋斯特讀到了一篇關於減少牛肉消費可以減緩氣候變化的文章後,開始了這個噁心食物博物館的專案。
“我不是素食主義者,也不是環保主義者,我不是想要拯救地球,但是我確實對肉類行業的不可持續發展表示震驚。”韋斯特說。
他創立這家噁心食物博物館,是想邀請人們跳出舒適區,走進食物的世界,探索關於什麼是可食用和不可食用的邊界,並嘗試改變我們的厭惡觀念,幫助我們尋找並嘗試新的、環保的、適合未來發展的可持續食品。
他也曾疑惑:“當你看到豬是如何被工廠化養殖的時候,當你看到工人給豬打入促進生長的激素的時候,其實更令人作嘔,甚至會威脅人類的生命。但是,為什麼大部分人還是願意吃豬肉,而不願吃昆蟲等更可持續的蛋白質來源?”
因此,他邀請了好友安德烈亞斯·阿倫斯(Andreas Ahrens)——一位前 IT 企業家和美食家,一起評估哪些食物可以作為合格的展品。
他們首先排除了人工製作的純噱頭食品——比如,若可·非茲(Rocket Fizz) 的汽水和吉力貝(Jelly Belly)的鼻屎果凍豆,以及油炸奧利奧等新奇食物。在400件物品透過初篩之後,他們嚴格按照味道、氣味、質地以及製作過程,進行下一輪篩選。
比如,一種來自菲律賓的受精鴨蛋小吃(當地稱之為Balut),當阿倫斯看到蛋殼中的羽毛、喙和血時,引發了強烈的嘔吐反應;而對於鵝肝醬,韋斯特和阿倫斯都認為它在味道、氣味和質地測試中沒有任何不妥,但鵝肝醬通常透過強力餵食鵝,直到它們的肝臟膨脹到正常大小的10倍,因此,其製作過程讓它成功成為這家噁心食物博物館的展品之一。據阿倫斯說,原本喜愛吃鵝肝醬的妻子,在瞭解這一過程後,再也不想吃鵝肝醬了。
因為展覽物件是來自世界各地的令人作嘔的食物,食物有保質期,而且應付海關和交通都是巨大的難題,所以,為了給參觀者更加直接的品嚐體驗,韋斯特和阿倫斯會嘗試自己製作這些菜品。為了製作秘魯美食烤豚鼠,韋斯特看了大量的給豚鼠剝皮以及煮豚鼠的影片,他曾在回憶中提到:“我做這件事的當天,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把老婆和孩子送走。”
厭惡是一種被灌輸而來的情緒
噁心,往往跟厭惡有關。而韋斯特認為,厭惡是人類六種基本情緒之一,它也不只是發生在食物的某個單一的方面。
比如有人對於氣味敏感,氣味通常因細菌產生,比如發酵以及洗過的乳酪等;也有人認為,糟糕的味道等於厭惡,比如鹹甘草,世界上只有六個國家喜歡;還有人認為,質地可能讓人噁心,比如柔軟黏稠的榴蓮果實;還有一種厭惡來自道德,比如某些動物被活剝皮等。當然,人類進化而來的厭惡功能是為了保護我們免受有毒或危險食物的侵害——這是主要目的。
不過韋斯特認為,“厭惡總是主觀的,這是一種被灌輸而來的情緒。如果是陪伴我們長大的東西,我們就不太會認為它噁心”。
因此,首先不要批判食物及其所在的文化場域,因為美味與噁心僅有一牆之隔,這其中包含個人喜好,也包含歷史、文化等因素。“噁心食物博物館的存在是為了讓人們探索食物世界,並從另一種文化的角度看待他們自己的食物和其他食物。”阿倫斯說。
為了突出這一點,展覽將來自世界各地的食物置於平等的地位,按照地理位置劃分,這種形式的背後,是食物所代表的地區與民族等文化因素。
比如,為什麼冰島發酵鯊魚肉(當地稱之為hákarl)在當地如此受歡迎?冰島當地的鯊魚數量很多,但有毒,因此,他們發明了一種技術來淨化這兩千磅重的動物——將鯊魚肉埋在沙中三至六個月,讓鯊魚肉自然腐爛、腥臭,然後才挖出來烹飪。因此,除了令人厭惡的臭味,你是否也認為冰島人這種淨化鯊魚的方式十分智慧與巧妙?
“厭惡使我們本能地拒絕可能有毒、已經變質、被細菌感染的食物。但還有一種可能是不熟悉的食物。此外,有些食物中存在貧窮與富貴的等級。”韋斯特說。
他還分享過一個可能是杜撰而來的故事,但是同樣具有說明性。當馬鈴薯從南美洲第一次來到歐洲時,歐洲人並不想要這個討厭的東西——它們長在地裡,嚐起來也很奇怪。儘管馬鈴薯在瑞典的氣候中生長得很好,但沒人吃它們,因為幾乎所有人都覺得它們很噁心。
而瑞典國王想出了一個辦法——他開始禁止非王室成員食用土豆,並在王室宴會上供應土豆。他利用心理學使土豆成為一種具有吸引力的奢侈品。結果沒過多久,公眾就要求他們也能買到土豆,因為“少”便意味著迷人。
當食物只提供給少數人時,它就成為一個人社會地位的象徵。比如法國貴族吃的奧托蘭——將鳥類眼睛挖掉,使其以為是晚上而過量進食,然後將它們活埋並煮熟食用,儘管法國已經於1999年禁止狩獵,但其鳥類數量仍因非法捕獲而減少;還有中國古代皇室宴會上供應的猴腦——儘管文化背景不同,但精英人士總是傾向於那些由於價格、稀缺性或準備困難而難以獲得的食物。
塞萬提斯在《堂吉訶德》中寫道:“飢餓是最好的調味料。”柬埔寨的地方美食油炸狼蛛(當地稱之為a - ping),本是由於紅色高棉統治時期食物短缺而出現,但最終因其大小和人的手掌差不多,且腹部和頭部外部酥脆,而成為柬埔寨人美味飲食的一部分。
韋斯特認為,噁心食物博物館的目的不只是展覽對人們來說奇異的東西,更是為了呼籲大家放下偏見和固有的傳統觀念,以全新的角度探索我們周圍的世界,挑戰人類對事物的認知,重塑“噁心”與“美味”的定義。
“因為,即使在一種文化中,噁心和美味之間的界限也可能非常狹窄。牡蠣或有臭味的乳酪被普遍認為是一種美味——但在這種食物的原產國,很多人都覺得它們很噁心。”韋斯特說。


噁心食物博物館裡展示的各種令人“作嘔”的食物。(圖/ 視覺中國)
噁心食物博物館就是最好的名字
自成立以來,噁心食物博物館一直在挑戰世界各地的厭惡觀念——一名來自中國香港的大學生表示,“這是我去過最有趣的博物館”,但也有不少批評家認為,無論作何種言論的包裝,當一家博物館在其名稱中使用“噁心”一詞時,便包含著種族主義與偏見。
其中,《全球化時代的食品電視與差異性》一書的作者凱西· R.凱利( Casey R . Kelly )認為文化機構的問題在於,運營機構的人並不總是能控制傳播的內容。“一方面,博物館在向遊客介紹新的食物,但另一方面,食物被剝離了它們的文化背景,僅僅在一個博物館展示。而該博物館,只是記錄了它們讓多少人嘔吐。”
對此,韋斯特認為,無論是支援還是批評,這些複雜的反應都證明這場味蕾實驗的奏效——他想要透過展覽與公眾交流,探究什麼才算食物,什麼是人與食物“相處”的邊界。
他表示,“噁心食物博物館”是最好的名字,如果他將其命名為“吃肉不好,你應該吃昆蟲”,那麼可能沒有人會感興趣;而“噁心”這個詞是有爭議性的,如果被更換為“奇怪”或者“有些不同”,則會因為太過於中性,沒有這樣的效果。
“‘噁心’會引起注意,我們是一家依靠公眾支援的博物館。這就是我們的生存之道。”韋斯特坦言道。
但是,來自對食物的淺層的厭惡感受,也許能催發人們對於不同地區文化的新的思考——由於不瞭解或者過於在乎自身感受,變相地理解為對於其他文化的厭惡,是否正確?
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一位美國華人記者分享了自己的經歷。當唐納德·特朗普將COVID -19稱為“中國病毒”後不久,這名記者的郵箱中收到了一張蝙蝠照片並且附帶一則訊息:“你們所有中國人都想吃蝙蝠湯和活老鼠,難怪這種冠狀病毒從你們中國開始,吃活生生的動物的人,請和你的家人一起滾回中國。”
此外,當她在雜貨店外面被路人聽到她在用普通話通話以及在坐地鐵時,“討厭的中國人”“噁心的中國佬”等聲音便不斷在她耳邊響起。
對此,她說:“認為所有中國人都攜帶冠狀病毒,是因為它可能起源於吃蝙蝠的想法,是荒謬的。但COVID -19的難以捉摸,使得帶有偏見的種族主義的觀點變得可信,即食用噁心食物的亞洲人肯定是攜帶和傳播病毒的人。”
這一瞬間,人們送進口中的食物,彷彿不僅僅是食物,而是衍射了一系列由無法接受的噁心食物而產生的種族、文化等偏見。這種偏見是全人類的,就如同噁心食物博物館的展品也是來自世界各地,這大概是韋斯特最想探討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