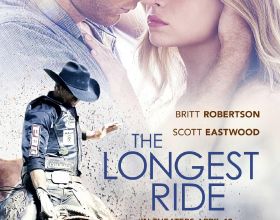小時候,某個中秋節,奶奶看著銀盤狀的月亮,問我要不要聽嫦娥奔月。有故事,當然要聽,更可況是仙女的故事。
我不知道你們的嫦娥為何奔月,反正我聽到的嫦娥奔月理由出奇離譜又萬分真實,故事大概是這樣:
部落一枝花嫦娥嫁給射日英雄后羿是一樁人人皆稱完美的好事。美女配英雄,十里八鄉都在流傳他們的幸福婚姻。原本他們確實你打獵我織布郎情妾意相親相愛在一起,甚至很長一段時間,他們的家庭都是“全國五好家庭”典範,他們的生活都是“高階品質”代名詞。
一萬年、兩萬年……十萬年,過去了。後來,嫦娥再聽旁人說起羨煞她婚姻的時候,都忍不住回懟:你試試十萬年,一日三頓,頓頓吃烏鴉炸醬麵什麼滋味……這樣的福氣,給你要不要!
“再吃,我都要變烏鴉了!”一日,嫦娥看到后羿又端出一碗麵,上面蓋著一團黑黑的烏鴉肉炸醬,心裡的弦終於崩了,歇斯底里,暴躁怒罵,“又是烏鴉炸醬麵,你是想吃死我……對,你就是想我死……”
后羿望著癲狂的嬌妻,也很絕望。他能有什麼法子,怪只怪他射箭技術實在高超,先是射絕了周邊各種動物,好不容易活下來的皆聞風喪膽避他如瘟神躲得越來越遠。萬年後,以他為中心的方圓十里,只有不長眼的烏鴉在亂飛。
他是沒關係,他有西王母送的仙丹,不吃不喝都行,可嫦娥不吃烏鴉炸醬麵又如何活?
自那天崩潰後,嫦娥便開始賭氣,連著好多天不吃不喝。后羿心痛得無法呼吸,再也感覺不到她的溫柔。他親了親嫦娥日漸瘦削的臉頰,告訴了她實情,並承諾會出遠門看看能不能獵到其他,哪怕一隻雞。最好是熊,那他就能做嫦娥最愛的熊掌炸醬麵。
嫦娥心想,你可拉倒吧,不如我吃了那仙丹,你愛吃烏鴉炸醬麵你就吃個夠。
又一日,后羿出遠門,嫦娥乘機吃了那仙丹。孰料多日沒進食的身體竟越來越輕,漂了起來,直到飛進了淒冷孤清的月宮。她恨恨地想,就算不吃不喝,沒滋沒味,她終於擺脫了那該死的烏鴉炸醬麵!
講完故事,奶奶問我,小囡說嫦娥為什麼奔月?我吃了口蛋黃月餅回答:烏鴉肉可能真的太難吃了!
後來,我只把這個故事講給了周澤頤聽,他說什麼來著?我努力地搜尋著記憶,試圖拼湊我和他所有的細枝末節,可他始終模模糊糊的,如鏡中花水中月。有時候,我忍不住懷疑,周澤頤是否真的出現在我生命裡,與我有過交集,還是他僅是我主觀臆想的一個關於思念的幻象,如同奔月的嫦娥,是千百年來人們締造的神話。
如果翻開封存已久的畢業冊,周澤頤三個字赫然就在我名字的上方。是啊,我應該和他認識了許多年,可關於他的一切,印象裡只有那3個夜晚和寥寥幾句話。
第一夜 桂子
我和他相識於高三的中秋夜,彼時全員衝刺,這節也不過是稀鬆平常的一天,大家都在沉默地晚自習。我有些不舒服,交完作業就早早回宿舍休息。
整個校園靜悄悄的,月光很亮,照得樹上的桂花粒粒分明,細小而飽滿,淡黃色地光暈綿綿不絕地往外散發輕輕柔柔的甜甜香氣。
桂花可太好聞了。我想,我要摘幾枝插在床頭。心動必須行動,我踮腳伸手去夠正對著月光最潔淨最鮮嫩最多花的那枝,樹都被我扒得搖搖晃晃,桂子撒了一地。
“是這枝嗎?”
有個清亮的嗓音從我頭頂傳來,我一個激靈,不會是學校風紀隊(主要職責抓違規違紀以及學生早戀行為)吧。
我故作鎮定放開了那棵樹,仰頭看到月光下一張白皙清亮的臉,我有些驚訝又有些疑惑,他只是我同窗兩年眾多沒有說過一句話的同學之一。
他眨眨眼,以他優越的身高隨手一折:“給你。”
“額,謝謝你,周澤……頤!”
“哈,原來你知道我的—”名字還沒說出來就被我“噓”地打斷了。
我做了個噤聲的動作,然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閃進林子裡面。
他一臉懵逼,不解地看著我貓在兩棵樹交疊的陰影裡。
我無語地翻了一個白眼,手指了指拐彎處,用氣音說:“風、紀、隊!”
我話剛落,一束電筒光就照到了周澤頤臉上:“同學,你哪個班的,不好好上晚自習,在外面瞎晃啥呢!”
周澤頤很鎮定地向走近的風紀隊行了個禮:“老師好!”然後規規矩矩地回答,“今天中秋,我父母找我一起吃了個晚飯,耽誤了一些時間。”為了增加可信度,他又從兜裡掏出一個月餅,“這是他們帶給我的月餅。”
風紀隊看著他那雙亮晶晶滿是真誠的眼睛,便沒有盤問,只催促他快去自習。
他目送著風紀隊遠去,良久,對著兩棵樹交錯裡問:“你不出來麼?他們都走遠了。”
我也從樹葉縫隙中抬眼看他:“你不去上晚自習麼?”
大概是看我貓在樹下模樣滑稽,他笑了出來,抓著我的領子把我從樹下提溜出來,想了一下,陳述道:“有時候我看到你,會覺得你很孤獨,宋一夏。我想—”
我一愣,然後笑著擺擺手:“不會的,不會的。我奶奶告訴我,只要還有想見的人,人生就不會孤獨。”我看著天上的月亮,接著道,“我一直有想見的人的。”
周澤頤沉默了幾秒,垂眼看著手裡的月餅,問:“你想吃嗎?今天是中秋節。”
我大腦一個激靈,突然意識到也許孤獨的人是他,便不假思索地接話:“嗯,好!一起吃!是蓮蓉蛋黃餡的吧!我可只喜歡蛋黃蓮蓉的月餅。”
他也開心了起來。我們找了棵最大的桂花樹,坐在路邊的石墩子上。我把摘的桂花插進兜裡,他把掰開的半個月餅遞給我:“是蛋黃蓮蓉餡的。”
中秋過後,我兩依舊沒有說過話,也沒提起過那個夜晚,一如既往的陌生。平靜沉默的高中生涯就在無聲無息中過去。高考後,同學都加了班級QQ群,因為感情淡漠,始終無話,一如整個高中生涯。每個人都有前路要走,每個人都有新的生活要嘗試,平靜無漪的過往終究會在記憶中淡去,直至遺忘。
第二夜 別離
再次見到他,套用卡薩布蘭卡那句話,世界上那麼多城鎮,城鎮上那麼多小飯店,他卻偏偏走進了我在的那一家。
他站在我桌前,問道:“是宋一夏嗎?”見我抬頭,驚喜道,“宋一夏,真的是你!”他很自然地坐在我對面的位置上,一副老鄉相見分外眼紅的模樣。
“那不是你的位置。”我指了指側邊,“要坐就坐這吧。”
他訕訕笑了笑,尷尬地挪個位置,問:“你是在等人嗎?那等他來了,我就過去。”他指了指斜對面的六人大桌,“我社團同學在那聚會。”
我順著他指的方向望去,他的同學友好地朝我微笑示意,其中有一個鬈髮的男同學還神神秘秘向周澤頤擠了一下眼睛。
我搖搖頭:“他不會來了!”
周澤頤斟酌了一下,問我:“要是不介意,你可以和我們一起聚的。人多熱鬧。”
我依舊搖搖頭,一邊給對座擺好碗筷杯子碟,一邊向周澤頤陳述這件事的意義:“以前我有一個一直很想見的人,他就在這座城市,這個大學,就坐在這個位置。”
“現在呢?”周澤頤敏銳地嗅到了八卦的氣息,忍不住追問。
“現在。”我輕輕地嘆氣,頹頹地答:“現在就不見了吧。”
不一會,服務員把我點的五個菜都上齊了,米酒也端了上來。
我把自己的玻璃杯和對座的杯子倒滿,然後問他要不要,要喝就自己倒。他擺擺手,給自己倒了一杯白開水,安靜地坐著,空氣一般透明,實際存在著。
我夾了一筷番茄炒蛋嚐了嚐,又用勺子挖了一勺花蛤燉蛋,皺著眉問周澤頤:“你嚐嚐,是不是不好吃?”然後又嚐了一口酸菜魚,頗感怪異,“真是奇怪的味道……以前他帶我吃的時候,明明覺得又鮮又美。”
周澤頤吃了幾口,低聲回答,又像是說給自己聽:“某些時刻,某些食物確實會被賦予美好的味道,比如八月十五、月餅。”
我沒有聽明白:嗯?
他沉默半晌,問我:“你是不是在難過?很難過嗎?”他試著開解我,“其實吧,其實某些感情一開始就意味著結束,有些東西一旦擁有就意味著要失去的。”
我咕嘟咕嘟喝了整杯的米酒,看著他不可思議道:“你在說什麼胡話!你是覺得我在難過?!”我趕緊擺擺手,“不難過的!不難過的!”
換他不可思議道:“看你神志清醒,情緒冷靜。”他思考了幾秒鐘,努力跟上我的節奏,“我是說,不像一般的女孩子失戀,哭得稀里嘩啦、撕心裂肺,絕望又悲傷,崩潰又痛苦。”
“你想看我那樣?”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我要像一般女孩子一樣?”
他神色複雜地看著我,搖搖頭,想說什麼最後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我不是那樣的。”我垂著眼睫,用筷子戳戳這道菜,又戳戳那道菜,悶悶道:“我只是在告別。以後這裡我不會來了。這個城市也不會來了。菜也不好吃。”
出了小飯店,我在打車,周澤頤跟同學說了幾句,又追出來,隔著馬路,大聲問我:“這麼晚,你要去哪?!”
“去看海!”我向他揮揮手。九月的晚風輕輕柔柔吹拂著這偶然的夜。
他隔著人流向我奔來,像摩西分開紅海一樣,邊跑邊盯著我喊:“等一下!等一下!我和你一起去!”
然後我們一起在海岸上散步,遠處一座大橋裝飾著燈帶,夜晚的風有些涼意,吹得人清醒。海對岸似乎有人在放煙花,一簇簇小小的光。他一直走在我和海的中間。
“你是怕我會做傻事嗎?”
“不是。”
“那是覺得米酒能把我喝醉?”我仰頭朝他笑笑,擺擺手,“我不會醉的。”
走累了,我們就隨便坐下。他指著前面黑漆漆地一片說:“以前我和別人也來這裡看過海。此刻,我覺得夜裡的海比白天的好看。深沉神秘,讓你猜不透水底藏著什麼。偶爾有月光觸碰的地方又是波光粼粼。”
月亮從雲層中透出來,又大又亮,整片海浮起一片銀白波紋,潮汐的聲音吞沒了一切嘈雜。
我看著那碩大的月,想著又是中秋了,我可真慘啊。我抬手揉了揉乾澀的眼:“又快中秋了,你看沙灘上的情侶,聽著音樂,放著煙火,花好月圓。我卻分手了,他說一分一秒都堅持不下去了,連過中秋後分都不肯。”
周澤頤定定看著我,問:“你是要哭了麼?”他伸手想要擦拭我流出的淚。
我往後躲了躲,擺擺手:“我不會哭的。我哭不出來。”
周澤頤悻悻地放下手,又建議我:“比如放煙花,不一定是情侶才可以的。我也可以放的。”
“可那又有什麼意思呢!沒意思!沒意思極了!”說著,我開始脫鞋子脫襪子,然後張開雙臂衝進海里,像是走入了另一個時空黑洞,安全又靜謐。
我對著深夜的海,大聲地喊:“宋一夏不想見顧劍深了!宋一夏不喜歡顧劍深了!”
所有的文字語言愛恨情仇都被黑洞洞的海水吸走吞噬,只剩下海浪的聲音。我的身邊沒有別人,只有周澤頤,我知道天亮後他也會消失的。
我回頭看周澤頤,月光下他白著一張臉站在我身後,然後走近我,虛虛地環住我。悶悶的聲音從我頭頂灌入我耳膜:“回去吧。”
“嗯,受涼生病苦得只有我,不值得。”
後半夜裡,我們都有些困了。躲在一處背風的臺階後,免得被海邊的巡邏人員看見。我知道海邊晚上是不讓待人的,是怕有人喝酒喝多墮入海里,還怕有人深更半夜在海邊做愛有傷風化。
我真的困了,靠在堤壩的一側睡了一會。朦朦朧朧中感覺額頭有極輕極柔極軟的東西一擦而過,似羽毛劃過。我的思維意識好像飛上了外太空。困、乏,這是夢嗎?還是現實的確如此?我已經沒有意識去分辨。
天矇矇亮了起來。我們掐著時間,到車站去等早班車。車上,誰都沒有說話。到分開的站臺,我們頭也不回的道別,向著相反的方向賓士而去。
又過去了幾年,畢業、工作。周澤頤的QQ有時會亮著,狀態一直是加班。加班,這個詞幾乎刻在他的基因裡了。我不知道他在做什麼,同樣他也不知道我在忙什麼。有時候想隔著QQ聊幾句,又覺得無關緊要,就把視窗關了。
第三夜 奔月
最後一次見周澤頤,是他突然聯絡我,說他到了我在的城市,要不要見一面。
我說,好,可是要加半小時班。他問我要了公司地址,在樓下的咖啡館等我。
等我去找他,他很自然地接過我手裡的手提電腦:“走吧,我定好了餐廳,就在這附近。”那一刻彷彿我們之間隔開的所有時間空間都已被填平。
他在前面引路,我跟在他後面低著頭思考我和他的關係,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嗎?好像也不對。
他突然停下腳步,轉頭看我:“我說,博學路是這條嗎?”
我抬頭,冷不丁撞上去:“啊?”
他一下樂了,玩笑道:“一夏,你這是在投懷送抱?”
我翻了個白眼,無視他:“一點不好笑。”然後繞開他,“博學路是左拐。跟上我前進的步伐。”
大概過了兩條街,他帶我去了一家酒店的空中餐廳。從玻璃幕牆往外望,能看見整個城市的燈火,也能看見天幕上掛著那輪碩大圓潤的月。
又是一箇中秋時節。
他端起杯子:“來,提前慶祝一下,中秋節快樂!”
我也端起杯子,和他碰了一下:“謝謝你,周澤頤。”
“嘗一下這個鵝肝吧。我看點評說是這裡的特色。”他把碟子挪到了我面前。
“sorry,無論多貴的內臟我都不吃。有點惡。”我如實拒絕。
他有一些茫然:“我怎麼記得,在哪裡你有說想來嘗試一下。”
“網上我都瞎說的。”我擺擺手,“試是不可能試的。”
他看了我好一會,久到我以為我臉上沾到了東西,我還在納悶我吃相有這麼差。他才開口:“你一點也沒變。這麼多年你一點也沒變。你好像永遠也不會變。”
我很詫異:“這話該如何說?我應該有成長吧,你看看,至少這法令紋長了。”
他搖搖頭,組織了一下語言:“吶,我的意思是,你整個人的狀態很自由,很舒展,一直都是這樣,不會刻意去適應什麼,不會為了什麼去強行改變,不喜歡的永遠不喜歡。你只是你,這樣才是你。”又補充了一句:“我無法想象,以後相夫教子的你,柴米油鹽的你,好像那些都不是你。”
聽完,我擺擺手:“誰知道以後會怎樣呢!”
“不過你以後一定會成為一個好老公、好父親的。”我篤定道,“你心裡是個溫柔的人呢。”
周澤頤垂著眼睫,輕輕地嗯了一聲,默了幾秒,還是說:“一夏,我要出國了,或許要定居在那。”他深吸了一口氣,試探地問,“如果可能,你要不要……可不可以……”
我擺了擺手,看著玻璃上印著的兩張一般淡漠的臉,我突然意識到如果這世界上有性轉版的我,那個人必定是他。這麼想著我就很高興,從心底溢位喜悅。我和他互為倒影,也是一塊磁鐵永不能相遇的南北兩端。
但我沒有告訴他我那時的想法,我只是指著窗外的月亮,問他:“你知道嫦娥為什麼奔月?”
他答:“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怎麼說,只能講你有點文化。”我揉了揉太陽穴,讓喝得微醺的腦子清醒一點,繼續講開頭我奶奶告訴我的奔月故事,“原本部落一枝花嫦娥和射日英雄后羿幸福地生活著……直到嫦娥吃到了后羿牌烏鴉炸醬麵……”
周澤頤聽得無比認真,若有所思,聽完哈哈大笑,給我比了個大拇指:“故事編得不錯,講得繪聲繪色生動活潑。”
“所以你覺得嫦娥為什麼奔月?”我繼續問他。
“誰家的婚姻不是一地雞毛?!神仙也逃不過去的。”他神色黯淡了下來。
也許與我而言,你才是那個嫦娥呢。我在心裡對他說。
那天我們後面說了什麼,我已經不記得了。再後來,他出國、結婚、生子,每一樣都要耗費太多時間精力,而我也在繼續我的生活,我們徹底失聯了。
也許在某個月圓之夜,他會想到我。但我聽說結婚的人的世界是多線並行交織成亂麻團,他們無法再有精神處理婚姻以外的人事,所以過往種種只能遺忘。
遺忘也是很好,至少我還能對著八月十五的月亮說一句:中秋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