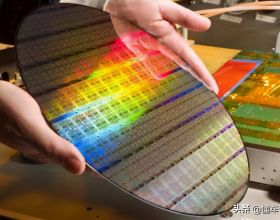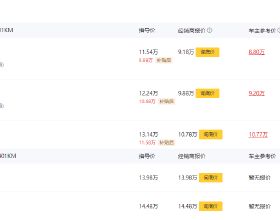崇禎七年一月,北京城沉浸在一片節日的氣氛中。大街小巷,張燈結綵,男女老少依然悠閒度日,過了初一過十五。
彷彿陝西的連年大旱、山西的大旱與蝗災、河南黃河以北的大旱、安徽、江蘇的大水、起義軍所到之處燃起的烽煙、遼東日益嚴峻的形勢,獨獨對北京人沒有什麼影響。
北京依舊是雍容自如、祥和安寧的老北京,它像一個飽經世故的老者,對苦難與貧寒,對危機與悲慘,早已經見慣不驚,它從容不迫,既不消沉,也沒有激情,只知道興致悠然地得過且過。
然而,對另一個家住紫禁城的年輕人來說,事情卻並非如此。按照中國傳統的年齡計算方法,朱由檢,就是大明天下萬世一系的崇禎皇帝,今年已經24歲了。
他絲毫沒有像北京城裡某一個小巷中與他年齡相仿的年輕人那樣生氣勃勃,無憂無慮。在他單調刻板的生活中,他感到除了煩躁,剩下的便是疲憊。這樣一個千瘡百孔的天下,壓在這樣一個僅僅24歲的年輕人身上,他怎麼能夠承受的了呢?
可是,他自以為憑藉自己的英明果決,憑藉自己的日夜憂勞,他能夠把這一堆爛攤子調理好,實現他中興的夢想。
也許,如果他是一個荒於政事、耽於享樂、縱慾無度的皇帝,人們會說他理當亡國,亡得其所;問題恰恰在於他不是,即使在歷朝歷代最勤奮的皇帝之中,他也算得上是突出的一個。這樣,這個年輕人的一生,註定是一個令人嘆惋的悲劇。
這一天,崇禎早朝施畢,便往慈寧宮來拜會太皇太后。太皇太后是神宗皇帝的后妃,她為人謙和慈愛,深受崇禎的尊重。崇禎的母親李莊妃早已去世,他對太皇太后就特別地禮敬有加,就像對親生的祖母一般。
這兩天軍務,政務繁忙,崇禎已經兩天兩夜沒有好好休息了。他非常疲憊,思量著拜見完太皇太后,趕緊回去休息一下。
山西流賊踏冰渡河的訊息他早已知道了,河南的流賊攻陷了伊陽、廬氏,遍掠汝州、浙川、內鄉、犯南陽,流入了湖廣境內,掠均州、光化,又以假作進香,攻陷隕西。
這一切,都讓他火冒三丈。各地撫按不思報國,除了接連寫幾篇告急的奏疏,該做點什麼,一點也不知道,任流賊在朝廷的腹心地帶往來奔突。
最可氣的是鄖陽撫治蔣允儀,身為朝廷大員,把守三省要衝地帶,眼見流賊入境,束手無策,只知上書請死。
自己就成全了這個無能的東西,前天已經下旨將他押回京城候審了。崇禎自即位以來,眼見那一班在魏忠賢當政時,還意氣風發、直言抗辯的大臣,閱歷了太多的仕途之後,都漸入頹唐;到了自己重新起用他們時,他們不願再多樹敵人,紛紛採取了明哲保身的態度。
這不能不讓年輕奮發、意圖有所作為的皇帝對他們失去信心。另有一些官高祿重的大臣,不過是進士出身,論資排輩地向上升官,真實本領卻一點沒有,平時倒還煞有介事地抖抖威風,裝裝樣子,一旦事到臨頭,就一塌糊塗,這蔣允儀不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嗎?
太皇太后聽到稟報說皇上要來拜會,急忙收拾停當,正襟危坐等候皇帝的到來。
崇禎行過叩拜之禮,站了起來。太后命人給皇上看座,崇禎便在宮女搬過的椅榻上坐了下來,微微曲身問道:“您御體可還安好?”
太后答道:“託皇上洪福,我最近身子骨倒還硬朗,但我看皇上倒是清瘦了許多。”
崇禎笑了笑,眼角扯起細細的魚尾紋,灰黯的眼窩顯著小了一點,他說道:“太后有所不知,昨天接到遼東急報,說廣鹿島守將尚可喜率眾降了韃子。我正為此事憂心,是以看起來精神不像是從前那樣了。”
太后平時並不關心時勢,但她也知道遼東的邊事、山陝的流賊是朝廷的兩大禍患,聽崇禎這麼一說,也跟著吃了一驚,道:“這卻是為了什麼事?”
崇禎不願讓太后過分擔心,只大略地敘述了一個梗概。
原來,尚可喜原是毛文龍手下驍將,毛文龍被袁崇煥誅殺,他便成了黃龍的部下。黃龍苛扣軍餉,激起兵變。沈世魁在幕後操縱,意圖殺死黃龍,自己取而代之。
尚可喜支援黃龍,聯合其他將領將兵變壓下去。黃龍感激尚可喜,將其拔為副將。去年孔有德降了滿人,為了立功襲取旅順,黃龍戰死,尚可喜全家死於旅順。
黃龍死後,沈世魁欲報私仇。他下令調尚可喜回皮島。尚可喜行至長山島,遇到了海風,船不能行走。沈世魁屢屢下令,催促尚可喜趕快回島,以免引起尚可喜的懷疑。他派人潛回皮島打探,知道沈世魁要將他處死,嚇得回了廣鹿島。
崇禎七年元月,尚可喜殺死副將俞克泰、仇震,全軍反明。接著,他率部連陷長山、石城、海洋諸島,集結軍民萬餘人降了後金。
昨天接到疏報的時候,崇禎也是震驚異常,現在經過一天的緩衝,他的精神已經平靜多了。他說著說著,一陣陣睡意襲來,他勉力支撐著,不讓自己在太后面前失態,身子卻不由自主地歪了下去。
太后見崇禎憔悴憂勞的神色,一陣憐憫的感情油然而生。她早聽身邊的人說,皇上憂國憂民,勤於政務,晚上經常批閱奏疏至深夜。現在親眼見到皇帝疲憊不堪的樣子,才切實感受到這個年輕人為治理國家辛苦到什麼程度。
太后輕輕揮了揮手,宮女們便都悄無聲息地退了回去。只留下兩個人悄然侍立在皇帝左右,靜靜等著皇帝醒來。
片刻之後,崇禎身體猛地抖動了兩下,醒了過來。他疑惑地看了一下四周,明白髮生了什麼事,慌忙跪在地上。不提防睡的姿勢不對,一條腿睡麻了,下跪時差一點摔倒。
崇禎神色中全是歉意,道:“稟太后,神宗顯皇帝在位時候,四海承平,天下安寧。現在四方多難,兒臣勉力撐持,這兩天夜裡都在通宵批閱文書,沒有片刻休息。想不到在太后面前,竟如此不能自持!”
太后聽了,淚水順著保養得極好的面頰流了下來,她喃喃地說道:“你的祖父若有你一半勤政,又何至於讓皇上你這般憂勞!”
崇禎出了慈寧宮。剛才小睡片刻,他的精神好了一點。不過經過這一睡,他想趕緊休息一下的念頭更迫切了。他早飯也不想吃了,心想,去他孃的,今兒就是天塌下來,我也要睡足了再說。
經過乾清宮的時候,崇禎看見皇后的鳳輦遠遠地過來。他猜測這是到宮裡來給自己請安的,便匆匆進了乾清宮。
不一會兒,近侍太監王承恩稟報,說皇后覲見。崇禎準了,周皇后低著頭進來。皇后生得容貌端莊,氣質華貴,眉宇之間稍稍帶著一點憂傷的神色。
當年,朱由檢受熹宗遺命入宮即位,雖貴為天子,卻時刻提心吊膽。魏忠賢當時權勢炙手可熱,宮廷內外,但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崇禎連宮中的食物都不敢吃,生恐稀裡糊塗地死於非命。
當時周皇后身居外邸,每天禱告占卜,為丈夫祈求福佑,測示吉凶,也是憂慮朝中有變。那時候,環境險惡,兩個人雖然經常很久不得見面,但感情卻非常熱切甜美,他們也特別珍惜相聚的美好時光。
後來,崇禎一舉掃清了魏忠賢等奸黨,自己成了大權在握的皇帝,周妃也變成了母儀天下的皇后,兩個人的感情反倒沒有從前那樣甜蜜。
崇禎已經失去了作藩王時的那份悠閒自在,他信心十足地要實現作“中興之主”的美夢,每天接見大臣,批閱奏摺,到坤寧宮的次數越來越少,也越來越短了。周皇后知道皇帝政務繁忙,理智上也理解崇禎的苦衷。然而皇后的心裡又不免生了一些幽怨,一個人整天呆在巨大空曠的坤寧宮裡,該是多麼的乏味和孤單呀!
周皇后給崇禎請過安,皇帝讓她與自己並肩坐了。皇后看見崇禎滿臉疲乏困倦的顏色,忘了自己的一點小牢騷,關切地問道:“皇上身體還安好吧?”
一股暖流迅速流淌進崇禎的心田,偌大的紫禁城裡,只有面前這個女人曾經和自己同甘共苦。在他最軟弱、最危險的時候,只要一想到她在為自己默默地祈禱,他的心裡就感到一絲安慰。
在這個平和安寧的女人面前,他這個萬乘之尊的皇帝,卻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的浮躁與卑微。在崇禎的內心深處,皇后與其說是一個賢德穩重的妻子,倒不如說更像一個慈愛的小母親或小姐姐,她是他浮躁與孤獨時依靠的溫柔寧靜的港灣。
在崇禎的印象裡,皇后從沒有氣極敗壞歇斯底里地發作過,甚至連發怒或大聲說話的時候都沒有,她總是那麼從容那麼鎮定,使人很難同時想到她其實也不過是個二十幾歲的年輕女人。
崇禎沒有回答皇后的問題,只是伸手握住皇后的雙手。那雙手溫潤細膩,崇禎把它們握到手裡,感到好溫暖好舒服。皇后有點難為情了,抬頭向下掃了一眼,貼身侍女香兒和王承恩無聲無息地退了下去。
朱由檢這時已忘了自己是一個九五之尊的帝王,忘了他不依賴任何情感和力量的幫助與撫慰,他是一切威嚴與力量的源頭,他是自足的。此刻他像一個疲倦的孩子,定定地望著皇后寧靜安祥的眼神,關愛地說道:“近來政務纏身,冷落了卿,卿不怪朕吧?”
周皇后雙頰微顯紅暈,道:“皇上為了黎民萬姓,日夜辛勞,臣妾自恨不能為皇上分憂,又何敢口出怨言?”
崇禎道:“這樣最好。現在天下多事,大臣們又沒有幾個忠於職守,整天拉幫結夥,勾心鬥角;山陝河南一帶,非旱即澇,民不聊生,真讓人勞神。”說著他不自覺地搖了搖頭。
皇后道:“外邊的事情,臣妾並不知曉。只是皇上近日清容消減,令臣妾不安,請皇上務必善保龍體,也好為天下蒼生造福。”
崇禎道:“我知道啦!”
過了片刻,周皇后問道:“近來掌管敬事房的總管太監好像換人了,不知道為什麼?”
一語觸動了崇禎的心事,他不由地輕嘆了一聲。道:“不光是敬事房,好多地方的太監都換啦。朕已經派陳大奎、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作內軍,分監曹文詔、張應昌、左良玉、鄧玘幾個總兵,派楊應潮、盧九德監京營兵,派張彝憲鉤校戶工二部出入。”
崇禎一一列舉,倒把周皇后嚇了一跳,她不禁聯想到天啟年間,魏忠賢一統天下的恐怖情景,道:“陛下讓這些太監們去外供職,握有重權,不會將來駕馭不了吧?”
崇禎的臉上浮現出一種輕蔑夾雜自負的神色,冷冰冰地說道:“他們不過是一群走狗罷了,誰要是敢鬧事,朕要殺要剮誰敢不服!”
崇禎嘴裡這樣說著,心裡卻想著另一件事。前兩天,因為張彝憲到戶部工部總理二部事,工部右侍郎上疏。說,部有公署中,尚書身旁列立著侍郎是禮儀如此,內臣張彝憲奉命總理工部,氣派儼然,是侮辱朝廷褻瀆國體。現在國家事糜爛到了這個地步,他們還在那裡爭論什麼國體,真令人氣憤。
自己在批奏中說,因為軍旅調動,餉事急緊,才不得已才派張彝憲去核驗。誰料這高宏圖也真有脾氣,連上七次奏疏,引疾求去,毫無身為人臣之禮,自己便不客氣地削了他的官職,讓他回老家了。
這件事情還沒過去,工部又出了亂子。張彝憲赴任,建專署,命工部諸官員謁見。工部主事金鉉恥於這樣作,兩次上疏爭辯這件事,崇禎因為張為自己所指派,剛剛赴任,不宜掃了他的情面,駁回了金鉉的奏疏。
誰知那金鉉又是一個牛脾氣,竟然私下裡約集了戶工兩部官員,約定誰私自謁見張彝憲,大夥一塊啐他的臉,弄得張彝憲好生下不了臺。所以張彝憲參奏金鉉的疏條一上,崇禎便免了金鉉的官職,好讓張彝憲大膽行事。
每每想起這些事情,崇禎心裡就感到惱火,自己使用內臣,原是不得已的措施。自己在上諭裡說得明明白白,這些文官不好好反省自己,反而動不動就以禮儀相威迫,以辭職相要挾,置國家安危於不顧,這豈是為人臣之道?
皇后見崇禎陰晴不定,滿臉悻悻之色,知道觸動了皇上的心事,便欲拿話岔開。她猶豫片刻,說道:“陛下,新選充任後宮的秀女,可有中意的嗎?”
崇禎不提防皇后說出這話,楞了一下,隨即會意,心道:“唉,現在滿朝文武,後宮妃嬪,也只有這個女人體諒朕的難處,肯於一心一意為朕著想。他微微一笑,忽然想起新選的秀女之中,有一個姓田的,生得容色秀麗,活潑伶俐。
那天太監們將她們一個個御覽的時候,那姓田的女子毫不做作,也不懼怕,與其餘恭恭敬敬,死死板板的女人比起來,多了不少青春的氣息,給自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此刻聽皇后問起,便隨口說道:“有一個姓田的,生得不錯,難得的是活潑靈動,倒是讓朕的心情輕鬆了不少。”
周皇后聽了,故意噘起嘴,裝作氣嘟嘟的樣子說道:“皇上得了新歡,過不了幾天,就把我這老太婆丟到脖子後頭去啦!”
崇禎見皇后說話時裝成的一副楚楚可憐的樣子,不禁動了真情。他復又挽住皇后的雙手,柔聲說道:“無論有多麼好的女人,也替代不了卿在朕心中的位置。”
周皇后沒注意皇上語氣的變化,接著開玩笑道:“說得倒是好聽,等真的見了那些千嬌百媚的小妮子,誰還記得這裡還有一個糟糠老太婆呀?”
崇禎正色道:“你如果不信朕說的話,那朕立刻傳旨,將那些女人盡皆逐出宮門,也就是了。”
周皇后見崇禎動了真格的,慌忙就地跪倒說道:“臣妾不過是哄陛下開心,一時說錯了話,請陛下恕罪!”
崇禎急忙將皇后攙扶起來,道:“朕哪裡生氣了?快起來,這裡又沒有旁人,何必要如此拘謹?”
周皇后見耽擱得時間不少了,便復又向崇禎請安,然後別了皇上,回自己的宮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