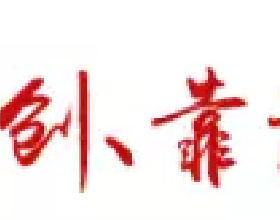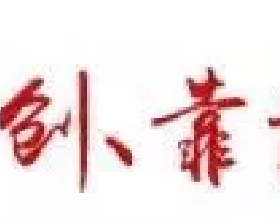走近黃河口
原創 李玉德
奔騰咆哮的黃河由起初的衝動,變為相遇前的羞澀。當黃河遙望到大海那寬闊偉岸的胸膛時,在嬌羞中放緩了步伐,挪動著踟躕的腳步走向了大海。一向沉穩的大海面對黃河的青睞,澎湃的內心再也壓抑不住原始的衝動,面對款款到來的黃河,湧動出了第一次潮汐。瞬時,黃藍之間完成了亙古以來第一次碰撞。從混沌初始,就相互心儀的黃藍,對結了盤古開天闢地後的第一吻。這一吻,成就了黃河和藍海的千古之戀。這一吻,如后羿射日的衝動,如夸父逐日的執著。這一驚天地泣鬼神的黃藍之吻,編織出了中華民族的搖籃,孕育出了中華民族的東方文明。齒唇之間的壯闊波瀾,攪動得中華大地蕩氣迴腸。
2017年初冬,應分別三十餘年東營籍老惠師同學之約,造訪慕名已久的東營市。剛剛踏上這片神奇的土地,就被眼前的壯觀景色折服了。古人有詩云,“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用它來形容黃河三角洲,應該是再貼切不過了。橘紅色的落日,在西邊的地平線上緩緩下落,透過薄薄的雲層透出絢爛的斜暉,一彎月牙已經在東方天際悄悄掛起。黃河在天水一色的朦朧中波光粼粼,掩飾著少女般的羞澀寧靜地融入大海的懷抱。詩一樣的畫卷沿海岸線舒緩地展開,濱海溼地荒灘蔓延,蘆葦茂密隨風搖曳。碧空遼闊,不時傳來婉轉的鳥鳴。
黃河三角洲溼地是國際關注的自然生態保護區,也是北半球候鳥遷徙的棲息地。據說東營的得名,相傳來自唐太宗的東征。新中國成立之前,現在東營的這片土地,還依然是渤海淺灘。1961年,繼大慶油田開發之後,“九二三廠”——也就是1971年定名的勝利油田,在這塊年輕的土地上紮下了腳跟,把昔日的鹽鹼灘初建成城市的摸樣。這片神奇的土地,是人們記憶中的“九二三廠”,是人們拼搏中的“東方紅”基地,是人們為之奮鬥的“孤島”。
當我們一行驅車來到黃河口溼地時,已是下午三時許。穿過水榭,踏上棧橋,腳下沼水清澈,魚兒歡遊,臨水灘塗蒹葭蒼蒼。蘆蕩深處,弱柳搖曳。登臨亭榭,極目遠望,天地之間,蒼蒼莽莽,日暮將至,晚霞滿天。偶聽離鴻聲聲,忽見雁陣自霞邊掠過。遠觀長河落日,低首水光倒影。蒼茫景色,蔚為壯觀。此時此刻,此情此景,沉寂的心不由地為之一振,難以描述的激動霎時襲上心頭。唐代王維《使至塞上》似乎從耳邊響起——
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
徵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
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
蕭關逢候騎,都護在燕然。
這裡既不是邊塞,亦不是胡天。既沒有大漠,也沒有孤煙。但長河卻在,落日亦圓。眼前廣袤的蘆蕩,浩淼的長河,孤懸的落日,和邊塞詩人王維的詩作卻有異曲同工之妙,在這裡亦能感受到同樣的蒼茫。這黃藍之間,宛若天之盡頭,地之邊沿,一片原始洪荒的景象。也許,只能在此情境中方能吟出“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泣下”那悲憫千古的詩句來。大西北的空曠和遼闊,固然會讓人發思幽情,可海岸線上黃藍之間的黃河口卻更讓人浮想聯翩。 這片新生土地的存在也許是一種偶然,這是大自然的賜予。1855年,因黃河從銅瓦廂決口,奪路大清河,入海至此,淤積出了這片年輕的土地。滔滔黃河,帶來了大西北的蒼茫雄渾。置於此間,仍可感覺到黃土高原那濃濃的氣息。
東營市同學孫榮文是此行現成的導遊,他如數家珍地掰著手指介紹。這一望無際的黃河口,地貌以蘆葦沼澤、溼地為主,其次為河口灘地、帶翅鹼蓬鹽灘溼地、灌叢疏林溼地,以及人工槐林溼地等,集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為一體,既有滄海桑田的神奇與壯闊,又有黃龍入海的壯觀和長河落日的靜美。
不到黃河口,難分蒹葭之別。初冬的季節,還有秋天的餘味兒。蘆花盛開,蓬蓬鬆鬆。朔風一吹,葦絮紛飛,在天空中悠悠飄蕩,彌天蓋地。這蘆蕩裡最多的其實就是兩種植物,一種為葦,一種為荻。這葦和荻,遠觀貌似,近看則有質的不同,正是貌似而神異。蘆葦有順風順勢生長之性,而蘆荻無論在什麼環境上都是挺挺拔拔,迎風而立,絕不曲意逢迎。心中對蘆葦雖無鄙視之意,但面對蘆荻,不由從內心產生了深深的敬意。那一棵棵挺拔而立的蘆荻,不正是一條條錚錚鐵骨的山東漢子嗎?不就是一代又一代不屈不撓的中國人嗎?正如毛主席所說:“我們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不被敵人所屈服!”棵棵蘆荻亦如激勵著中華民族的《黃河大合唱》。只不過,蘆荻是在用無聲的肢體語言頌揚著讚歌中的精神。 濱州學院同學李和教授對蘆荻做了更深層次的講解。他說,蘆荻就是《詩經》中描述的蒹葭。《詩經·蒹葭》中雲: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
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從之,道阻且長。
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詩經》中的蒹葭指的就是兩種植物。這“蒹”就是蘆荻,挺拔而立。“葭”就是蘆葦,曲意逢迎。也許詩經的原意,或許就是蒹為男剛,葭為女柔,蒹葭蒼蒼,自然成趣吧。蒹葭深處,弱柳叢生,雖為初冬,但仍葉綠枝茂,生機猶存。此等柳影,曾在宋人山水畫中見過,實景相見卻是初次。榮文介紹說,這是黃河口獨有的一種柳種,是從黃土高原沖刷而下的古樹種。想不到從巴顏喀拉山沖刷而下的古柳,歷經幾千年,行程幾千裡,在這黃河口落地生根了,這也許就是上蒼的賜予吧。也難怪古人描繪的柳樹和現代的柳樹差異這麼大,此可謂古今有別。也難怪古人有折柳為情,離恨條條之說。今日同學相聚,已經三十三年未曾謀面了。我們是1984年7月14日在惠民師範畢業並離校,至今已33年有餘,真是彈指一揮,轉眼即逝。此情難敘,此景難表,寫下再多的語句,也描述不出此時此刻的心境。
初臨黃河口,乍見一行大雁。只以為是雁陣掠過,再往蘆蕩深處,只見那大雁,低飛的,高翔的,水中的,蘆叢的,隨處可見,起落參差,鴻鳴雁叫,呼喚聲聲,北雁迴旋,千迴百轉。此情此境,讓人平添了一種別愁離緒,使初冬的暮色,愈顯出幾分蒼涼。這時若再聽歌曲《鴻雁》,肯定會別有一番滋味。
鴻雁天空上對對排成行江水長秋草黃草原上琴聲憂傷鴻雁向南方飛過蘆葦蕩……
落日時分,天色漸暗,我們一行登上了黃河口的標誌性建築——望遠樓。站在瞭望臺上,只見滔滔黃河,一覽無餘,天水一色,愈顯蒼莽。佇立望遠樓,遙望黃河口。遠見滔滔黃河舒展開了胸懷,宛若文靜少女飄然的黃絲帶,沒有喧鬧,沒有洶湧,靜靜地流淌著,去赴神聖的約會。極目遠眺,似乎剎時見到了黃藍交匯那激動人心的一刻。波濤洶湧,白浪翻滾,跳躍咆哮,激情四射。初為半藍半黃的河海交匯,後為流淌交錯,直至融為一體。
天色漸暗,意猶未盡。帶著對黃河口的眷戀,帶著同學深深的情誼,我們離開了這片令人蕩氣迴腸的土地。那顆激動的心,久久不能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