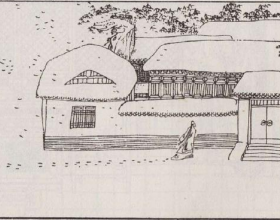一位母親用並不流利的英語撰寫書信,多年後,她曾經使用中文書寫的信件被女兒發現,然而女兒似乎既無法理解蹩腳英語書寫的內容,也無法讀懂母親留下的中文……這是譚恩美小說中常見的一幕。作為當下美籍華裔作家的代表人物,譚恩美的小說大量書寫了第二代與第三代移民在美國生活後產生的文化隔閡,母輩的歷史對他們來說成為了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傳說世界。利用民間傳說、夢境、現實等多種形式,譚恩美在《喜福會》《接骨師之女》《奇幻山谷》等代表作品中描繪了海外華裔的精神困境。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週刊》7月9日專題《譚恩美 陌生之信》。
撰文 | 宮子
譚恩美的小說基本都以美國華裔為背景,這也是她的作品能夠在美國獲得好評的原因。對中國讀者而言,譚恩美的小說能夠喚醒一種文化溯源的情感,她講述民國末期中國移民的經歷,尤其是那些幽深的情感在中國傳統的故事和風俗中得到了某種解釋後,我們也會在現代社會中發現那些被時間淘汰的文化血統。而對外國讀者來說,譚恩美的小說完全是理想的亞洲音符,村上春樹在寫普林斯頓大學的階級規則時也曾寫到,對歐美大學的教授而言,閱讀譚恩美象徵著一種品位的保障。兩三代人的間隙,傳統故事的角落,對上世紀社會歷史的追溯,這些形成了譚恩美小說中的標誌性元素,而這些元素反覆出現的原因,與譚恩美本人的家庭歷史密不可分。或者說,她的每一部小說,其實都具有濃烈的自傳色彩。
父親的缺席
譚恩美比較知名的小說作品包括《喜福會》《接骨師之女》《奇幻山谷》等等,但是在閱讀這些小說的時候會發現一個很明顯的特徵,那就是“父親”這個角色一直在譚恩美的小說中處於缺席的狀態。在自傳中,譚恩美本人對此有過解釋,她說,那是因為她與父親之間的記憶已經淡化稀疏,她腦海中的父親,不太像是那種穩定的親人形象,而更像是一種朦朧的、理想化的狀態,而自己在寫小說的時候,會盡量避免這種理想化的虛構。所以,“父親”的角色在小說中很少會出現。
在譚恩美本人的故事中,存在著兩位“父親”,形象也截然不同。一位是她的生身父親,也是她母親前往美國後所結婚的物件。這位父親在譚恩美的家庭回憶中一直是溫婉體貼的形象。他本來是一位牧師,為了要娶譚恩美的母親而放棄掉了牧師的職位,後來又在教堂裡公開宣佈自己將要迎娶一位比自己大六七歲的已婚之婦。這些行為在當時的美國社群看來近似於瘋狂。在婚後,相比於母親的脾氣暴躁,父親在大多數時候也扮演著調解員的角色。譚恩美講述過一個“吃西瓜”的故事。

“弗雷斯諾,1952年:清貧的牧師、節儉的妻子,逐漸添丁進口的家庭。”
那是一個全家人乘車出遊的夏天,父母買了一個解暑的西瓜讓譚恩美抱著。結果一不小心,譚恩美將西瓜給摔碎了。其實還是能吃的,但譚恩美的母親當時非常生氣,大發脾氣,認為都是小譚恩美將這天完美的出遊計劃給毀掉了。她很生氣地說那個西瓜不能吃了,直接將西瓜扔到了垃圾桶裡。譚恩美的父親此時倒並沒有指責她,而是悄悄衝女兒使了個眼色,然後趁著譚恩美的母親沒有注意,兩個人偷偷把垃圾桶裡摔碎的西瓜拿出來大快朵頤。對於年幼的譚恩美來說,在成長過程中,父親一直都在用類似這種的方式給自己關懷和安慰。他不像母親那樣,有時會將“愛”表達得特別明顯,有時又會將“恨”和“恐懼”噴塗在譚恩美的髮絲間。他更像是一股清澈的流水,用溫和的行動滋養著譚恩美的成長。
壓抑的遠方
而另一位名義上的“父親”,則是譚恩美母親在中國時的丈夫。譚恩美沒有見過他,所有這個男人的相關形象都是基於母親講述的故事揭秘而來。有其他美國華裔作家批評過譚恩美的小說,趙健秀認為譚恩美的作品在性別立場上是非常不公的,“她將中國男人置於最壞的一面去進行展示”。
其實只看小說作品的話,對譚恩美描寫中國男性時角度的批評倒也沒有錯。不過,在文學作品中,幾乎沒有哪種塑造事物的角度是憑空而來的。視角和態度都與創作者的經歷有著或多或少的關聯。
譚恩美母親的前夫,在現實中便幾乎是一個男人所能表現出來的最壞特質的集合體。
他是當時上海崇明島的第二大富豪的長子,譚恩美的母親因為面容姣好,家境優渥,而被對方看中。結婚之前,這個男人還算是理想伴侶的形象——外貌俊朗,身材也不錯,參加過軍隊,家境也很殷實。但在結婚當天,這個男人便馬上換了另一副面孔。他會將其他女明星直接帶到家中過夜,和譚恩美的母親說,即使結婚,他也沒有辦法拋棄之前認識的情婦,還告訴譚恩美的母親應該開放一些,和他們睡在同一張床上。譚恩美母親拒絕後,那位前夫居然還大發雷霆。
婚姻中有了這些遭遇,讓譚恩美的母親想到了自殺。可即便如此,男方也沒有任何收斂挽回的跡象,也不肯放她離去。他認為既然已經嫁過來,那麼女方便是自己的私人財產。譚恩美的母親拒絕讓這個男人再觸碰自己,他便把軍用手槍掏出來,用槍抵住譚恩美母親的頭顱進行婚內強暴。
對譚恩美母親來說,婚後的精神折磨還不僅如此。在她離家出走後,這位前夫僱傭了一批私家偵探,到處張貼她的照片,最後在一家美容院抓到了她,然後直接送到了拘留所裡和妓女們一起關了幾天。同時還聯絡媒體釋出頭條新聞,用類似“交際花對飛行員丈夫不忠”之類的標題。報道一出,譚恩美母親在家族中的形象頓時跌到谷底,即使回到孃家都要遭受親戚們的冷眼相待。在種種折磨後,譚恩美的母親最後終於決定選擇了在美國的情人,也就是譚恩美的父親。她離開了中國。多年之後,她聽到的訊息證明那位前夫的殘暴行為還遠遠沒有結束——他甚至強姦了數位自己親生女兒的同學。
對這件事情,譚恩美的母親一直是內疚而痛苦的。她自己逃離了魔爪,選擇了自由的生活,但她的幾個孩子們卻永遠留在了魔爪中。那位前夫後來娶的年輕妻子,對待前任留下的小孩子也用盡了折磨的手段。她們會恨自己嗎,她們會記得自己曾經有一個母親嗎,是保留著對自己的記憶好,還是徹底忘掉這個母親更好——這些問題繼續在美國折磨著譚恩美的母親。所以,在譚恩美的小說中,我們也總是能讀到那些看起來精神十分脆弱,好像背後有什麼可以直接摧毀掉她們的秘密的母親形象,這些並非是小說家刻意為之的人物塑造,而是對母親那代人遭遇的轉化描述。
當這些類似的故事被寫成小說之後,有記者問過譚恩美的母親,你的女兒把你曾經痛苦的私人遭遇公開描述出來,你會感到介意嗎?譚恩美的母親回答說,不會,她認為女兒將這些故事寫出來後,會讓某些事情發生改變。
成績單與遺書
譚恩美經常在小說中透過信件來鋪墊出家庭的秘密。比如《接骨師之女》,便以一封信件作為小說開頭,還有《奇幻山谷》中陸成寫給薇奧萊的信件,在其中吐露“現在,我要向你供認我對你犯下的深重罪行了……在離開上海之前,我沒有告訴任何人我是你的父親”。即使是在虛構的、以幻想為主的小說中,信件也是一種直白式的表達,是小說人物直接展示內心獨白的空間。在譚恩美的小說中,這些信件象徵著深沉的音調,它將一種總結式的、真相大白的悲劇詠歎帶入了小說的整體基調。
現代人的一大遺憾或許在於,我們未來難以從他人留下的資料痕跡中分辨真假——聊天記錄或者社交賬號都與一個人的真實自我之間存在著極大的割裂性。而由筆跡形成的物品,那些信件,日記,哪怕是日常的單據,都會以真實的方式指涉某個生活的秘密。譚恩美小說在使用信件形式方面,也與其童年時期在信件中發現的秘密有著強力關聯。
我們是否能感受到,當你從一份文字資料中,讀到了某張笑容背後的冷峻面孔所帶來的打擊呢?那種讀到私人文字後,導致在日常生活中對方的所有表現都變成偽裝的、近乎重塑世界般的毀滅感呢?這種感觸,譚恩美在還是個孩童的時候便已經深有體會。
譚恩美雖然擁有一位溫和的父親,極大程度上緩解了母親的人生傷痛,但是在家庭教育方面,譚恩美有些時候也會感受到那種無形的壓力。父親對譚恩美的教育要求很高,希望女兒能成長為優秀的人才。不過,即使譚恩美在學校裡表現得非常優秀,但是在家中,她還有一位比她更優秀的哥哥。父母喜歡在親戚朋友面前誇耀自己的孩子,話術類似於兩個孩子都特別優秀,非常令自己驕傲之類。儘管譚恩美的成績離哥哥彼得尚有一點距離,但其實在這種氛圍下,她從來沒產生過內心的不平衡,也沒有對哥哥產生過什麼嫉妒心理。

從左至右分別為譚恩美與哥哥彼得,譚恩美的母親及譚恩美的父親。
第一次讓她感受到失落的,是一份學校成長手冊的評語。平日裡對譚恩美態度很好的老師,在學生評語中寫到,“恩美在哥哥更出色的聰明才智下曾感到相形見絀。這份成績單大大鼓舞了她計程車氣·。她仍需我們和您持續不斷給予鼓勵,讓她能以這種精神飽滿的狀態繼續闊步前進”。
在這之前,譚恩美從來沒感覺到“自己在哥哥面前相形見絀”,她也第一次意識到,原來父母的鼓勵和誇讚,可能是為了照顧她,避免讓她在哥哥面前感到自卑。這些無法消除的墨跡在譚恩美心裡留下了強烈的心理暗示。之後,當她聽到家長誇讚自己的時候,內心反而會產生出一種不安全感,覺得自己變成了弱勢的、需要被保護的一方。
另一封信件對譚恩美的打擊或許更大。那是在父親去世多年之後,譚恩美整理父親的書信,發現,印象中呵護自己、溫存體貼的父親,在生命的最後時光中卻留下了讓人心碎的話語:
“最重要的是,我家出現了‘青少年’問題。恩美突然叛逆得不可理喻。一大清早,她會連著兩小時看報,懶得抬一下小手指去幫她媽媽……”
“恩美的冷漠態度大概是因為我本人疏於給予她耶穌基督的自我犧牲之愛。其實,這暴露了我的失敗之處:沒能向她彰顯上帝之愛。愛,從來不會失敗。如今不是愛的失敗,而是我的失敗。”
父親在譚恩美15歲的時候便去世了,(一同去世的還有她的哥哥彼得,父子兩人在幾個月的時間內先後因腦瘤去世)這封信是父親在去世前四個月寫下的最後文字。譚恩美從沒有想到,自己留給父親的最後印象是一個感情冷漠的女兒,更讓人痛苦的,是逝者已矣,這一切也再沒有機會挽回。
真相的多重版本
父親和哥哥去世後,譚恩美母親的內心變得更加偏執。本來就受到多重傷害、脾氣不好的她,現在陷入了更加難以擺脫的人生恐懼,她擔心幸福的生活永遠與自己無緣,擔心譚恩美也像丈夫和兒子一樣,突然從自己身邊離去。因此,她一度對譚恩美表現出了極強的控制慾。她不能容忍女兒在外面結交看起來不靠譜的朋友,不能容忍女兒在戀愛中失去貞操,當譚恩美與一個德國青年相識的時候,母親甚至拿出了切肉刀來進行威脅。
在譚恩美的回憶中,母親的精神狀態一直不太穩定,她多次產生自殺的傾向,在譚恩美6歲練習鋼琴的時候,看到女兒產生了不想練琴的厭惡感,母親也放棄了嚴厲批評的態度,轉而嘆氣,“你為什麼要聽我的?很快,也許明天,我反正要死了”。她總是以十分消極的態度看待人生,但只是給譚恩美帶去壓迫感。不過這次,是母親第一次以殺掉女兒而非自殺的架勢進行威脅。如果自己繼續堅持的話,會是什麼下場——譚恩美事後回想,她覺得,當時母親也很有可能為了保護女兒而殺了她的。
《喜福會》,《接骨師之女》,《奇幻山谷》都是譚恩美的代表作,每一本小說分開閱讀都能給人帶去深刻的體驗,然而,如果三本連著一起閱讀的話,就會發現那些複雜的故事貌似也並不是特別深刻,它們在敘事背後隱藏的線索非常相似,都是關於女兒追尋母輩命運,尋找自己血液中流散的家族之根的故事。《喜福會》的故事更是牽涉到了多個家庭。它們都在講述一種家族歷史的創傷延續。而譚恩美本人母輩的故事,只要原封不動地陳述下來,幾乎就能構成另一篇《喜福會》的故事。譚恩美母親的精神創傷除了第一次結婚的經歷外,也來自於她的母親,即譚恩美的外祖母,一個被用刀抵著強暴後被迫嫁入富商人家做小妾的女人,她在屈辱地生下了女兒後便選擇了自殺。(這個故事還有另一個版本,即這位外祖母報復性地帶著富商丈夫一起吸鴉片,最後吞食鴉片自殺)總之,自殺的念頭就這樣從外祖母的命運中傳遞到了譚恩美母親的生命裡。譚恩美回憶,母親曾經說過,在六七歲的時候就有想跟著死去的母親一起飛走的想法。
而同時,母親不穩定的精神狀況和那些往事給她帶去的創傷,也並沒有因為隔代的原因消逝。譚恩美本人也曾接受過精神治療。在《往昔之始》中,譚恩美寫到,“儘管我沒有自殺傾向,但童年經歷的確在我身上留下了痕跡。我無法容忍情感操控。我會匆匆逃離那些以威嚇和不確定性作為操縱手段的人,也絕不原諒那些有此企圖的人。我的身體不喜歡我當年體驗過的那種感覺”。
也許是童年的經歷和母親的故事給譚恩美帶來了反面的刺激作用,成為作家後,譚恩美出現了奇怪的情感體驗問題。她對於悲傷事情的感受倒是和普通人沒什麼兩樣,但是在某些時刻,她會莫名其妙地被一些場景感動。例如經過一場葬禮的時候,即使和死者素不相識,她聽到悼詞的時候也會禁不住痛哭流涕;在電視上觀看比賽頒獎儀式時,只要聽到國歌,不管是哪個國家的,哪怕是自己從來沒去過、或者並沒有好感的,也會因此流淚。醫生對此的解釋,是譚恩美曾經服用的抗癲癇藥物對大腦左顳葉產生了化學作用,讓體內的多巴胺升高,使得譚恩美很容易被刺激到、進入到幸福感爆棚的感動狀態。譚恩美對此的解釋是,服用抗癲癇藥物不僅控制了疾病,緩解了神經疼痛,同時如果停藥的話,那麼她可能陷入抑鬱狀態,會從被莫名的事物感動哭泣變成對著它們憂傷痛哭,“所以說,比較風險與收益,感覺太幸福又有何妨?”
而文學對此的解釋是,那些秘密——即使它們埋藏在我們的生命之外——但只要它存在於時間和記憶中,就會對人的生命產生震盪式的影響。正如譚恩美在小說中創造的那些故事一樣,女兒們試圖不斷破解母親的秘密,即使漂洋過海,換了迥然不同的文化與社會環境,那些記憶與憂傷,依舊會以某種形式,與當下的人輕輕地勾連起來。
“在中美兩國不通郵的那些年裡,母親只能靠生活在與中國有外交關係的國家的朋友轉寄信件,偶爾獲悉女兒們的訊息。前幾天,我找到錦多二十歲出頭時的一張照片,頗似母親年輕時的相貌。照片背面是工整的中文題贈:‘最親愛的母親惠存。我日夜夢想見到您。’這句話使母親感到痛苦與內疚嗎?我從未聽母親表達過懊悔。她表達對現實的屈從時,倒有一些不同的表述,像‘無可奈何’‘別無選擇’‘無法避免’等。其他家庭,比如我們的親戚朋友家,也無法避免這種事。母親的嫡親哥哥和他妻子,在戰時將剛出世的女兒留給一個貧苦的農氏收養,這樣他們這群年輕的革命者就不會因嬰兒的啼哭而暴露在日軍面前。舅舅和舅母在七八年後與女兒團聚。而母親直到三十年後才與女兒們團圓,那時女兒們比母親離開她們時的歲數還大。”
撰文|宮子
編輯|張進 肖舒妍
校對|薛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