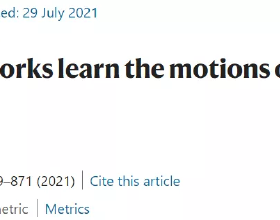當地時間2020年10月26日,法國“首家”寵物葬禮機構。視覺中國供圖

4月1日,廣西南寧市,一位寵物行業工作人員在挑選祭奠用的乾花。俞靖/攝(視覺中國供圖)
10年來,莫莫一直在面對死亡。
她在殯儀公司工作了5年,總在深夜接到電話。她負責到醫院、養老院、居民樓,給陌生的逝者淨身、穿衣,之後她寫悼詞,給葬禮上前來弔唁的人朗讀。
2017年,莫莫成為一名寵物殯葬師,幫人們送別狗、貓、兔子、烏龜……動物的遺體和人類一樣,有的已經僵硬,有的尚有餘溫。莫莫會拿消毒溼巾把它們的排洩物、嘔吐物或血跡一點點擦淨,拔掉它們就醫時埋下的針頭。最後,把它們火化後褐色或白色的碎骨放進罐子裡。
這份工作讓她感受到的是平等——跨越身份、地位,甚至物種的平等。
據《2020年中國寵物行業白皮書》,全國城鎮犬貓數量超過1億隻。《寵物行業企業資料報告(2020)》的調查研究資料顯示,全國有將近1400家經營範圍含“寵物殯葬、寵物喪葬、動物無害化處理”的企業,截至2020年11月,當年新增寵物殯葬相關企業超過1200家。
2020年冬天,紀錄片《離不開你》攝製組找到莫莫,想拍攝寵物殯葬師的故事。片子有6集,以寵物的衰老、失蹤、死亡為主線,呈現人和寵物的關係。聯合導演杜鵬參與了片中多個“死亡”主題故事的拍攝,他想透過拍動物,展現人類對死亡的態度。
北京的寵物殯葬師英豪曾感受過“生命的重量”。在給重病的寵物實施安樂死時,他會把手放在動物的下巴上安撫,兩管藥劑注入,它們的頭會逐漸失去頸部的支撐,完全落在他的手上。
1
22歲時,莫莫入職廣西一家殯儀公司。一開始,她只負責佈置靈堂,後來一位家屬希望能由女性來為女性逝者更換衣物,女同事沒人敢,她做了。“人心在肚皮裡。”
她回憶,初中時曾遭遇嚴重的校園暴力,被一群人圍毆、踹肚子,臉也被打腫過,有些施暴者她甚至並不認識。“噩夢一樣”的3年消磨了她對人的信任。高中之後,她性格變得更加敏感、多疑,總是融不進集體。沒有什麼時候最孤獨,“一直感覺孤獨”。
2009年,莫莫父親因患癌症去世。莫莫始終記得父親彌留之際所在的那間不足10平方米、沒有窗戶、不通風的單人病房。在走廊裡,最後一次被女兒攙扶行走的父親看著窗外說:“爸爸再也出不去了。”
與父親告別的時候,莫莫全程“手足無措”。她回憶,爸爸愛乾淨,但離開前都沒有好好給他清理,一切都很倉促。她總是遺憾沒有讓父親走得更體面些,便有意關注殯葬行業。
在殯儀公司,她見到有年輕的男士剛做了父親,就在大年初一早上腦出血離世。有老先生的遺體,被放在養老院的露天雜物堆,老鼠、蟲子到處爬,蜘蛛網粘在遺體上。有人的房子很大,卻在盡是鳥屎的鳥籠上搭一塊佈擺放母親的靈牌。還有老人在一間直不起身的閣樓裡去世,閣樓不通風,是那戶人家繁育寵物貓的基地。
寫悼詞時,莫莫總要先聽家屬講述逝者生前的情況。她把悼詞寫得具體,比如“他是一個愛吃蘋果的人”“他是個幽默的人”。但在莫莫的印象中,大多數告別儀式都像“走流程”,親屬圍成一圈,宣讀一份殯儀館提供的“通稿”,在這份稿子裡,每位逝者,都“勤勤懇懇,兢兢業業”。
2
當然,莫莫知道,“每個人都是不同的”,每隻狗也是。就像莫莫那隻名叫“娜娜”的哈士奇犬。
它有一身雪白髮亮的毛髮、渾圓有神的眼睛、略帶粉色的鼻頭和尖尖的下巴,是個“清秀的小姑娘”。莫莫家裡擺放的一張照片中,他們的頭摞在一起,莫莫笑著,露出整齊潔白的牙齒,剛好8顆。她的眼睛彎成新月。
擁有娜娜之前,莫莫很少會那樣笑。小時候,她父母比較嚴厲,不怎麼讓她和同齡人玩,她總自己待著,久而久之就不知如何和人相處了。看到一群玩沙土的同齡小孩,她走過去會聽到“人已經夠了”的拒絕。她不敢向別人指出照片裡真實的自己,“會選擇一個好看的小孩,說那是我”。
2011年遇見莫莫前,哈士奇娜娜在多個主人間轉過手。其間,它的腿曾經被摩托車嚴重碾扎過,留下長長的傷疤。據說它曾是一位法國來華支教老師的愛寵,在主人回國後無家可歸。最後,它給桂林一家狗廠看門,生不出小狗,不受重視,被一條三指寬、生了鏽的鐵鏈拴著。
莫莫認為娜娜和她很像。比如,她的人類朋友不多,動物夥伴卻一大群。她從小喜歡撫摸遇見的小貓小狗,沒有恐懼。娜娜和同類的相處也不融洽,有時是不搭理它們,有時會撲上去打架。但它在遛彎的時候,見人就搖尾巴。
“有娜娜的時候我就有了家。”莫莫說,他們一起生活了9年。
莫莫回憶起第一次見到娜娜時的樣子——染上了土黃色,很髒,很瘦小。一見到莫莫,它就奔過來,好像“特別開心有人關注到它了”。莫莫憑著一種直覺要帶走它,掏光了身上的300元路費。
一人一狗學著如何相處。剛開始手忙腳亂,後來,他們開始讀懂對方的眼神、動作和語言。
莫莫出門時,娜娜圍著她轉來轉去,是想出去遛彎。不讓它去,它就在家裡搞破壞,表達抗議。它會試探著爬上沙發,在主人回家時下去。莫莫則“都知道,沙發是熱的,還有狗毛”。莫莫會對狗抱怨生活。它聽了會嘆著氣走開。它喜歡吃蛋糕上的奶油,會吃掉荔枝的果肉,吐出核。
慢慢地,莫莫發現,她的飯碗裡、全身上下都有狗毛,她漸漸不再穿毛呢大衣。64G記憶體的手機儲存空間滿了,有80%的影像內容都是關於娜娜的。娜娜被養胖了,從30多斤長到60多斤,失去了“腰身”,它的毛色變得鮮亮,褪去了當年在黃泥地裡打滾的土氣。
她的工作地從廣西到北京、瀋陽,就帶著狗搬家。每次娜娜都不慌張,緊緊跟著她。無論在哪裡生活,娜娜都睡在她的床邊,她一伸腳就能碰到的地方。
在她的精神世界裡,“沒有什麼比它更重要”。
2017年,娜娜生病了,莫莫很焦慮,她決定轉行做寵物殯葬師,先在別人的“告別”中演習。2020年,娜娜的身體情況逐漸惡化,5月突發抽搐,6月29日忽然沒了心跳。從此,莫莫的沙發上沒有了娜娜,雜物越堆越高。
如今,莫莫在瀋陽一家寵物殯葬公司工作,今年10月,有人送來一隻哈士奇的遺體。大型犬很重,以往莫莫抱不動,但這次她堅持要抱著它去稱重。這隻毛色黑白的哈士奇讓莫莫蹭了一胳膊的毛,她就任由它去蹭。她在朋友圈裡對娜娜寫,“原來你也總是掉毛,一年四季,不分時候”“我沒有哈士奇了,我就是想抱抱哈士奇”。
3
不光哺乳動物能激發人的這種感情。資料顯示,2021年中國寵物狗和貓的數量最多,但也有人養金魚、龜、倉鼠和鸚鵡,把豬作為寵物的養寵人比例達到2.3%。
北京彩虹星球寵物火化殯葬服務中心曾接到一隻青蛙的遺骸。女主人見證火化時,與在外地的男主人打影片電話,男人一直在哭。後來,兩人一起取走青蛙骨灰紀念品,男人重複地說著,“你知道嗎,它特別好,特別聰明,特別乖”。在這家殯葬中心工作的英豪想了半天,想不出青蛙的“聰明”和“乖”應該是什麼樣。
曾有大學生從學校門口遞給他一條死去的金魚,讓他幫忙火化,金魚像餛飩大小,燒出來的骨灰“可以忽略不計”。他總是在琢磨,老鼠、魚、烏龜和人少有互動,怎麼也會讓人哭得死去活來。直到他想到自己那隻不親人的貓。這隻小貓跟著他從寧波搬到北京,從黏人的小奶貓,長成高冷的成年貓。以前他搞設計工作,週末加班,貓就躺在一邊睡覺,喊它也不理,但“那就是一種陪伴”。
透過送別“動物”,英豪見到各種各樣孤獨的人。有年輕人獨自前來,他們好像自帶著“烏雲的buff(電子遊戲術語,指有魔法的效果)”,讓整個空間的氣氛都壓抑了,他不知如何開口安慰。
他去過很多北京老小區,進去之後看見的全是老人。老人在家裡等著殯葬師,寵物已經被收拾妥當,蓋著床單,或放在冰櫃裡。英豪會問:“您想跟我們一起過去,再陪它待一會嗎?”大部分老人會拒絕。他們只會在身後不停道謝,說“拜託了,麻煩了,我們家孩子就交給您了”,邊說邊哭,還給他鞠躬。去接寵物時常常是夜晚,有時候他帶寵物遺體離開時,要默默走過那種聲控燈都壞了的長廊,扭過頭,“能看見身後有一扇開著的門,有個老人獨自靠著門看著你”。
他意識到,在獨居老人的生活中,“寵物常常替代了子女的角色”。英豪打過一個三方影片電話,連線在外地的女兒、在冰櫃裡的寵物遺骸和獨自在家的老人。那是在進行遺骸火化前,老太太實在捨不得,想對寵物說幾句話。老人獨白了20多分鐘,說著我們家孩子多麼乖,又多麼可憐,她的女兒在遠方輕輕哭泣。
英豪還經常接到聽起來“無所謂”的電話,一般都是中年男性打過來,“可能都不太好意思哭”。他們會說,“我的狗死了,拉走燒了吧”,好像不想被這件事牽動情緒,只想當作事務來處理。
4
兩年前,玥玥與丈夫在成都創辦了天堂事務所,除了提供入殮、火化的服務,他們還會為動物舉辦葬禮。就像人的葬禮一樣,主持人要朗讀悼詞,主人和親友會輪流發言,回憶寵物生前的點滴。
在這樣的葬禮上,人們常因為回憶寵物往事而在哭和笑間來回切換,有的葬禮要持續6個小時。有一個老人前來送別15歲高齡的狗,為它寫了一封很長的信,把這封信也和它一同火化了。
玥玥是經歷過與寵物貓的告別後,選擇了這份事業。那時小貓患了慢性病,但她女兒剛出生,無暇顧及,沒有及時發現。貓咪住院期間已經非常虛弱,但玥玥回憶,每次去醫院看它,它都會站起來,蹭她,朝她叫一聲。它死後,玥玥看到它曾鮮活的生命變成像一攤水的樣子,抱著它,它會從懷裡滑出去。她於是用浴巾把小貓包裹起來放在床角,不敢再看上一眼,而躲在角落裡哭了整整一晚。
最後,她在郊區山上找了個能幫人火化寵物的地方,是果農在家邊搭了個棚子,專做這門“生意”。老闆讓她給貓上炷香,祭拜一下,同時播放了一些佛教音樂。拜完之後老闆說,可以了,要燒了,讓她把貓放到焚化爐上去。她頓了好一會兒問,直接這樣燒了?老闆說,對,你讓開一點,我要推進去了。
玥玥發現,那一刻在焚化爐前,她有很多話說不出來。她的情緒,在那種環境下顯得“特別矯情”。她一直等到晚上回家才一個人悄悄地哭。她在那件事上理解了葬禮的意義。
英豪在工作中回憶起對死亡的初印象。一次深夜2點多鐘,一位客戶帶著寵物的遺骸來,同來的有3輛車。那是一隻大型秋田犬,4個男人一人一角用擔架把它抬進屋。這群人在告別室時,英豪在院子裡看著天空發呆。他回憶起小學四年級的一個夜晚,半夜突然醒了,聽見隔壁爺爺家有動靜。他迷迷糊糊地下了樓,看到隔壁的房子燈火通明,人們進進出出。南方的溼熱霧氣好像把他們隔開,對面像另一個世界。
朦朧中,他看見父親在拆門板,姑姑說:“把門板拆下來,讓爸躺上去,以後回來認得家門。”最後,他看見大人一人一角把爺爺抬走了。英豪曾經想,“怎麼可能找到回家的路呢”,但在那個看著一群人告別秋田犬的夜晚,他理解了這種傳統,是生者撫慰自己的方式。
他變得更寬容了,以前吵鬧的酒席,在他眼裡變得溫暖。有顧客帶來七八個朋友,把舉辦告別儀式的房間佔滿了,大家透過監控畫面看寵物遺骸被推進火化室,一些人哭了。但後來,他們叫的外賣到了。他們開始吃飯、喝酒、聊天,聊那隻狗,聊各自生活。狗的離開把平時沒機會見到的朋友重新聚到一起了,他們被狗的往事重新勾連起來。
5
莫莫的母親從來不對親友提起她的工作。每次回家,母親都會讓她跨火盆,除除晦氣。玥玥則記得,小時候有鄰居過世,家人會提醒她,不要去看。如果好奇打聽,會被告知“不要提‘死’字”,提了要馬上吐口水。她參加過親戚的告別儀式,“大人會讓小孩避開(遺體)”。
對大部分年輕人來說,死亡一直是“陌生”的。但真正每天面對它之後,玥玥覺得一點都不可怕。她會向兩個女兒自然地講起死亡。她會解釋,意外是如何發生的,而死亡意味著“不存在在世界上了”,“但想念它的親人會永遠記得它,會一直活在記憶裡。”等到女兒大一些,她希望可以帶女兒參加那些寵物的葬禮。
2017年,哈士奇娜娜患上子宮蓄膿和乳腺腫瘤,手術後恢復得不錯,但莫莫還是很焦慮,何況娜娜已經8歲,步入犬類老年期。她向熟悉的殯儀公司打聽,能不能給狗善後,多付幾千元錢也沒問題,但都被拒絕了。她最終決定改變自己的職業方向,找到北京一家寵物殯葬公司,投了三四次簡歷,最終成為一個寵物殯葬師。
但即使這樣,娜娜的死亡仍給她留下太多遺憾。
她總會想起,疾病給娜娜帶來疼痛,醫生開了止疼片,她怕有副作用,沒給它吃。娜娜保持著“大家閨秀”的作風,忍著不叫,疼得睡不著覺,白天黑夜都走來走去。直到有一天,莫莫的朋友發現它不對勁,說“如果難受的話你就叫出來”。只有那一次它叫了,像狼一樣,“嗷嗚嗷嗚”。
她回想,娜娜有時像她的女兒,有時像朋友,有時又像祖母,“總是遷就著我”。她覺得自己的愛有自私的成分,後悔沒有帶她看更多外面的世界。
莫莫描述的娜娜喜歡球,聽見球彈跳的聲音會豎起耳朵,“像兔子一樣”。2018年她開車載娜娜途經葫蘆島,下車看海。它踩在海水裡,“啪啪”跺腳,搖著尾巴。海浪一陣一陣撲過來,它跳著去咬海水。
莫莫甚至覺得,如果沒有娜娜,她寧願自己沒有出生過,但有了娜娜,她就要來到世界,要找到它。她希望把自己的骨灰和它的一起撒進大海,“我有深海恐懼症,但它喜歡”。
娜娜走後,莫莫會夢見它,但常常醒來就忘了具體的細節。只有一個夢令她印象深刻。夢裡,娜娜還活著,她卻知道它要走了,用雙手使勁兒捧著它的臉。以往她這樣做時,娜娜會抗拒,但在夢裡它沒有。莫莫一直覺得,是娜娜想要給她機會,說出那句她想說未說的話:“謝謝你,我愛你。”
實習生 郭玉潔 來源:中國青年報 ( 2021年12月01日 08 版)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