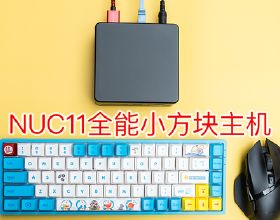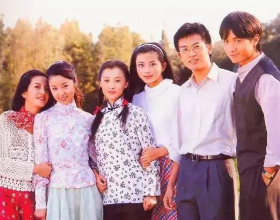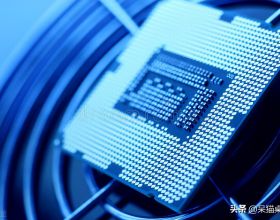執筆/叨叨姐&刀劍笑
北京“警告”在華開展業務的美企:“你們不可能‘悶聲發大財’。”
英國衛報今天以這樣一個標題,報道了中方與美國工商界人士剛剛進行的一場影片交流。
標題中的“警告”、“不可能”,報道中還用了“威脅”一詞,描繪出一個咄咄逼人的中國,“逼迫美國工商界遊說美方收斂反華舉措”。
這與實際情況存在不小的反差,根本不存在“警告”,“威脅”,還有什麼“逼迫”。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謝鋒在那場交流中的發言,早已公開發布,整個現場氣氛是坦誠友好的。中方“希望”美企為中美關係止損企穩仗義執言,在場美國商界人士也都認同經貿問題不應政治化。
西方輿論在報道中國時誇大其詞甚至歪曲抹黑,都是常有的事。但謝鋒當天說了那麼多話,獨獨一個“悶聲發大財”,被衛報捕捉到了,並做了發揮,這並非是偶然的,有頗多耐人尋味之處。
坦率地說,在這一輪中美關係的惡化中,美國工商界發揮出的正面作用是令人失望的,沒有像它們曾經表現得那樣,實際上阻止了華盛頓對中國的非理性打壓。
也確實存在只想“悶聲發大財”的情況,更有甚者,還有個別美企出於短視的一己之私,推動華盛頓加強打壓中國。
如此,謝鋒的話就有針對性了。
1
在中國外交部的網站上,有著對這場交流更詳細、更客觀的報道。
11月30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謝鋒與美國工商界和地方州市代表進行了一場影片交流。
隨文附帶的照片上,謝鋒面帶微笑,態度謙和。整篇發言給人的感覺也是友好深入,在寄望美國商界為中美關係止損企穩“發聲出力,仗義執言”時,都是坦誠之言。
謝鋒說:中美經貿合作不是發生在真空裡,必然受中美關係大環境影響。“大樹底下好乘涼”。大環境好了,經貿合作就會更順暢。反之,兩國關係惡化,商界也不可能“悶聲發大財”。
無論謝鋒這次發言還是之前中方歷次表態,也都明確強調加大開放,打造更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讓包括美企在內的國際商界安心放心”。
在11月30日的影片交流中,美工商界代表當即表示贊同經貿問題不應該被政治化,認為對華加徵關稅不符合美中任何一方利益。
在場的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代表提到,他們今年8月就曾聯名近30家美國商協會致信拜登政府,敦促降低對從中國進口商品的關稅。
9月2日,紐約時報曾以“美國商界敦促拜登推進對華貿易政策”為題,報道商界對拜登政府對華態度“越來越失望”。
報道說,拜登不但沒有取消特朗普時施加的對抗性政策,還放大了一些舉措。在華美企對這種做法日漸失去耐心。商業團體也抱怨他們的成員因關稅而處於競爭劣勢。
2
其實,在促進中美關係尤其影響美國對華政策方面,美國商界一直以來都發揮著重要作用。
有資料總結說,與中國保持相對密切聯絡的美國商界非政府或帶有一定政府色彩的組織,主要包括美國全國商會、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美國全國對外貿易理事會和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等四個機構。
11月30的影片交流,其中兩大機構都參加了。一個是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另一個是美國全國商會,中國美國商會和上海美國商會就是它在中國的兩大主要分支機構。
美國商界這些機構的共同點,就是它們囊括諸多商界和政界精英,透過“旋轉門”或遊說機制,對美國政府高層具有強大影響。這些機構的負責人每年都會定期拜訪美國國會山,與議員交流。
一位國際經貿問題學者對此也是印象深刻。他著重提到1990年代早期,中美關係出現劇烈震盪的時候,美國商界曾經發揮了很關鍵的作用。
尤其是在克林頓政府期間。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之後,中國對外開放力度較大,對外資的吸引力進一步增強。當時中美關係緊張,而歐洲和日本的企業就在進入中國市場方面佔了先機。
當時的美國商界向政府施壓,勸說不要攛掇“人權”等議題,還是要維持甚至加強與中國的經貿關係,不能讓歐日企業佔了便宜。
一定程度上,克林頓政府正是在美國商界施壓下,放棄了將人權和最惠國待遇掛鉤的政策。後來中國入世等事件,背後也有美國商界的影響。
克林頓時期,被認為是美國商界對中美關係發揮作用最大的一個時期。
3
但是,美國商界的對華態度並非完全一致,他們的具體利益訴求有著明顯分化。
看待中美貿易關係時,紡織業、鋼鐵業等的態度比較負面。而在中國有著巨大利益的飛機、汽車等行業,則力主美國緩和對華貿易關係。
比如,特朗普政府2018年以國家安全為由對進口鋼鐵加徵25%的關稅。等到拜登上臺,美國鋼鐵行業與工會組織趕緊呼籲,繼續維持加徵的關稅,因為“解除或削弱這些措施只會導致鋼鐵進口再度激增”,那將對國內鋼鐵生產商與工人造成“毀滅性影響”。
飛機行業的情況就不一樣了。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和最重要的飛機採購市場,它未來10年的採購量預估將佔到全球商業飛機銷售量的1/4。
然而,自2017年中美貿易關係緊張以來,直接來自中國買家的訂單隻佔波音公司新訂單的1%。波音公司執行長卡爾霍恩對此很是著急:美國航空航天業成績的好壞取決於中國訂單,“現在是時候指出與中國貿易關係的重要性了”。
既然如此,為何美國商界對推動中美友好的態度遠不如以前積極主動了呢?
一個客觀現實是,美國商界對華盛頓的影響力出現了明顯下滑。
轉折點出現在特朗普時期。特朗普雖說是個商人,但他和商界的關係並不密切,商界與白宮的溝通渠道也就不太暢通,商界的影響力下滑在所難免。
由於特朗普的持續毒化,即使拜登上臺,美國國內形成的貿易問題政治化氛圍已經積重難返,中美經貿很難被只當作經貿問題來看待。
而且,在中美經貿問題上,一些美國商界人士本就對我們有些看法。
一位中美經貿問題專家告訴補壹刀,這主要是兩個方面的原因。第一,我們對外資企業的政策有所調整,尤其是逐漸取消了諸如稅收優惠等很多措施,不再區分內資外資。有些外資由此出現心理落差,覺得不像以前那麼受重視了。
當然,這也和中國經濟體量的增大有關係。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外資企業在中國經濟中的相對重要性逐年下降。2007年是吸收外資的一個高點,全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826億美元,佔當年GDP的近2%。2020年吸收外資1630億美元,佔GDP的1%。
單看絕對值,吸收的外資這些年確實有了不小的增長,但它的增速明顯趕不上我國GDP的增速。
第二,外資企業在中國市場的日子不如原來好過了。
這些年,中國企業成長很快,對外資形成越來越激烈的競爭,他們被迫走出舒適區,不再能躺著賺錢。他們還感覺自己受到歧視,在中國市場面臨“不公平競爭”,尤其是有關政府採購、產業政策、智慧財產權、市場準入等問題。
雖然我國商務部資料顯示,2017年至2020年,已經連續4年修訂外資准入負面清單,限制措施減少近2/3,但是有些外資企業仍然覺得還不夠。
它們的心理很好理解:錢賺得少了,競爭還很激烈,只要沒法再像以前那樣舒舒服服地賺大錢,那就有各種不滿。
這就容易理解,為何在特朗普發起對華貿易戰的時候,沒有多少美國企業去遊說,其中一些人還偷偷揣著幸災樂禍的心思,甚至不乏個別美國企業在背後推動慫恿。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學者一語中的地說,還是因為個別外企以前在中國的日子太好過了,不管美國政府如何冒犯我們,它們都覺得損失不到自己頭上,還可以繼續賺錢。
必須說,這是非常短視的,或者說是很糊塗的。令人遺憾的是,這樣短視而糊塗的外企,不僅存在於美國,還存在於日本、歐洲……它們會因此付出代價。
中國已經成長,中美雙方力量發生變化,導致中美關係進入深刻的結構性調整時期。過去一些變通性做法將不再生效,有些玩法也必然會發生改變。
華盛頓不惜動用強大的政府力量,把900多家中國企業和機構列入各類“實體清單”,打擊、阻斷中國企業在美國的正常經營。我們考慮要不要使用“不可靠實體清單”,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中美關係如果進一步惡化,必將殃及美國工商界。這個道理對中日關係、中歐關係同樣適用。從這一點來說,謝鋒的話也算苦口婆心了。
圖片來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