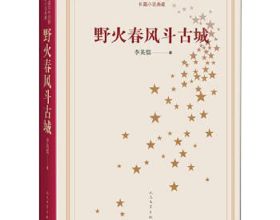首屆茅盾文學獎於1982年初開始啟動,評選的範圍,集中在1977年——1981年之間出版的長篇小說,參加評選的作品有134部,與今天每年動輒上千部的長篇小說相比,並不算很多。
經第一輪淘汰後,留下26部作品。之後又經歷了一輪淘汰,留下了17部作品。
最終獲獎的是六部作品。分別是:《許茂和他的女兒們》、《李自成》、《將軍吟》、《冬天裡的春天》、《芙蓉鎮》、《東方》。
當時馮德英的長篇小說《山菊花》也參加了評選。
這是當時山東推薦的三部長篇小說中的一部。
山東推薦的另外兩部是:
一是《異國飄零記》。小說1980年由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署名為未艾,但其作者的真實姓名卻是叢聳。據《濟南優秀文藝作品選》(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年版)介紹,這部小說的作者簡歷為:叢聳,男,1934年生,山東威海市人。原濟南市文化局局長,現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山東省魯迅研究會副會長、濟南市文聯顧問等。創作、發表及獲獎的代表作品有文學《異國飄零記》、《誰是幕後者》、《吳三桂與陳圓圓》、《古今藝術縱論》,戲劇有《趕考記》、《重審詩扇案》、《河祭》、《門當戶對》、《真與假》及“叢聳劇作選”等。大型歷史歌舞劇《窺鏡媲美》獲1988年山東省藝術節優秀劇本獎,並晉京演出。
這部小說之前是一部電影劇本,後擴充套件成四十五萬字的長篇小說,主要表現的是愛國華僑回國的故事,整個小說在今天看來,就像是一部通俗小說,語言上沒有什麼特色,在第一輪就被淘汰了。
二是《臨河的村莊》。作者肖鳴,山東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全書只有213頁。作者肖鳴,曾在《山東文學》當編輯,參與過京劇《紅嫂》的改編工作。《臨河的村莊》是農村題材,語言頗有鄉土氣息,但小說裡涉及到小村並大村的主題缺乏新意,自然在茅盾獎的評選中,難以擁有勝算的機會。肖鳴在小說出版數年之後就英年早逝,年僅50歲,令人扼腕。
這兩部山東推薦的小說都沒有什麼名氣,唯有《山菊花》尚有勝出機會。
《山菊花》當時只出版了上部,通過了第一輪、二輪的篩選,但在第三輪的評選中,也被淘汰了。
現在看來,《山菊花》被淘汰的原因,與它只有上部參選有著明顯的關係。
畢竟小說上部的情節還沒有得到充分展演,人物的命運,也沒有得到完整地演繹,自然很難用半部作品,去叩響茅盾文學獎的大門。
而且更為關鍵的是,《山菊花》的結構,仍沿用的是傳統長篇小說的板塊結構,敘述手段有些陳舊。
首屆茅盾文學獎作品中,與《山菊花》反映的題材類似的作品《冬天裡的春天》,就採取了一種回憶式的結構,使用了意識流的表現手法,在當時看來,帶有一種文體上的突破,而獲得茅盾文學獎。
但現在看來,《冬天裡的春天》的故事情節支離破碎,且帶有一種生編硬造的痕跡,反而在故事情節上,不如《山菊花》運用從容的手法所呈現出的蕩氣迴腸、峰迴路轉的氣韻。
畢竟《山菊花》塑造了非常真實的人物形象,刻畫了完整的人物心理歷程,這要比譁眾取寵的小說結構創新所導致的損傷人物的副作用,更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山菊花》的上部,1982年改編成電影,由倪萍主演,這也是倪萍出演的第二部電影。
《山菊花》的下部最早由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時間在1982年。小說定稿在1981年,出版速度還是挺快的。
本來電影《山菊花》是準備拍下部的,但是小說下部,人物的情感經歷,並沒有進展,驚心動魄的心靈的博弈,在上部都完成了。
其中,最代表性的是桃子在丈夫失蹤之後,被逼著嫁給了一個被稱為痴子的男人,反映了戰爭年代的女性,所遭遇到的一種尖銳鬥爭給情感生活帶來的巨大影響。幸好小說裡的這個痴子還是一個好人,沒有對桃子施以非禮與暴力,也沒有與她建立夫妻關係,當桃子的丈夫回來後,桃子完璧歸趙,潔身自好。但這個情節足以聳動人心,顯現出馮德英小說一以貫之的曾經被界定為自然主義的創作傾向。
馮德英的所謂的自然主義傾向,從他的二十多歲寫出來的處女作《苦菜花》中就已經露出端倪。
這與馮德英非常喜歡蘇聯作家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有關。
肖洛霍夫具有標誌性的兩個設定,後來都出現在馮德英的小說裡。
這兩個設定,一個是激烈的社會動盪,給家庭關係,帶來巨大的撕裂。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說《胎記》裡描寫了父親殺死了自己不同立場的兒子。這種殘酷的描寫,在《山菊花》裡也得到了反映。小說裡描寫的一個家庭中的兒子,因為出賣了家裡的秘密,父母不得不忍痛割愛,除掉了親骨肉。
另一個設定,就是一個養尊處優的富庶女性,看上一個低維的長工。
這個設定在《苦菜花》裡就以醒目的方式呈現出來,震撼了讀者,包括莫言在童年閱讀該小說時,也留下難以磨滅的記憶。後來他在《紅高粱》中也沿用了這種模式,設計了一個酒坊女老闆,與家裡的長工建立了額外的情愛關係。
馮德英的這個設定,在《山菊花》裡也得到了再一次故態復萌。小說裡描寫的一個綽號叫“小白菜”的女子,原是一名戲曲演員,後來被富豪家的病兒子娶為妻子,不久就成了寡婦,她大膽地愛上了家裡的長工,主動示愛,終於走到了一起。
因此,《山菊花》裡的對各色人等的情感描寫還是相當的波瀾起伏的,在倪萍主演的電影版裡,只抓住了主線,而支線上的這些遠超主線的離奇且曖昧的情感描寫,電影裡一筆帶過。在小說裡風情萬種的“小白菜”在電影裡毫無光彩,就如《苦菜花》裡給予了莫言以強烈的衝擊力的杏莉母親,在電影版中直接給刪掉了。
因此,小說《山菊花》帶著馮德英的自處女作之後就一直餘韻不斷的兩大主題,這兩個主題,正是日後莫言小說裡的一個貫穿始終的主線脈絡,只不過莫言給這個主題進行了重新定調而已。
但這也意味著,馮德英在《山菊花》裡的傳統敘事筆法,已經難以匹合文學程序的飛流直下三千尺的速率了。莫言抓住了這些部分,然後用新型的敘事手法,調和了一下,一道莫言大餐,便閃亮登場,在八十年代中期創造了一個震顫文壇的莫言力場。
從這個角度來看,1982年的茅盾文學獎評選中,《山菊花》的落選也是意料之中的。
馮德英的處女作《苦菜花》太過早熟,其實他根本沒有戰爭的參與經歷,我們可以看一下,他是1935年出生,建國時才14、5歲,剛剛是上學的年齡,與《紅日》、《林海雪原》的作者描寫的是自己的戰鬥生活,馮德英更多沿用的是他的童年的記憶。
到《山菊花》出版的時候,他也不過47歲,而李國文這時候已經52歲了,卻憑著一部文體創新的《冬天裡的春天》而獲獎。
馮德英過早地成熟,也過早地定型,在新時期文學中,他的年齡比王蒙還要年輕一些,但他一直給人一種老作家的感覺,後期寫作的小說,都不如他早期作品影響深遠。
這也是一個令人覺得奇怪的現象。處女作的成功,並沒有帶來後續的持久的發力,他把他的最好的才華,留在了他的二十多歲的年齡時的創作中,後來的創作風格,也與處女作《苦菜花》的語言風格,有了較大的變化。《苦菜花》中的一些深邃的帶有西化風格的語句,在後期作品中,幾乎不見了。
而比他大的王蒙,卻越來越依靠著氣韻貫通的翻譯語體,橫刀立馬,縱橫八十年代初的文壇,直到一九八六年莫言正式在文壇上奠定地位,王蒙的文學時代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