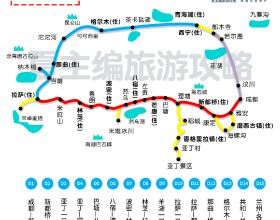古老的青石板上碾過司馬相如高頭駟馬的車軲轆聲,青羊宮燈會上流動著輕歌舞女的如絲眼波,錦江劇場響起李伯清東拉西式的川味評書。流傳已久的老話“少不入川”,是對成都難以抗拒誘惑的無奈反抗。
這不是個銷魂蝕骨的溫柔之鄉,因為歷史的岔路依然殺出了一彪人馬。有長衫裹頭的“袍客”,也有腰揣利刃的“哥老會”,有單槍匹馬殺死趙爾豐的尹昌衡,還有科甲巷冒死從法場劫出石達開的鐵杉黨。
川足死去的時候,被稱為最火爆的“金牌球市”只有九百六十五個球迷來為它送行,最肯拋頭露面的大概只有魏群一個人。“這個身體裡縫了兩百多針的人,被視為這座城市雄性的標誌”。魏群離開成都時,正流行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請將我遺忘》。經過成都最繁華的一條街道時,魏群突然感慨,“從此以後,成都就沒有‘大俠’了。”
馬明宇和黎兵沒有出面,但鮮為人知的是,魏群幾乎跑斷了腿籌到的七百萬錢款中,馬和黎各自掏了兩百萬。姚夏連夜把車開到了青島投奔黎兵,全興退出川足時他是第一個在大河的檔案上簽字的人。這個“家庭自助式”的球隊,印證了那句話,“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川足的死去過程極其痛苦,四川體育局回購冠城一度成為現實。當時身在廣州、掛職在四川足協的餘東風親自致電正隨賈秀全的國青隊在河北香河集訓的翟飈“回來執教”。
翟飈扔下電話直奔機場,在深夜回到成都。一路上盤算著“新川足”種種的興奮,讓他直到凌晨兩、三點都沒能睡著。第二天早上八點,翟飈早早起床,第一個出現在四川省足協大樓裡。
三天後,四川體育局因為不滿實德將球員全部掛牌,召開發佈會宣佈冠城解散。“不要再窩裡鬥了!”,“不要再打著拯救四川足球的名義來搞垮四川足球了!”徐明殺不死四川足球,殺死四川足球的只是四川自己。
翟飈在成都的某個飯店,與他因為承諾“來打職業聯賽”而招來的六名四川十運隊的小球員痛飲告別酒。之後二十二歲的譚望嵩帶著生死未卜的十運隊小隊員向副省長上書請願時,人們依稀從他身上找到了當年魏大俠的影子。
在實德正式要求譚望嵩到實德報到的當天晚上,他打了個電話,“我想寫一封信給副省長,告訴他我們現在的情況,要他幫我們這班十運隊的哥們兒想想辦法,他們不能沒球踢。”
最終譚望嵩成功地為自己的“兄弟夥”贏得希望,省足協著手組建乙級隊。當記者們隨同請願隊伍跑完全程後,對著一直極少說話的譚望嵩問,“這事到底是誰組織的?”他只是平淡地回答道,“是我。”
大連實德最開始點了三名四川冠城球員的卯,第一個就是譚望嵩,“屬於非賣品”。但譚望嵩最終還是去了天津,大連人出完了惡氣,在國奧戰略面前不得不做出讓步,國奧球員的身份最後救了譚望嵩。
那場永載史冊的“成都保衛戰”之後,一家專業報紙是這樣讚歎的:“這是一座從骨子裡向外流淌出酒味的城市。”在曠日持久的“第四城”爭論中,這次很陽剛的戰例曾經為成都添上了最具說服力的籌碼。但現在成都人似乎已經不喝白酒,晚飯時喝點紅酒,為夜場喝下各式各樣的洋酒作鋪墊。
四川冠城崩塌的時候,許宏濤將成都五牛倒賣給了英格蘭的謝菲聯,英國財團意外挺進成都足球。成都五牛在中甲聯賽結束後吼出了來年衝超的口號,對於這支以前川足為核心打造的隊伍,“衝超”只是他們玩膩了的噱頭。
曼聯在成都最中心的商業街春熙路,開設了它在中國的第一間快餐連鎖店餐吧。餐吧開業那天,春熙路實行了交通管制,開業典禮極盡奢華。大連實德老闆徐明攜曼聯副主席博比·查爾頓,球員韋斯·布朗聯袂出席,大連人和英國人似乎都鐵了心要吃定成都這碗足球飯。
大連人看中的是四川的建材市場,英國人據說想到成都修房子,謝菲爾德聯隊自己在英甲裡都廝混了十來年,也只是一個“準英超”球隊的假帽子,沒人能救得了川足。
在中國,金牌球市這個飯碗,沒那麼好端。川足那幾年的經歷,總結就是三個詞:“高樓起,宴賓客,高樓塌”。那棟樓本身不屬於誰,甚至也不該屬於任何人。大連人對川足的打劫,川中企業的懦弱,這注定是一場劫。
川足死去僅僅一年後,成都就已經沒有球市的概念了,他們擁有了李宇春、張靚穎、何潔、譚維維,這些叫做“超女”的女孩,數家報紙的“體育版”改成了“體娛版”。
對於川足的滅亡,一年前他們給予了冷遇,一年後連紙錢都捨不得燒一點。它可能是死於球迷的熱情不在,也可能是死於有關部門的官僚或本位,但更可能是死於媒體的冷漠。
川足以前有性格是因為有魏群,川足現在沒有性格是因為沒有魏群。魏群是四川足球的一粒鹽巴,生長在天下鹽的自流井。
中國職業聯賽元年,四川球迷從重慶包了一艘大船,出夔門,入浦江,“雄起”響起在虹口體育場。這一把鹽鹹透了上海灘,四川球迷在虹口被數萬之眾的上海球迷圍攻仍屹立不倒。
但如今,商業氣息早已經浸染過度,情懷已然顯得不值一文。人們晴天可以曬太陽,雨天可以躲在窗戶後面扮小資,喝茶可以喝得翻天覆地,泡吧可以泡得蕩氣迴腸,就是沒人再願意做痛苦狀去守著足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