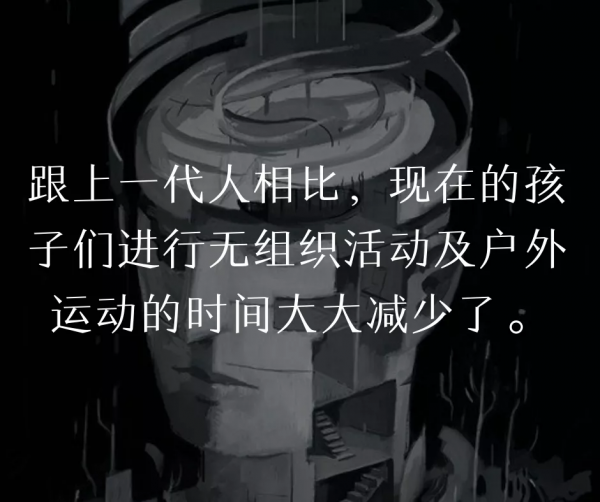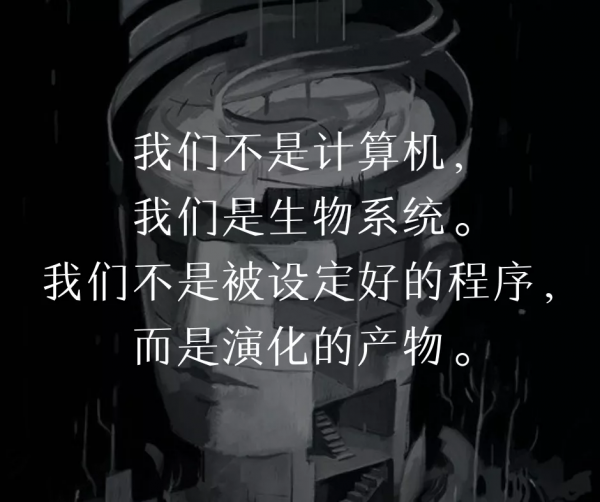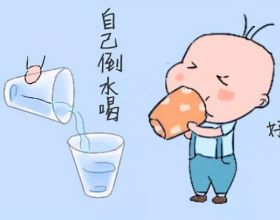以下文章來源於神經現實 ,作者M. R. O’Connor。
談及生命中最初那些年的記憶,我們無一不是遺忘症患者 | 圖源:pexels.com
導 讀
海馬體的存在不但讓我們建立起關於空間的認知地圖,還表明我們關於過去的記憶正是建立在認知地圖上的。
撰文 | M. R. O’Connor
翻譯 | M.W.
校對 | 里昂
責編 | Orange Soda
● ● ●
喬恩(Jon)是個26周的早產兒,出生時體重僅0.91千克,無法自己呼吸。起初的兩個月裡,他都被放在保溫箱中,但他最終還是順利地度過了嬰兒期和幼兒期。四歲時,他有過兩次癲癇發作。大概一年後,他的父母開始注意到,喬恩無法記住日常生活中發生的事情。他記不起自己看過電視、在學校發生了什麼、讀過什麼書。喬恩的智商是正常的,他能讀寫,在學校表現也還不錯。他能記住事實,卻記不住過往的情景。
等到喬恩19歲時,他找不到去任何地方的路,他也不記得熟悉的環境、自己的東西放在哪裡、以及兩地之間的路線。
直到神經科學家用磁共振成像技術探察他的大腦時,那些奇怪表現的原因才終於被揭開。他們發現喬恩的海馬體(顳葉深處的雙側腦區)異常地小,大約只有健康海馬體的一半大小。而這似乎是由於嬰兒時期的大腦缺氧(hypoxia)以及伴隨其而來的驚厥*(convulsion)對海馬體細胞造成了嚴重損傷,嚴重阻礙了海馬體的正常發育。
*譯者注
驚厥(convulsion)是一種身體肌肉快速反覆收縮和放鬆的醫學狀況,導致身體不受控制地搖晃。由於驚厥通常是癲癇發作的症狀,因此術語“驚厥”常與癲癇發作(seizure)混用。
海馬體——對空間認知和記憶至關重要,受兒童對環境的探索、在空間中的導航的經驗影響 | 圖源:Wikipedia
自1990年代以來,喬恩便已是諸多研究論文的研究物件了,但為了保護隱私,他的真實姓名並未公開。他的案例說明海馬體在人體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海馬體的存在不但讓我們建立起關於空間的認知地圖*、幫助我們記住位置並找到正確路線,還表明我們關於過去的記憶,即情景記憶正是建立在認知地圖上的。
*譯者注
認知地圖 (cognitive map)也稱為心智地圖或心智模型,是一種心智表徵,它服務於個人獲取、編碼、儲存、回憶和解碼有關其日常或隱喻空間環境中現象的相對位置和屬性的資訊。
天普大學的心理學教授諾拉·S·紐科姆(Nora S. Newcombe)解釋道,“海馬體演化出了空間導航的功能。我們的一個猜測是,在我們演化的歷史長河中,由於海馬體的神經結構十分適宜情景記憶,於是被演化所 ‘劫持’ 了。”
而空間認知和記憶對人類的意義遠超日常生存:它們形成了我們的自我感知。過去的記憶就像是我們個體身份的支柱;我們用它鑄造了我們生活中的獨特敘事。是這些故事塑造了我們的行動和決策,也為我們描畫出對未來的遐想的框架。
最近的研究揭示了海馬體在幼年和童年時期是如何發育的,而此時的神經迴路正在逐漸成熟,新的細胞也透過放電將空間編碼成了認知地圖。而孩子對環境的探索、在空間中導航、自身運動(self-locomotion)的經驗都會影響海馬體的發育。
紐約大學神經科學中心的研究員阿萊西奧·特拉瓦利亞(Alessio Travaglia)說:“這是非常令人興奮的發現,因為我們一般認為大腦的成熟只取決於時間和基因程式。但我們想說明的是,大腦的發育不是一個程式,它關乎經驗。在紐約成長的嬰兒和在沙漠或森林中長大的嬰兒肯定會有不同的經歷。”
這個關乎神經可塑性的發現令人著迷,但也敲響了警鐘。兒科醫生早已發出警告,兒童們玩耍的時間及其自由時間變少了,他們久坐不動的時間正變得前所未有地長。
一個多世紀以來,像喬恩一樣記憶缺失的人們為科學家提供了一種研究記憶的新途徑。科學文獻中最著名的遺忘症案例或許就是H.M.了。他最先是一位癲癇患者,後來在1950年代,也就是他27歲時,他的部分顳葉被透過手術移除,他也因此失去了獲取及提取情景記憶的能力。正是H.M.的案例使得科學家們發現,海馬體是情景記憶的源頭。
有意思的是,我們其實都像H.M.和喬恩一樣。談及生命中最初那些年的記憶,我們無一不是遺忘症患者。我們沒法回憶起2歲以前的事情,而直到6歲以前的記憶也都十分粗略和不可靠。這個奇怪的現象叫作嬰兒期遺忘(infantile amnesia),這之後是童年期遺忘(childhood amnesia)。幾十年來,它們在人類及其他物種(從大鼠到靈長類)中的普遍存在一直都是個謎。
天普大學空間智力與學習中心的首席研究員紐科姆說,“大家都覺得人生最開始那兩年太重要了。可是,如果我們都沒法記住這兩年,它們又是怎麼個重要法呢?對於這個問題,我們確實有一些答案。但如果我們沒有一個清晰乾脆的答案,那意味著,我們對大腦的瞭解還是太少。”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命名了嬰兒期遺忘,並將其解釋為一種壓抑(repression):大腦會避免嬰兒時期的慾望和情緒進入成人的心靈,而心理治療則可以再次通向那些慾望和情緒。後來一些針對嬰兒期遺忘的解釋都試圖反駁弗洛伊德的看法,並提出另一種假設:語言習得讓兒童有了長期記憶的能力。但也有其他表現出嬰兒期遺忘的物種壓根就沒有發展出語言,因此這一觀點的正確性仍存疑。
1978年,神經科學家林恩·納德爾(Lynn Nadel)和約翰·奧基夫(John O’Keefe)出版了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海馬體作為認知地圖》(The Hippocampus as a Cognitive Map)。它提出一個理論:這個形狀像海馬一樣的大腦結構是大鼠、人類以及其他動物對環境進行表徵的地方。這些認知地圖為空間記憶、定向和導航提供了基礎。值得注意的是,空間記憶系統正是從我們自傳式的回憶中提取出了用於儲存情景及敘事方式的素材。的確,我們對經驗的記憶總是注入了時間-空間的背景。當我們回憶很久以前發生的事,我們就會進入一次精神上的時間旅行,將過去的事件發生的時間和地點在腦海中具象化。
奧基夫早期的一個發現支援了這個理論:大鼠的海馬體中有一類他稱之為位置細胞(place cell)的神經元,當動物處於陌生或熟悉的環境中,這類神經元都會放電。不同的位置細胞在一個環境中不同的地方活躍,並共同形成了認知地圖。這項發現讓奧基夫獲得了2014年的諾貝爾獎*。在他之後,其他科學家們又發現了海馬體中其他用於空間記憶和導航的重要細胞。這些細胞包括:根據在水平面上我們的頭部朝向何方而放電的頭向細胞(head-direction cell),以及當我們在一個環境中漫步時放電並建立起座標系的網格細胞(grid cell)**。
移動、探索、陌生或熟悉環境中的經驗都會讓這些細胞放電。有證據表明,環境的豐富和複雜程度都會影響神經元的數量,進而影響海馬體的體積。比如在1997年,就有研究者發現,在豐富環境***(紙管、築巢用的紙條、滾輪以及可以重新排列的塑膠管)中探索過的小鼠比對照組多長了4萬多個神經元。這些新增加的神經元讓它們的海馬體的體積增大了15%,並且讓它們在空間學習測試中的表現有了顯著提高。研究者們總結道,是神經元、突觸和樹突數量增加的共同作用讓這些動物們在測試中的表現大大提升。
*譯者注
*科學家John O'Keefe 、May-Britt Moser、Edvard I. Mosel於2014年因發現組成大腦定位系統(GPS)的特殊細胞的研究成果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頭向細胞(head-direction cell)是在許多大腦區域中發現的神經元,只有當動物的頭部指向特定方向時,它們的放電率才會增加到高於基線水平。
網格細胞(grid cell)是在動物大腦的內嗅皮層(entorhinal cortex)中發現的神經元。它和位置細胞的相似之處在於,當動物經過給定環境中的一個小範圍區域時,二者都會發生強烈的放電;但與位置細胞不同,每個網格細胞都會在給定環境中的多個位置放電,放電的位置節點遍及整個環境,並形成六邊形網格。
***豐富環境刺激(enriched environment stimulus)是指由於周圍的複雜環境給大腦提供的物理和社會環境的刺激。大腦在更豐富、更刺激的環境中具有更高的突觸發生率和更復雜的樹突,導致大腦活動增加。
納德爾說,在寫書的過程中,他開始對海馬體的發育過程感興趣。其它的腦區在出生時就已經相對成熟,而海馬體並非這樣——不同動物的海馬體成熟時間是不一樣的。他說,“我們現在已經有了關於海馬體功能的理論。但是如果海馬體失靈了,會發生什麼呢?簡單來講,就是失憶症(amnesia)。” 納德爾的思路指引他聯想到關於嬰兒期遺忘的神經生物學解釋。本質上來說,像喬恩這樣的孩子是因為海馬體沒有發育完全,所以才無法儲存記憶。
納德爾在1984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表述了這一假設。他與共同作者斯圖爾特·佐拉-摩根(Stuart Zola-Morgan)共同提出,只有當一個生物體的大腦能夠對地點進行學習後才可能有情景記憶,而嬰兒期遺忘正發生於針對空間的海馬記憶系統尚未出現的時候。
而如今,納德爾卻認為在這個假設中,不管是對嬰兒期遺忘的定義,還是對海馬體成熟過程的描述都太過簡單化。但發育本身以及它與記憶之間的關係已經成為神經科學過去30年的議題中十分關鍵的一環。大腦是天生就能發育出空間和情景記憶系統的嗎?還是說這一過程需要經歷的參與?
行為神經科學家凱特·傑弗裡(Kate Jeffery)在博士後期間與奧基夫共事,主要研究的是海馬神經元,她說,“我認為該領域還在不斷努力解決這些問題,但我們還沒有得出確切的答案”。不過,她也解釋道,截至目前為止的研究揭示了一個神奇的過程:頭向細胞是最先活躍起來的,然後是位置細胞,最後才是網格細胞。因此,認知地圖的這些組成零件對於哺乳動物的大腦來說雖然是與生俱來的,但哺乳動物的大腦還是有一個獲取空間知識的時期,而這一時期可能會影響海馬體之後的功能。
2010年,兩個不同的研究團隊都揭示了這個發展過程是如何發生的。他們在尚未斷奶的大鼠腦中放置電極,在它們自由移動時記錄海馬體中單個神經元的放電。這兩個團隊一個來自挪威科技大學,另一個來自倫敦大學學院,二者都從大鼠出生的第16天開始記錄了數百個頭向細胞、位置細胞和網格細胞。
研究者發現,在幼年大鼠睜眼的幾天後、開始離開巢穴探索環境之前,這三種細胞就都已經出現了。但是在這三種細胞之中,只有頭向細胞是完全成熟的。幼鼠需要對環境進行幾周的探索,然後位置細胞和網格細胞才會成熟。從這些資料中,兩個團隊得出結論:即使在形成認知地圖的 “零件” 就位之後,空間學習的能力仍會持續提高。
神經科學家們結合了這些研究結果和靈長類動物及兒童的行為,來探尋這個過程在兒童大腦中是如何發生的。瑞士神經科學家皮埃爾·拉文克斯(Pierre Lavenex)和帕梅拉·班塔·拉文克斯(Pamela Banta Lavenex)提出,兩歲左右時,負責在長期記憶中區分物體的海馬體CA1區開始成熟並與嬰兒期遺忘作鬥爭。而從之後幾年的幼兒期開始一直到成年,可塑性極強的齒狀回(dentate gyrus)仍會進行神經發生(neurogenesis,新神經元形成的過程),逐漸成熟並開始支援新記憶的形成。
7歲之前,兒童的海馬體體積和他們的情景記憶能力有很強的關係—海馬體越大,他們回憶事件細節的能力也就越強,而這也正是童年遺忘完全退散的年齡。
納德爾說,“海馬體不是某天突然出現的。但是它的功能確實是慢慢實現的;正是這個網路以及海馬體各個部分內部的連線讓你有了長期情景記憶。”
2016年夏天,紐約大學神經科學中心的一個研究團隊在發表的文章中提到,他們發現海馬體的發育極易受到學習的影響。該團隊選擇了兩個階段的幼年大鼠進行研究,一個是出生後的第17天,大致對應人類的2歲,另一個是出生後24天,大致對應了人6到10歲的這一階段。
透過測量海馬體分子標記物的水平,他們發現了環境經歷是如何正向影響海馬體成熟的。此外,他們還透過增加或減少這些分子的水平操控大鼠的海馬體快進到記憶保持(memory retention)的階段或延長嬰兒期遺忘。
研究者還認為,嬰兒期遺忘與關鍵期有關,而關鍵期是環境刺激對大腦可塑性的影響尤其活躍的階段。上述研究的作者之一特拉瓦利亞說,“關鍵期是神經系統最為敏感的階段,如果這時候它沒有接收到正確的刺激,大腦的正常發育將會被阻礙。現在我們的假設是,人類的大腦在關鍵期也需要正確的刺激。這是對於獲取記憶尤其關鍵的發展期。缺乏合適的刺激會導致認知和記憶上的不足。”
除了環境本身,另外一個對於海馬體來說十分重要的刺激可能就是自身運動了。2016年初,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心理學教授阿瑟·格倫伯格(Arthur Glenberg)提出一個假設:當兒童開始爬行、走路時,嬰兒期遺忘就開始消退了。格倫伯格與共同作者賈斯汀·海耶斯(Justin Hayes)提出,一旦嬰兒脫離了成人的懷抱,開始在空間中自己探索,他們大腦中的位置細胞和網格細胞就會開始放電、對環境作出響應,並將嬰兒探索的環境進行編碼,最終形成情景記憶的框架。
格倫伯格過去20年的研究都聚焦在具身認知理論上,該理論認為,不論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的認知過程都離不開我們的身體,就像笛卡爾說的那樣。我們在世界中的經驗及思考都與我們的腿、胳膊、眼睛、耳朵、運動系統以及情緒系統的存在密不可分。格倫伯格說,“如果身體沒有影響認知等能力的演化,那才不合理。我們不是計算機,我們是生物系統。我們不是被設定好的程式,而是演化的產物。我們應該把人類的認知看作是其他動物的認知能力之延伸。”
在一次關於兒童發展的學術會議中,格倫伯格靈機一動,具身化(embodiment)或能幫助他解開嬰兒期遺忘的謎題,而且一些非常有趣的證據恰恰支援了他的這一假設。2007年,英國的一個研究小組發現,9個月大的嬰兒爬行的開始與其認知水平上巨大的飛躍密切相關:他們的記憶檢索能力更加靈活且成熟了。研究者們還發現,鍛鍊和自身運動能夠提高小鼠的空間學習和神經發生水平。
不過自身運動開始的早晚似乎遠沒有兒童探索環境的程度重要;2014年,荷蘭的研究者發現,在4歲之前,童年期探索環境程度更高的兒童擁有更強的空間記憶能力以及流體智力(fluid intelligence),也就是解決問題、總結規律以及邏輯的能力。
而格倫伯格的想法並不能解釋為什麼兒童從生命最初開始自身運動到6歲時擁有穩定的記憶能力要花上這麼長時間。他提出,這可能是因為兒童需要足夠豐富的空間探索及複雜認知地圖建立的經驗,來發育出像成人一樣全面運作的海馬記憶系統。
格倫伯格說,“10個月大的嬰兒可能知道他家附近的路,但如果讓他從家走到公園就不太可能了。他們需要大量行走的經驗來發育出複雜且相互關聯足夠多的一系列神經元來支援記憶。”
紐科姆在一次學術會議上的演講曾啟發了格倫伯格的假設,而前者認為,雖然格倫伯格的想法還只是猜測,卻正促使科學界往正確的方向發展。對她來說,海馬體可塑性最為吸引人的一點是,我們對它的進一步理解很可能會指導對運動受限殘疾兒童的治療進展。如果我們在關鍵期為兒童提供能輔助自身運動的器械,會不會幫助他們獲得認知技巧呢?2012年的一項研究顯示,有嚴重運動缺陷的嬰兒在使用定製的推車進行移動訓練後,與對照組相比,他們在認知和語言測試中得分都更高。該研究中,一個7個月大、患有脊柱裂的嬰兒在認知和語言技能上的進步速度甚至超過了在他的年齡應有的水平。
跟上一代人相比,現在的孩子們進行自由活動及戶外運動的時間大大減少了。一項研究發現,在1981到1997年間,孩子們自由玩耍的時間減少了25%;另一項聚焦於西雅圖的學齡前兒童的研究發現,孩子們一天70%的時間都在坐著。因此,儘管美國兒科協會建議每天至少做2小時體育活動,大部分孩子卻沒有這麼多玩耍的時間。
根據我們對海馬體發育、嬰兒期遺忘以及空間認知三者之間關係的最新理解,除了要對抗肥胖以及多動症等問題,我們還要讓孩子們有探索和建立認知地圖的機會,因為他們的認知健康,也就是大腦中將透過各種方式不斷影響自我感知的那部分正是有賴於這些機會才得以正常發育。大量資料表明,成癮、創傷後應激障礙、精神分裂症以及阿茲海默症的發生都與海馬體體積的下降有關。
還有一些有意思的證據表明,大腦的空間認知能力中蘊涵著智力的奧秘。在2016年9月的《自然》中,一項針對5000名 “數學能力超常的青年” 持續45年的研究發現,這些人的專利數及經同行評審的期刊文章數量和他們在空間能力測試中的得分具有相關關係。該研究的負責人之一大衛·魯賓斯基(David Lubinski)告訴《自然》期刊,“我認為(空間能力)可能是最為未知且未經開發的人類潛能。”
現在看來,嬰兒期以及童年期遺忘其實是我們的大腦正在為經驗學習打基礎。雖然我們記不得那些早先的經驗,但是他們最終塑造了我們成為真正的 “人”。紐康姆說,“這是我們理解人類心智和大腦及其發展的巨大事業中的重要一環,它意義重大。”
本文譯文原載於《神經現實》,《知識分子》獲授權轉載譯文。
作者簡介
原文連結:
https://nautil.us/issue/40/learning/for-kids-learning-is-mov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