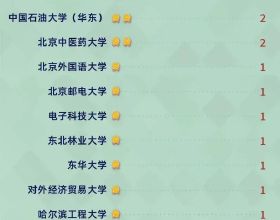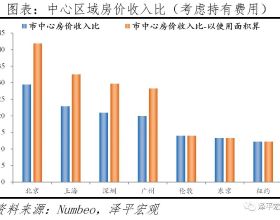東南亞地區一直被視為國際政治格局中的重點,是大國競爭的逐鹿之地。
儘管東南亞地區並非核心經濟體聚集區,但是約6.25億的人口總數和豐富的自然資源,當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的中國經濟的發展之時,依舊吸引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進行新一輪全球戰略佈局。
誠然,儘管美國國力在伊拉克戰爭和金融危機的侵蝕之下相對衰弱,中國在區域內也表現出越發強勁的領導力和影響力,然而,雖然兩者之間存在結構性矛盾,但此前中美關係在東南亞區域內一直表現為大國之間的包容性競爭,針尖對麥芒的激烈對抗未曾有過。
直到中美貿易戰爆發以來,中美之間競爭對抗關係愈發尖銳,原本在外交戰略上具有較大自主空間的東南各國只能被迫改變“軍事靠美國,經濟靠中國”的刻板思維,對中美兩大國互存的東南亞區域政策產生於巨大影響。
東南亞各國這種看似兩邊倒的政策不過是為了更好地在中美摩擦之下,既不被美國和中國當作棄子而放棄,又希望趁亂在中美的爭鬥之間漁翁得利。
2020年6月,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於美國“外交事務”網站發表了《瀕臨險境的亞洲世紀,中美對抗的危害》一文,表達了越發嚴峻的區域各國憂慮。
李顯龍
“亞洲世紀”:戒驕戒躁,慎思慎行
美國太平洋論壇上盛行一篇文章,名為“為什麼21世紀不一定屬於亞洲世紀”。
該文章長篇大論講述了中國現今的國際地位和未來發展,挑戰了所謂的“19世紀是歐洲的世紀,20世紀是美國的世紀,21世紀是隨著中國等亞洲大國的崛起,亞洲逐漸成為世界的中心和重心”這一說法,提出了“21世紀不一定是亞洲世紀”的論斷。
怎麼樣才能證明21世紀是如假包換的“亞洲世紀”?或者說,“亞洲世紀”完全等於“亞洲奇蹟”嗎?“亞洲世紀”的實現過程中遭遇了哪些挫折和磨難?又該如何克服,實現自我的超越?
中國身為區域內大國,必須明確自己的歷史地位和歷史使命。
在看到中國近代歷史上,確立的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朝貢關係在亞洲地區,尤其是東南亞地區的遺留時,無論朝貢體系本身先進或是落後的口水仗誰勝誰負,都必須承認多維的朝貢體系,決定了歷史上中國在亞洲的主導地位。
“亞洲世紀”是21世紀以來的熱詞,因上世紀50年代以後,亞洲在“二戰”風波過去之後,進入了高速發展階段,中國、印度、日本、“亞洲四小龍”等國家和地區飛速崛起,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亞洲各國積極開展產業升級和轉型,成功實現了亞洲經濟的快速復甦。
並在美國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面前,挺過了風浪與嘲諷,實現亞洲經濟不斷增長,貿易總額快速擴大,令一些鼓吹“亞洲世紀還未開始便已結束”的噓聲不攻自破。
而現如今,在新冠肺炎疫情惡潮的拍打之下,亞洲的經濟卻依然保持良好的增長態勢,向世界昭告,全球政治經濟中心和重心正在不可逆轉地向亞洲地區轉移。
首先,亞洲整體上保持了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
在亞洲,除了印度尼西亞以外,40年來從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歷過毀滅性通貨膨脹,貨幣當局穩定的宏觀經濟管理使得財政赤字得到有效控制,一旦經濟上迎來高速發展的契機,就會在財政上創造盈餘。顯然,一個‘“亞洲世紀”的到來,少不了充足的資金保障。
其次,穩健不等於保守,亞洲還致力於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出口已經成為了亞洲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亞洲地區,除了中國、印度尼西亞外,大國國家和地區都面臨著國內市場狹小的難題,因此只有轉向出口導向,保證國外市場的有效最小生產規模十分有必要。
正是在這種出口導向型經濟的推動之下,彼時,在許多亞洲國家地區實施進口替代措施,這意味著想要殺出歐美市場圈,亞洲生產者必須“過五關斬六將”,先打響本國國民度,再一步步接受經濟全球化市場的檢驗。
在這種運營模式下,亞洲國家打造了一批歷史悠久且富有競爭力的產品。
再者,亞洲國家趕上了工業化的浪潮,成功保持了十年內一如既往甚至愈發強勁的高速經濟增長,成功的工業化直接推動了亞洲國家經濟技術改造,使得工業結構迅速得到改善,工人階級不斷壯大,城市迅速發展。
工業化程序的不斷提高之下,大批優質人才轉向第三產業,為21世紀轉向“亞洲世紀”奠定了雄厚的工業技術和工業基礎,促使亞洲國家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內,實現了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再從工業社會邁向後工業社會和資訊社會的飛速騰起。
儘管工業化水平依舊暫時在國家和區域上發展不平衡,整體實力稍落後於歐美老牌大國,但亞洲的發展潛力足以令任何一塊大陸瞋目結舌。
絕大多數亞洲國家透過相關實用技術的轉讓,來吸引外商參與投資,助力工業化程序,這一模式不僅解決了亞洲國家發展資金不足的窘境,還從外商企業中學的了先進的管理經驗,前者是急人水火,後者則是授之以漁。
這樣,隨著亞洲工業化程序的不斷推進,工業化水平越來越高,越來越多的工商資本進駐當地,外國勞動力也隨之湧入就業市場務工,為亞洲國家創造穩定的就業機會和穩定的社會環境。
“美在亞洲”:美式霸權VS亞洲崛起
一片冉冉升起的新星大陸開始大放異彩,這其中必然會引起美國的注意,美國願意看到一個崛起的亞洲和一個強大的中國嗎?答案是否定的。
自奧馬巴“重返亞太”戰略,至特朗普推出“印太戰略”,都表明了美國試圖在亞洲建立一個以美國利益為中心的戰略佈局,表面上,美國似乎只是“對上了”中國,表現為中國崛起可能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的焦慮。
但實際上,在東北亞地區,中日韓歷史問題、朝核問題、香港佔中事件一直牽動著亞洲周邊地區的安全域性勢。
東南亞地區也並不安分,南海爭端使得中國和東南亞的合作面臨著重重阻礙,破冰融暖之旅道阻且長,美國當真是焦慮嗎?不得不說,焦慮的背後也不算亂打一氣,揪住老二就出手的瘋癲,和平崛起?不挑戰美國地位?
事實上,絆倒中國的最重要動機在於美國需要一個弱勢的地區大國,作為其重返亞洲,加強全球範圍內控制的傀儡。自然,中國做不到。
中國的崛起代表著什麼?放在區域範圍內甚至是世界範圍內來看,中國的崛起意味著“非西方世界”對美國主導下的所謂“民主”和“自由”的固有國際秩序的反思,代表著國際秩序公平化的大趨勢。
然而,在中美關係中,競爭大於合作,對抗大於攜手之時,一股較為悲觀的思潮湧動,即認為中國作為新崛起的大國必然需要直面現有亞洲政局不可避免地挑戰和衝擊,在這場對賭中,桌子的另一頭是美國。
龍鷹相鬥,不可避免地會引起夾在中間的東南亞小國對於治理危機和安全危機的擔憂。
拋開一部分統領控制慾和經濟既得利益,美國在亞洲地區具有三大事關國家安全的挑戰:
其一,“如何保持美國在印太地區戰略優先、促進自由經濟秩序”;其二,“如何保證朝鮮不在現在和未來威脅美國及其盟友”;其三,“如何在促進公平互惠貿易的同時提升美國的經濟領導力”。
從“亞太”到“印太”,印度以如此重量級的身份登場美國的對亞策略,不得不說,其居心實在險惡。
2021年1月12日,美國白宮號稱提前28年公佈了涉密檔案《美國對印太地區戰略框架》,其中重點闡述了美國自2018年至2020年對朝鮮、印度和中國的戰略圖景。
這份檔案,十分直截了當地說出了美國的目的,即“幫助印度崛起制衡中國”,“維持美國在印太地區的主導地位”。
在以往的思維定勢中,當這類新聞出現多次時,多數受眾會產生一種資訊刺激疲憊——“向來如此不是嗎?”“美國的目標不就是如此嗎?”可怕的不是美國堂而皇之地叫囂要以扶持傀儡來攪動亞太風雲,可怕的是在和平演變面前,人們對“惡”已然習以為常。
美國公然針對中國,將中國納入所謂的亞太圈內以企圖遏制中國崛起,但事實上,連美國自己也不敢直視“重返亞太”和“印太戰略”背後直指亞洲核心利益的嘴臉,不敢承認自己公然以域外國家身份干涉地區內事務:
當中印準備談談中印合作,龍象攜手時,美國這隻老鷹,仗著自己有翅膀,就撲騰撲騰地湊過來,我是隔壁山頭的老大,我們在地理意義上屬於鄰居山頭,所以現在我們是夥伴了,當然,想和我做朋友,得聽我的。強盜邏輯不過如此。
而現如今,美國依仗著長期依賴在印太地區紮下的經濟根基和軍事部署,強制要求區域內國家必須履行對話合作要符合美國利益和扶印抑中兩大條件。同時,主張在印太地區推行一個綜合經濟發展模式,以圖取代中國在區域內的經濟發展模式。
“地緣政治”:龍鷹相鬥,軟硬反思
在李顯龍的描述中,毋庸置疑,中國的快速崛起使得其硬實力在世界範圍內都是有目共睹的,因為他在文章中強調:“美國自己也不敢想象,取代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供應國,就像美國自己也不能沒有中國市場一樣。”
亞太國家並不願意在中美之間做出選擇,因為他們既無法保證中國在短時間內能夠完全填補美國軍事、科技、經濟領域的空白——事實上這是絕無可能的,也承受不起疏遠中國的代價。
因此,這些龍鷹相鬥之時,被夾在其中的國家確實有苦難言。國人常常說軟實力,但少有人真正明白軟實力到底有多麼重要,又是在哪一個節骨眼上發揮巨大作用。為何在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總會流傳一句:“經濟靠中國,安全靠美國”?
除卻經濟和外交領域的重要性同軍事、政治領域的重要性不可等同而論之外,中國需要正視一些國際上的聲音,如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所言。
經濟上的指標和外交上的成就可以充分反映中國經濟在亞洲的權重,但不能充分反映中國主導亞洲事務的能力,李顯龍除卻表明小國不想戰隊龍鷹之外,其意見的提出都不帶有明確的政治立場,多以一種客觀的陳述態度來擺事實,講道理。
為何李顯龍會發出“亞洲世紀”瀕危的喊聲?
首先,他在文章中提出:“皮尤研究中心釋出一項調查發現,加拿大、美國以及其他亞洲國家和西歐國家的人,對中國的看法越發負面。儘管在此前間中國努力地打造海外形象,透過中資國際報紙和電視媒體,透過孔子學院網路來打造海外軟實力,卻依舊於事無補。”
也許一些讚美美國是一個超級大國的言論並不動聽,但事實就是如此,現今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尚沒有國家可以撼動,李顯龍的發聲顯然是由於受到中國是地區內大國,而新加坡屬於東南亞唯一以華人為主的多元民族國家這兩點原因。
忠言逆耳利於行,在理性看待李顯龍的對中美關係提出的倡議時,更需要反思,中國的軟實力問題出在哪裡?
美國持續推進“亞太戰略”,甚至加碼為“印太戰略”,“再平衡”戰略受到亞太地區國家的歡迎;朝鮮半島局勢不穩定對中國周邊安全造成不利影響;日本大幅度調整軍事戰略;南海周邊國家安全域性勢能力有限……
諸此以往,需要承認的是,中國主導周邊安全域性勢的能力確實有限,國際上甚至在分析上述安全問題時,會將中國參與亞洲區域內組織的議程設定能力不足,作為一大原因。
身為一個具有十四億人口基數的大國,中國在引導國際輿論的“軟實力”領域尚待進一步加強。
然而,在促進“亞洲世紀”建設程序中談中國在亞洲的主事能力和領導能力,不能僅僅停留在老生常談的加強個別國家的軟實力建設,而應當密切關注新問題,去找與時俱進的新措施。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暴露了“亞洲”一定程度上仍然停留在地理意義層面,政治、經濟、文化缺乏整合的嚴重問題。
甚至麥肯錫研究所表明,世界上有“四個亞洲”——中國、新興亞洲、印度、發達亞洲、外圍亞洲。相當程度上指出了亞洲存在產業鏈分散化,碎片化的固有弱點。
誠然,“亞洲世紀”瀕危,除卻中美兩國在區域內的對抗使得亞洲國國自危之外,最為重要的是,在地緣政治和技術變革的影響下,全球化逐漸走向區域化、本地化和分散化,這不是一件壞事,但一個必要的前提:
加速區內經濟聯絡和區域外緊密程度同步提速推進,真正實現區域內經貿活動日益密切,這才是真正有意義的“亞洲世紀”。
參考文獻:
[1]:郭延飈 呂亞楠《淺析21世紀能否成為亞洲的世紀》
[2]:徐晏卓《變動中的亞洲秩序與中國影響力分析》
[3]:廖崢嶸《什麼才是真正有意義的“亞洲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