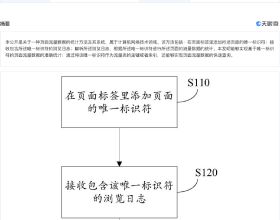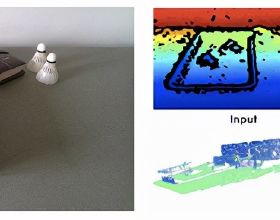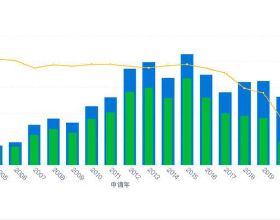秦行國
“夷夏”問題一直困擾著清帝,對於自關外入主中原的清朝而言,“夷夏”問題作為一種政治忌諱,時不時捲起風潮,觸碰到清帝的敏感神經。清帝一方面採用嚴厲的刪削、禁燬策略,對涉及到夷狄問題的圖籍進行全面處理;另一方面,也試圖樹立起一套新的夷夏觀,對傳統的夷夏觀進行了顛覆性改造。
刪削、禁燬的策略
晚近學者黃節較早發現康熙時編修的《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後省稱《彙纂》)中對《左傳》《公羊傳》有關“夷狄”文字刊落的情形,他覺得清帝作如此處理,是為“崇高其地位,使釋經者忘夷狄之恥”,滿人至關外入主中原,作為東夷異族,於圖籍中的夷夏之防、攘夷大義保持相當敏感與警覺。
不止《左傳》《公羊傳》,康熙的《彙纂》還對宋儒胡安國的《春秋胡氏傳》(後省稱《胡傳》)中申發攘夷之論的地方皆加以刪削。如僖公元年“夏六月,邢遷於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胡傳》雲:
書“邢遷於夷儀”,見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自遷為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興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至於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彙纂》中對此文字完全加以刪除。如僖公三十年“夏,狄侵齊”,《胡傳》雲:
左氏曰,晉人伐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遂侵齊,詩不云乎: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四夷交侵,所當攘斥。晉文公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率之職修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彙纂》將《胡傳》中討論“攘夷”的內容“詩不云乎: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四夷交侵,所當攘斥”加以刪除,諸如此類的例子舉不勝舉。
除了隱形的刪削手段,亦有因夷狄問題而產生文字之禍的治罪手段,康熙時處置過一樁私修明史的案子。浙江人莊廷鑨購得明人朱國楨的明史遺稿,並延請一大幫士子加以編纂,不久莊氏病歿,其父莊允誠於順治十七年(1660)將此書刻成,名為《明史輯略》。次年為人告發,莊允誠隨即下獄,莊廷鑨亦遭開棺戮屍。康熙二年(1663年),凡與此書相牽涉的人員,包括作序者、校閱者以及刻書、賣書、藏書者皆被朝廷處死,莊廷鑨之弟莊廷鉞也遭凌遲之誅,殃及同族,此案牽連到了千人之眾。《明史輯略》中涉及到滿洲入關以前的歷史,直言不諱地稱滿人為“奴酋”“建夷”“虜”等,這些明顯帶有強烈的夷夏之防情緒的文字,觸及到清廷的忌諱,遂釀成慘案。
乾隆對夷狄問題的敏感程度,亦毫不遜色於其祖父,借纂修《四庫全書》之機,對圖籍中所涉“夷夏之防”字眼皆加以嚴格處理。乾隆四十三年(1778),湖廣總督進呈的應毀各書清單中有兩部書赫然在列——明人鄭曉的《四夷考》與葉向高的《四夷考》,鄭著下附“內載《女直考》,語有違礙”之語,而葉著中列有《女真考》,將女直、女真列入四夷,這顯然是於滿人之大不敬,故遭禁燬。除了明確含有“夷狄”“四夷”字眼的圖籍之外,還有帶有容易引發夷夏之防聯想的詞句之圖籍,亦是稽查、銷燬的重點。四庫館臣制訂《查禁違礙書籍條款》,其中有一條說:
自萬曆以前,各書內偶有涉及遼東、女直、女真諸衛字樣者,外省一體送毀。但此等原地名,並非指斥之語,現在《滿洲源流考》內擬考核載入,似當分別辦理。如查明實止係紀載地名者,應簽出,勿庸擬銷。若語有違礙者,仍行銷燬。
在萬曆之前書中偶有涉及“遼東、女真、女直諸衛字樣”者皆要銷燬,“若語有違礙者,仍行銷燬”,“遼東、女真、女直諸衛字樣”皆是滿人入關之前的稱謂,遼東、女真、女直諸衛從地理方位上就屬於“夷狄”範圍,故這些稱謂很容易使人聯想到滿人來源於“四夷”的身份。
乾隆四十年(1775),湖南巡撫覺羅敦福查繳了陳祖法所著的《古處齋集》,其內第四卷《闈中》《秋感》二詩中有如“慚纓絡、泣冕旒、無明發、擊短纓”等句,被指“語涉詆譭,不應留存”“請旨銷燬”。另外,清初祝廷諍所作的《續三字經》內有“發左披,衣冠更,難華夏,遍地僧”字樣,戴移孝、戴昆父子所著之《碧落後人詩集》、《約亭遺詩》內含“長明寧易得”“短髮支長恨”之句,皆被視為“繫懷勝國”“指斥本朝制度”而遭懲治。漢人遵從的是“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的古訓,頭髮受之於父母,剃髮是為大不孝,而滿清入關以後要求剃髮,披髮左衽是夷狄風俗,故陳祖法、祝廷諍與戴氏父子皆是借“發”暗諷滿人,隱然表露夷夏之防,遂遭到清廷嚴肅處理。
《四庫全書》對宋儒胡安國《春秋傳》中的“夷”“狄”違礙等文字亦進行了大規模處理,將胡安國《春秋傳》激烈討論夷夏之防的文字皆加以刪削、剷除。如隱公二年“春,公會戎於潛”。《胡傳》原文雲:
戎狄,舉號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子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戎狄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君子外小人為泰,內小人外君子為否。《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載覆者,王德之體,內中國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繒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夷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羌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為此說者,其知內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奚會同之有,書會戎,譏之也。
《四庫全書》錄入之《胡傳》查不到此段文字,胡安國在此花費大量筆墨對《春秋》經文發表議論,將戎狄與“小人”同視,反覆陳說“內中國而外夷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警惕猾夏之禍,意在使人“知內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認為《春秋》經中書會戎,是譏戎狄也,通篇皆在議論戎狄與華夏的區別。這一討論很容易引發滿人作為外族的聯想。文公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洛戎,盟於暴”。《胡傳》原文雲:
《春秋》記約而志詳。其書公子遂盟趙盾及洛戎,何詞之贅乎?曰,聖人謹華夷之辨,所以明族類,別內外也。洛邑,天地之中而戎醜居之,亂華甚矣。再稱公子,各日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者,示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自東漢以來,乃與戎雜處而不辨,晉至於神州陸沉,唐亦世有戎狄之亂,許翰以為謀國者,不如學《春秋》之過,信矣!
此段遭全文刪削。胡安國認為,《春秋》中兩書公子遂以及會的具體時間、地點之緣由,是“聖人謹華夷之辨”,故“明族類、別內外”,中國與夷狄不可相混雜,其他幾處被全文刪除的,也大都如此。胡安國借用《春秋》經,連篇累牘地大加強調夷夏之別,在乾隆眼裡,這些都是極為刺眼的文字,遂遭到一例刪削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清帝一面刪削,一面禁燬,甚至加以治罪,實際是為了模糊民族分別,淡化滿漢衝突。
清帝對宋儒夷夏觀的改造
清帝不唯採取政治手段來嚴肅處理“夷夏”問題,對這一問題亦進行了充分地回應與解釋,試圖爭奪夷夏觀上的話語權。宋儒胡安國在《春秋傳》中從種族角度強調華夷之辨、夷夏之防。他指出“韓愈氏言,《春秋》謹嚴,君子以為深得其旨,所以謹嚴者,何謹乎?莫謹於華夷之辨矣”,“何莫謹於華夷之辨,要在明族類、別內外也”。隱公二年“公會戎於潛”,胡安國說:
《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以羌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
胡安國強調“內中國而外四夷”“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從地理上將之羌胡排斥在外。文公五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於暴”,胡安國說:
《春秋》記約而志詳,其書公子遂盟趙盾及雒戎,何次之贅乎?曰,聖人謹夷夏之辨,所以明族類、別內外也。雒邑,天地之中,而狄醜居之,亂華甚矣。再稱公子,各日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者,示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
胡安國“謹夷夏之辨”,“明族類、別內外”,批評戎狄居天下之中,乃“亂華甚矣”,表示中國、夷狄不可雜處,從種族上嚴守華夷之辨。
儘管清代官方對圖籍中的夷狄問題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刪削,但是並不避諱此一問題。康熙於二十五年(1686)編纂《日講春秋解義》(後省稱《日講》),表達夷夏之間本沒有嚴格的區分,關鍵在於是否守禮,夷亦可自進於中國。如僖公二十一年“公伐邾”,《日講》雲“邾曰蠻夷,蓋近諸戎,雜用夷禮,故極言之”,指出邾稱蠻夷,是採用了夷禮之故,如文公七年“冬,徐伐莒”,《日講》雲:
徐,僭號,即戎也。後自進於中國,數從會伐,經皆稱人,以能其附中國也。今以中國無霸,興兵伐莒,故以舉號。
《日講》以為徐本是戎狄,“後自進於中國”,在於其數從中國會伐,依附中國。可見,華夏可以滑落為夷狄,夷狄亦可以轉變為中國。
雍正曾於七年(1729)刊刻《大義覺迷錄》,頒行天下,其中就有諸多討論《春秋》中夷狄的問題。在雍正看來,《春秋》大義乃君臣、父子之倫,雍正進一步駁斥曾靜、呂留良:
而中國有論管仲九合一匡處,他人皆以為仁,只在不用兵車,而呂評大意,獨謂仁在尊攘。彌天重犯遂類推一部《春秋》也只是尊周攘夷,卻不知《論語》所云“攘”者止指楚國而言,謂僭王左衽,不知大倫,不習文教,而《春秋》所擯,亦指吳、楚僭王,非以其地遠而擯之也。若以地而論,則陳良不得為豪傑,周子不得承道統,律以《春秋》之義,亦將擯之乎。
曾靜認為“一部《春秋》也只是尊周攘夷”,呂留良在討論管仲管仲九合一匡之功時,“獨謂仁在尊攘”,雍正一併加以反駁,他引用《論語》解釋“攘”僅指的是楚國,“謂僭王左衽,不知大倫,不習文教”,“《春秋》所擯,亦指吳、楚僭王”,並不是在於地理之遠近,他所要突出的依然是君臣大倫、尊王之義。也就是說,夷夏之間的區別根本在於是否講究君臣、父子之倫。在《大義覺迷錄》中,雍正表示“朕於普天之下,一視同仁”,大清乃是“合蒙古、中國一統之盛,並東南極邊番彝諸部俱歸版圖”,故不當“以華夷而更有殊視”,天下一統,華夷一家。是故,文教與地理上的一統,皆成為清帝反駁傳統以種族區隔為中心的夷夏之辨的依據,以此論證其統治正當性的理論支撐。
乾隆於二十三年(1758)編纂《御纂春秋直解》(後省稱《直解》),對夷狄多有褒獎、稱許。如僖公十八年“狄救齊”,《直解》雲“苟有善,雖狄必予之”,對狄救齊之舉表示讚許,如襄公十八年“春,白狄來”,《直解》雲:
春秋之時,戎狄錯居中國,與之會盟則有譏。若其慕義而來,則容而接之,亦非不可,惟謹所以待之之道而已。
《直解》並不完全按照《春秋》中的理解,夷狄與中國會盟而持批評的態度,相反對夷狄“其慕義而來”,採取接受的態度。乾隆曾對胡安國的華夷之見表現出相當地不滿,並斥之為胡說:
又是書既奉南宋孝宗敕撰。而評斷引宋臣胡安國語。稱為胡文定公。實失君臣之體……夫大義滅親,父可施之子,子不可施之父。父即背叛,子惟一死以答君親。豈有滅倫背義。尚得謂之變而不失其正。此乃胡安國華夷之見,芥蒂於心,右逆子而亂天經,誠所謂胡說也。其他乖謬種種,難以列舉。
乾隆批評胡安國“華夷之見,芥蒂於心,右逆子而亂天經”。其與康熙一樣,乾隆亦表示夷夏之間並無根本區分:
大一統而斥偏安,內中華而外夷狄,此天地之常,今古之通義。是故夷狄而中華則中華之,中華而夷狄而夷狄之,此亦《春秋》之法,司馬光、朱子所為亟亟也。
乾隆以大一統自居,丟擲“夷狄而中華則中華之,中華而夷狄而夷狄之”之論,指出中國與夷狄之間是可以相互轉化的。清帝將《春秋》中的“夷夏之防”轉變為夷夏無別,實則為滿漢、中外一體的民族觀提供依據。康熙在滿漢、中外關係上,倡導“滿漢一體”“中外一體”,康熙二十四年(1685),他稱“滿漢人民,俱同一體”,康熙四十三年(1704),他稱“朕於滿洲、蒙古、漢軍、漢人視同一體”,康熙五十年(1711),稱“朕統御寰區,撫綏萬國,中外一體”。乾隆亦有一樣的看法,他表示“夫蒙古自我朝先世,即傾心歸附,與滿洲本屬一體”,“國家中外一家,況衛藏久隸版圖,非若俄羅斯之尚在羈縻,猶以外夷目之者可比”。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清帝對宋儒胡安國《春秋傳》中堅持“夷夏之防”的觀念進行了顛覆性的改造,強調夷夏本無分別,從文教、禮儀、地理大一統的角度,打破了胡安國所堅持的夷夏之間以種族為限制的傳統壁壘。
清人入關,儘管地理、疆域上實現了大一統,然面臨著種族、文化之異所帶來的巨大考驗。從康熙到乾隆,清帝對夷夏問題的處理愈來愈峻烈,刪削、禁燬,甚至不惜治罪,以高壓式的政治手段,清除夷夏之間的文化記憶與知識記憶,這只不過是剛性策略之一,直面並回應這一問題似乎更為要緊,清帝透過文教手段,對《春秋》中的夷夏問題重新進行討論、解釋,爭取夷夏觀上的表達權,這種柔性策略更具有說服力。邁過海內外種種論述,我們能具體注意到清帝的政治言說藝術,是如何克服種族、文化的衝突與障礙,使得清朝成為一種超越的共同體。
責任編輯:鍾源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