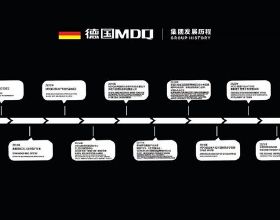懷疑論(Skepticism),是一種認識論,是認識問題的一種態度,它拒絕對問題作隨意的不夠嚴格的定論,對事物的看法採取一種類似於“中立”的立場,既懷疑“是”也懷疑“不是”。
在科學研究中,懷疑論對物理學家和心理學家有著極大的吸引力。為了驗證這一觀點,杜魯門州立大學的物理學副教授坦納·埃迪斯(Taner Edis)對2021年3月和4月的《懷疑調查》進行了研究,查看了封面上列出的懷疑調查委員會(CSI)研究員及其科學和技術顧問的附屬機構。據統計,大約20%的人員有物理學和天文學的背景,佔比最多。心理學家以16%的比例位居第二,而其他學科人員的比例都遠遠落後於以上兩者。經過進一步地仔細觀察,坦納發現只有幾個著名的懷疑論者是歷史學家,尤其是科學歷史學家,換句話說,似乎只有少數研究反科學運動的社會學家或政治學家得到了CSI的認可。
毫無疑問,造成這一現象的部分原因是由於專家們自身的興趣。對坦納而言,他教授物理學科,專業相關的性質便使得他很容易能闡明與超自然力量、自由能量或外星人相關的科學錯誤很容易。他最初對於偽科學和超自然現象等具有濃厚的興趣,因為它們都是物理學錯誤理解的典範。他還教授一門跨學科的研討會課程,名為“怪異科學”,這門課鼓勵不同專業的學生透過檢驗超自然現象和偽科學主張來探索科學的本質,班上心理學專業的學生通常都很熟悉那些助長怪異信念的認知偏見。物理學家喜歡解釋為什麼一種現象(如千里眼)不符合我們目前對世界執行規律的理解,而心理學家可以證明超自然力量為何無法透過實驗進行測試。此外,心理學家進一步推動了我們的理解,告訴我們為什麼心理信仰仍然如此令人信服。透過研究,坦納也理解了為什麼許多心理學家喜歡批判懷疑主義論研究目標的這一怪異之處了。
因此,懷疑主義論的標準實踐大量借鑑了自然科學和心理學,並摻雜了一些二十世紀中期的科學哲學。物理學家、生物學家和化學家們解釋了為什麼量子神秘主義、大腳獸、順勢療法等這些特殊的怪異現象看起來是可疑的。心理學家測試人類的能力,並描述了讓我們所有人都容易受到怪異信念影響的認知怪癖。大多數懷疑論者用一份可靠的非正式謬論清單(Boudry 2017)以及一份偽科學屬性的清單來總結他們的標準方法。我們經常說,科學是由科學方法來定義的,但問題就始於怪異現象的提供者不遵循科學的方法。
在陰謀論正在吞噬政治、反科學運動企圖解釋氣候變化而否認正在引發文明崩潰之際,區分真假知識並非小事。因此,坦納希望這種標準的懷疑論方法,能夠解決像“占星術”和“能量療愈”這樣的麻煩,併為處理更多的怪異現象做好準備。
採取什麼樣的方法?
無疑,標準的懷疑論方法存在一些缺點。例如,我們的科學哲學已經嚴重過時了,而許多懷疑論者仍在援引預先設定好的科學方法、科學的基本邏輯,以及可證偽性等標準,將真正的科學與偽科學區分開來,但這些標準沒有一個是長期存在的。有很多哲學家、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研究科學的運作原理,但他們不會對科學做出不切實際的斷言,而是仔細研究科學變化,對實際發生事件的細節進行描述,這種細緻事實上正是懷疑論研究所需要的。從事科學研究的學者們很可能會說,沒有專門的方法來定義科學,但事實恰恰相反:我們可以透過學科重疊或交叉的方法來建立起不同領域的知識。換句話說,如果我們僅僅認為科學方法優於鑽研和解釋,認為它是一種專注於知識和最佳解釋的超自然規則,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每種科學方法是否有效本身就是一個關於世界的事實(Edis 2018a)。科學領域,正如同生活中的許多突發狀況一樣,我們總是在一邊前進,一邊創造新的事物。
事實上,我們的認知偏見和推理錯誤清單已經足夠有用了,但我們可能還會忍不住把它們擴充套件得更多。某些型別的怪異事件,如對幽靈和鬼魂的信仰等深深根植於人類思維 (Turner et al. 2017)。即使在科技高度發達的當今社會里,我們也會看到很多人對鬼魂和超自然能力缺乏系統有條理的認識。我們現在能做的,也許就是防止讓人相信鬼魂的認知偏見,並讓這種偏見遠離我們的科學研究領域。
其他種類的怪異事件,如神創論,跟上述的鬼魂信仰則有所不同。雖然神創論利用了傾向於設計和目的的認知偏見(Kelemen 2012),但“科學”的神創論和智慧設計的複雜偽科學,如果脫離了高度組織化的神教背景和反對世俗化趨勢,便無法理解。但事實上,神創論似乎比那些從認知偏見中冒出來的鬼魂信仰更具社會和歷史深度。
對抗“神創論”
最令坦納著迷的怪異事件便是伊斯蘭的各種創世論。因為弄清楚對於一些事情的解釋是如何出錯的,對於弄清世界的運作原理而言非常有用,因此坦納從追蹤物理學和生物學上的神創論錯誤開始探究。然而,尋找對神創論更全面的理解這一過程超越了科學錯誤和認知偏見:虔誠的宗教團體也並不一定要接受神創論,相反,他們也可以被動地拒絕進化論,忽視對傳統信仰的科學挑戰。在某種時刻,宗教知識分子提出一種替代主流科學的方法,這種方式也會引起強烈反響。對坦納而言,這些偽科學的事例研究比一群業餘的“幽靈獵人”濫用實驗儀器更有趣,也更有影響力。弄清楚神創論者為何無法準確地描述這個世界,也會讓我們學習到更多關於真正科學本質的東西。
實際上,神創論並非源於個人的認知錯誤,它是由一些機構來組織和推廣的,如《創世紀的答案》或《探索研究所》等的辯解工廠,也包括保守派宗教和媒體網路。在某些情況下,神創論者試圖透過繞過或改造主流科學機構(如大學的科學系),比如在伊斯蘭主義者統治下的土耳其,從而大獲成功(Edis 2021)。如果我們認為各種神創論都不是真正的科學,這是因為主流神創論者錯誤地描述了物理學或生物學。神創論不是科學,因為它的機構並不是用來真正地瞭解世界的(Edis 2018b)。神創論者致力於創造一種另類的知識文化,在這種文化中,那些與主流科學家格格不入、近乎瘋狂的主張反而更加可信,其中一些工作包括利用認知偏見和常見的推理錯誤來道歉。在社會環境中,信念是有代價的:我們需要投入資源來獲取關於世界的信念,我們也會因為堅守信念並根據信念行事而產生成本。在強調群體忠誠的政治環境中,這樣的成本使一些錯誤信念變得具有工具理性。
如果我們想在“幽靈”和“大腳獸”等怪異事件之外運用懷疑論,解決當今存在的威脅文明的反科學運動,那麼我們需要從神創論中學習的便更多了。否定科學最重要的形式是有組織的、社會的、政治的,這就要求我們不僅僅要關注個人認知上的缺陷,也要更加關注制度。
社會建構懷疑主義
懷疑論者強調自然科學和心理學,不習慣偏向歷史和社會的思維方式。他們不喜歡政治,更喜歡“實事求是”的專業知識。此外,系統的懷疑主義具有強烈的科學倡導元素,能夠將研究者吸引到與人類進步相一致的科學英雄形象上去(Pinker 2018)。然而,如果我們把注意力全部轉移到制度上,我們很快就會發現,對制度的分析也可以應用到科學和懷疑論中。其中,需要注意的一個原因是,懷疑論者的近代科學哲學強調知識是如何社會化建構的。傑出的科學家和懷疑論者仍然會談論幾十年前“科學戰爭”的情節,以說明後現代社會對科學的批評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極端的(道金斯,2021年)。
在今天的科學研究中,科學是一種社會建構,並已成為一種司空見慣的現象。但我們透過社會機制來構建知識這一事實,並不意味著科學是不可靠的、武斷的,或者說科學脫離了實驗室的現實檢驗。社會建構並不意味著科學是神話,正如神經學家所言,人的推理是由於神經元放電,這意味著人們所有的想法都是幻想。因此,我們必須把科學和理性看作是一種世俗現象,而不是超驗的理想。科學研究對懷疑論者的神話設想提出了質疑,但這種懷疑來自於對科學機構的詳細調查,旨在解釋科學已經取得的突破和進展。CSI中至少有一位研究員——科學歷史學家內奧米(Naomi Oreskes),她採用了更為複雜的科學研究視角,認為科學專業知識完全值得公眾信任(Oreskes 2019)。

內奧米的ted演講,題目為《我們為什麼應該相信科學家》圖源:ted.com
坦納稱,研究機構中浮現出的更混亂、次英雄式的科學圖景更加準確。如果想要更精確,與複雜的物質現實更充分地接觸不失為一個更好的選擇。然而,把理性帶到現實中也會帶來一些棘手的問題。如果人們能找出創世論中的制度弊病,那麼他們必定也會對大學和研究機構的缺陷而感到好奇。任何批判大學管理、資助機構或同行評審程式的科學家們都知道,研究機構很重要,它們卻從來都不是完美的。但如果人們瞭解了一些機構特徵,並且這些特徵促進了人們對超自然現象和偽科學信仰的理解,那麼人們就可以利用這些知識來改進做真正的科學研究的方式。
懷疑論者也促進了公眾對科學的討論與交流。人們想要正確地溝通,關注知識生產的歷史和社會背景尤為重要。人們經常採用一種模式,即懷疑論者代表科學專業知識,並採取實際行動來糾正那些被認知偏見和錯誤推理誤導的人。但是,像神創論這樣的例子也充分暴露了這種模式的侷限性。在神創論中,偽科學被編織進右翼民粹主義運動中,“信任科學”這樣的口號不僅承認了現實的政治中立,而且也與技術官僚政治相結合,這促進了專業階層的利益,而非競爭群體的利益。然而,科學家和懷疑論者的利益並不總是與經濟學家、管理顧問或科技寡頭的利益相同,以種族或宗教為中心的民粹主義政治並不能滿足我們對純粹知識的渴望。我們的科學利益也可能與專業派別發生衝突,這些專業派別將會把科學變成生產智慧財產權的工廠,成為商業和技術的基礎設施(Edis 2020)。
不可否認,科學的進步總是伴隨著制度的變革,這通常也是對資金來源要求等外部壓力的反應。但我們也應深思,如何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更好地進行科學研究呢?
歷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學者對科學更準確的理解需要認識到偽科學存在的永續性,也需要更多地關注制度。這都要求懷疑論者要更好地利用歷史和社會視角,跨越物理學和心理學的界限。
對坦納而言,在懷疑論的圈子裡遇到更多的歷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是值得開心的。在他從教的幾十年中,不僅遇到了心理學家和其他學者,還遇到了像魔術師、媒體評論家和維權的消費者等人士。當坦納向他的學生傳授關於量子力學的深奧知識細節時,他總是擔心把時間花在了只有少數有抱負的專家才會關心的事情上。但是,當對超自然現象和偽科學主張提出懷疑時,他就與關於知識本質和現實的更深層次的問題建立起了聯絡。事實上,幾乎每個人都能找到值得關心的事情,甚至是能夠做出貢獻的事情。因此,要想用懷疑主義做更好的研究,我們便需要進一步拓寬自己的視野,從歷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那裡學習更多我們缺乏的東西。
如果我們足夠幸運,能夠儘可能地不摧毀文明,那麼在10年或20年後,CSI研究員和顧問的數量將只有一小部分的物理學家和心理學家,而更多的則是歷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那會是一種進步,因為懷疑論離不開歷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學者的參與。
注:坦納·埃迪斯(Taner Edis)是杜魯門州立大學的物理學副教授,最新著作《和諧的幻覺:伊斯蘭教的科學與宗教》(普羅米修斯出版社,2007)。
參考文獻:
Taner Edis. (2021, September/October). Skepticism Needs More Historians and Social Scientists.
Boudry, Maarten. 2017. The fallacy fork: Why it’s time to get rid of fallacy theory. Skeptical Inquirer 41(5): 46–51.
Brown, C. Mackenzie, ed. 2020. Asian Religious Responses to Darwinism: Evolutionary Theories in Middle Eastern, South Asian, and East Asian Cultural Contexts. Basingstoke, United Kingdom: Springer Nature.
Dawkins, Richard. 2021. Science: The gold standard of truth. Skeptical Inquirer 45(2): 38–40.
Edis, Taner. 2018a. Two cheers for scientism. In Maarten Boudry and Massimo Pigliucci, eds., Science Unlimited? The Challenges of Scientis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018b. From creationism to economics: How far should analyses of pseudoscience extend? Mètode Science Studies Journal 8: 141–147.
———. 2020. A revolt against expertise: Pseudoscience, right-wing populism, and post-truth politics. Disputatio Philosophical Research Bulletin 9: 13.
———. 2021. The Turkish model of Islamic creationism. Almagest 12: 40–65.
Edis, Taner, and Maarten Boudry. 2019. Truth and consequences: When is it rational to accept falsehoods? Journal of Cognition and Culture 19: 153–175.
Kelemen, Deborah. 2012. Teleological minds: How natural intuitions about agency and purpose influence learning about evolution. In Karl S. Rosengren, Sarah K. Brem, E. Margaret Evans, et al., eds. Evolution Challenges: Integrating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about Evolution. Oxford, United Kings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eskes, Naomi. 2019. Why Trust Sci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inker, Steven. 2018. Progressophobia: Why things are better than you think they are. Skeptical Inquirer 42(3): 26–35.
Turner, Jonathan H., Alexandra Maryanski, Anders Klostergaard Petersen, et al., eds. 2017. The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of Religion: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Abingdon, United Kingdom: Taylor & Francis.
徵稿啟事
中國科學探索中心微信公眾號歡迎賜稿!
稿件內容以反偽破迷為核心思想,科學普及、科學文化、科技哲學、科學與公眾、世俗人文主義、科技倫理等領域均可涉及,旨在將科學探索結果無偏見地告知公眾,避免公眾上當受騙。
稿件一經採用,將奉上稿酬。
投稿郵箱:
崇尚科學 反偽破迷